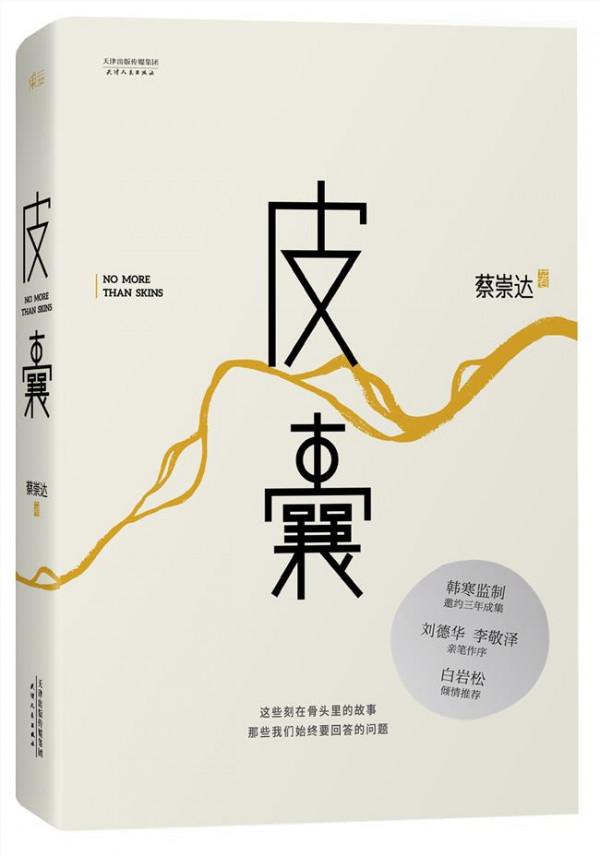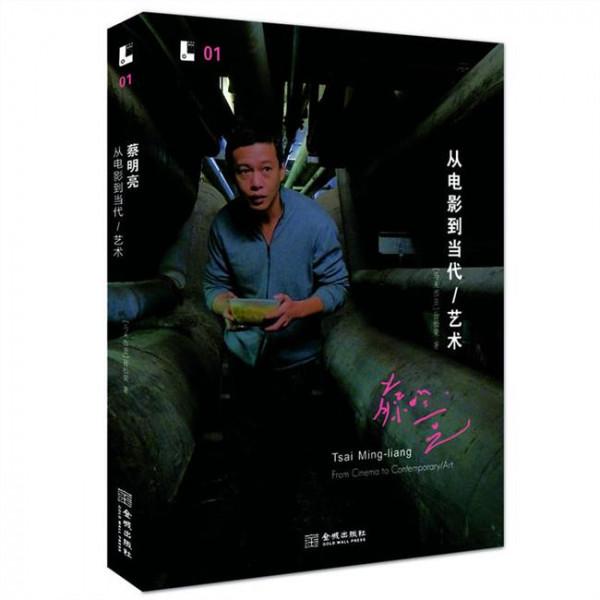聂华苓三生三世读后感 看电影《三世三生聂华苓》
闲来无事,想随便找个电影看,借以打发时间。找来找去,我喜欢看的动作片和恐怖片几乎没有什么看的了。无意之中,点到一个纪录片的栏目里头,就看到了一个电影名《三生三世聂华苓》。因为先前看过一些关于聂华苓的消息,最起码知道她是一个作家。然后就毫不犹豫的点击去看了……
记得是在今年5月第一次听到聂华苓这个作家名。一个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要我帮他找几本聂华苓的书,说是写论文用。我碰巧刚淘到了她的《失去的金铃子》和《千山外,水长流》两本书,于是就先给了他。后来,他又问我要《桑青与桃红》、《葛藤》和《翡翠猫》。结果,我花了很长时间都没有找到。后面,就不了了之了。聂华苓,这个名字,我倒是记住了。百科了一下“聂华苓”:
聂华苓(1925年1月11日——)。生于武汉,湖北应山(现湖北广水)人,1948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前身)外文系,同年以笔名远方发表第一篇文章《变形虫》。1964年旅居美国,应聘至美国华盛顿《作家工作室》工作,在爱荷华大学教书,同时从事写作和绘画,因创办国际作家写作室,被称为“世界绘画组织的建筑师”、“世界文学组织第一”。
代表作有短篇小说《翡翠猫》、《一朵小白花》、《台湾轶事》,长篇小说《失去的金铃子》、《千山外、水长流》、《桑青与桃红》,散文集《梦谷集》、《三十年后》,翻译集《百花文集》等。
人物关系一栏写着:女婿李欧梵
旁边配了一张她的晚年时的照片。一个戴着大镜框的安详的老太太。我猜她应该很喜欢笑。看这张照片就感觉她随时可能要笑。她的一生肯定经历了很多事情,但她肯定有了广阔的胸襟和乐观的生活态度。我猜她应该是这样。很多上了年纪却依旧显得安详的作家不都是这样吗。
作家最起码要拿出比较靠谱的作品出来说话。这是我一贯的想法。于是,就拿出我自己留的一本《失去的金铃子》来看。人文社1980年的本子,书页都已经严重发黄了。写在前面里头有一段话,让我读过之后有一些感触:
一九六O年,我工作了十一年的杂志停刊了;主持人雷震和其他三位同事以“涉嫌叛乱罪”关进牢里。我成了一个小孤岛,和外界完全隔离开了。那是我一生中最黯淡的时期:恐惧,寂寞,穷困。我埋头写作。《失去的金铃子》就是在那个时期写出来的。它使我重新生活下去;它成了我和外界默默沟通的工具——小说在读者之中的确引起了一些反应;台北的学生书局、文星书店、大林出版社陆续再版数次。
这可以说是这本书的写作背景的一个简单的介绍。六十年代的台湾还是一个动乱的地方。聂华苓在恐惧、寂寞和穷困中埋头写作,那自然是在用心在写,写出来的文章肯定也不会差。于是,花了很短一段时间就把这本书看完了。感觉有一些沈从文的《边城》的味道,尤其是那种旧时代里的乡土气息,简直是迎面扑来,洗人肺腑。
又由于同饮长江水的缘故,那种熟悉的乡土气息、风土人情更是浓得有些化不开了。跟《边城》不同的是,它没有像山歌对唱、龙舟竞赛这些宏大、热闹的场面,也没有最后白房子倒塌的悲惨结局。
它描写的是抗战时期一个在外读书的少女返回故乡的一段经历和见闻——山村故土的一些平平常常的人,一些简简单单的事。这些人、这些事细腻地、舒缓地展现出来,象一幅写意的山水画,素淡而隽永,带着一些诗意。虽然故事不长,但看完感觉有一股淡淡的茶香自从心生。
后来又找到一本《20世纪台湾文学史略》。里面是这样介绍她的:
聂华苓是著名的美籍华裔女作家,湖北应山人,1926年出生于宜昌,她的父亲是桂系军阀的官僚。1949年到台湾,在《自由中国》杂志社当了11年的文艺栏编辑。1960年杂志被国民党当局封闭后,聂华苓先是闭门写作,后来在台湾大学、东海大学教书。
1964年到美国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室”任教,不久与美国著名诗人保罗·安格尔结婚。他们发起组织了“国际写作计划”。她不仅以丰富的创作实践著称,而且因为卓有成效的文学活动而蜚声世界。
在台湾当代文学中,聂华苓是较早注意到思乡病和失根这一题材的作家。
她的比较重要的作品《桑青与桃红》同样取材于现实生活,但是融会了寓言体小说、超现实主义、荒诞派等写作手法……小说曾被《亚洲周刊》选入“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
后来,我又淘到了一本潘亚暾的《海外华文文学现状》。人文社1996年,刘以鬯先生题字的本子。里头是这样说的:
聂华苓(1925——),祖籍湖北应山,生于宜昌,在武汉长大。祖父擅长赋诗,中过举,当过知县;父亲是军人。抗战期间,辗转于湖北、四川等地上中学,后入中央大学外文系。1948年大学毕业。1949年全家移居台湾。
在《自由中国》杂志社当了11年的文艺栏编辑。1960年该杂志遭封闭,她曾在台大和东海大学任教。1964年,赴美参加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室”工作,不久与美国著名诗人保罗·安格尔结婚。1967年,“国际作家写作室”成立,由聂华苓和安格尔主持,成为国际文化交流的桥梁。
在过去的十几年间,该“写作室”接待了来自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作家。聂华苓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作出了杰出的贡献。1978年以来,她曾多次回祖国参观访问。1981年,获美国杜布克大学和科罗拉多州立大学颁发的荣誉文学博士学位。1989年退休后,仍笔耕不缀。
对共产党、新中国的认识,聂华苓经历了一个由怨恨到客观的变化过程,这对她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聂华苓早期创作的短篇小说集《翡翠猫》、《一朵小白花》等,主要表现从大陆流落到台湾的小市民的惨淡人生。
1960年她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失去的金铃子》,这是她早期小说中的代表作。
1971年,聂华苓出版了第二部长篇小说《桑青与桃红》,标志着她的创作进入一个新的层面。
1984年,聂华苓又创作了第三部长篇小说《千山外,水长流》。这是一部历史感很强的小说,流露出美华文学中罕见的乐观情调。
聂华苓新近创作的中篇小说《死亡的约会》也广受好评。
聂华苓的散文也很有特色,三联书店香港分店最近出版了她的散文集《黑色,黑色,最美丽的颜色》。香港作家彦火在《当代中国作家风貌》一书中用“风笑”二字形容聂华苓,她的散文也恰如其人,就像一阵阵爽利的清风,伴随着透亮透亮的笑声。她散文的文风是年青的,充满活力,给人一种连跑带跳、连说带笑之感。
文学史里的这些东西毕竟是模糊的,说了一大串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更何况,有些文学史的考据工作做得实在太差,甚至一不小心就出错。所以,只好对照着读一读。
手头还留有一本《千山外,水长流》,先留着吧。以后再慢慢体会。好书总是很多,而时间却不够。以后总会有时间去读的。《桑青与桃红》和《三生三世》也都从网上下载下来了,一并留着,以后慢慢来享用。剩下的几本书有机会也会去淘回来好好读的。
看了那么的介绍,终于还是到了电影环节。
电影是以采访和回忆的形式展开的。一座木头的房子,看着相当雅致,就是她现在居住的地方。一面墙上挂着很多的图腾面具。一开门,聂华苓就笑着拥抱中国来的客人。后面几乎都是她的回忆。
我是一棵树,
根在大陆,
干在台湾,
枝叶在爱荷华。
这样一句话,很好的概括了她四处流浪的一生。她出生在武汉,因为战乱,14岁便逃到宜昌三斗坪。《失去的金铃子》这本书的故事背景大概就是在这里了。1948年,她看到左右两派的互相攻击,觉得荒谬,于是写了《变形虫》。
49年,24岁的她带着全家到了台湾,并与王正路结婚,生了两个女儿。然后到《自由中国》做了编辑,结识了雷震、殷海光、胡适(电影画面里一直都有胡适出现,但聂华苓似乎一直都没有提过他,不知为何)等人。60年,《自由中国》被封。聂华苓于苦闷中写出《失去的金铃子》。
我觉得,热情为人带来的如此破坏性的结局,远不如一种迟缓安静的痛苦更有悲剧感。
这是《失去的金铃子》里的一句话,启发了作家蒋韵和李锐。
大弟弟飞行失事,让聂母很受刺激。
天蒙蒙亮,母亲醒来,看见我在床边,拉着我的手说:你在这里,我就安心了。这几天,你猜我想什么人?想你爹!二、三十年了,怎么现在这么想他!我一个人躺在床上想,说不定他会走进房,笑眯眯的,也不说话。我问他:噫!你怎么来了?你害我吃了这么多年的苦,把女儿都抚养成人了,你来享现成的福呀。
这是聂华苓回忆母亲的文字,字字见来都是情,也都是亲啊。
台湾的白色恐怖,让聂华苓再次流浪。于是,她就来到了爱荷华,也遇到了她一生的真爱——保罗·安格尔。他们相爱,然后结婚,一起发起组织了“国际写作计划(即IWP)”。于是,我们在电影画面里看到了很多我们熟悉的作家:萧乾、丁玲、艾青、陈白尘、茹志鹃、王安忆、吴祖光、徐迟、谌容、张贤亮、冯骥才、白桦、汪曾祺、北岛、阿城、刘索拉、王蒙、莫言、余华、格非、古华、毕飞宇、残雪、苏童、刘恒、李锐、西川、孟京辉,港台的有余光中、陈映真、梁牧、王文心、白先勇、柏杨、林怀民、蒋勋、骆以军、李昂、董启章、王祯和、郑愁予、痖弦、殷允芃等。
当然还有很多其他国家的著名作家(总计近600名),都来到了他们这个计划之中。他们吃喝谈笑,甚至打架,到最后都是带着满满的收获回家。
聂华苓与安格尔夫妇为此在1976年还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被誉为“实现国际合作梦想的一个独特的文学组织的建筑师”。这让我想起了电影《鲁迅》里头鲁迅对萧军和萧红两人的支持,又是请吃饭,又是给路费。
但鲁迅毕竟只是在国内如此,而聂华苓夫妇他们却将这种精神发扬到了国际上。这对跨国夫妇的胸怀与智慧实在是让人不得不佩服。在那个战乱纷飞的年代,他们深刻的认识到,只有文学、艺术、科学是能够超越国界的,事实也真的证明了这一点。
电影画面中的一个个作家都那么的精神,那么的开心,就因为聚到了这个写作计划之中。这是一种文化与心灵上的包容,一种凌驾于经济基础之上的自由的精神交流。
同时我在想:那时的文坛真的与现在的速食文化、网络文化差距太大,他们淳朴、真诚,或尖锐、刻薄,或忧郁、沉思,但每一个人又都像小孩子那么的可爱。我实在忍不住掉下眼泪,因为我看到一个女作家抱着聂华苓说:“你就是我们共同的妈妈。”
电影快要结束的时候,聂华苓回到台湾参加纪念殷海光和雷震的纪念会。当时的台湾最高领导人马英九代表国民党向白色恐怖中遭到迫害的文人志士表达了最深刻的道歉与忏悔。这是多么让人感动的一鞠躬啊。历史的问题,本不能归咎到一个人或一群人头上。但他们却有勇气正视历史,承认事实。他们愿意用自己的坦诚,获取死难者家属与世界的原谅。这种气魄,实在让人不能不敬佩。
到最后,聂华苓又回到了自己的爱荷华小屋。回忆、写作、做家务,还要时不时往写作中心跑一跑。一个经历了死亡、战乱、流亡和短暂的快乐、幸福和辉煌的中国女性,一个处处在“外”而又时刻不忘本不忘根的中国女作家,最后能够安享晚年,也算是一个美好的结局吧。
看着她蹒跚前行的身影,我真想冲上去扶她一把,告诉她:我也是一个文学爱好者。我相信当她看到我这张年轻的中国人的脸,肯定会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再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
电影已经演完了,脑海里出现了一些碎片,碎片慢慢拼成了一些问题。于是,我问自己:如果我是她,我会坚持走完自己平凡而又有价值的一生吗?不要慌着回答。这样的一个女作家,生长于武汉,在宜昌也待过,为什么武汉几乎从来不提她的名字,湖北也不提她的名字呢?就连各大高校的文科教材也很少提到她呢?武汉的各种大小书店也几乎看不到她的书。
国际写作计划和创意写作的构想似乎很有些类似,国外似乎很流行,也确实让人看到了成效,但在国内似乎还很不成气候。中国当代的文人究竟要怎样才能活出一条路来?中国当代的文学又要如何才能散发一丝活气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