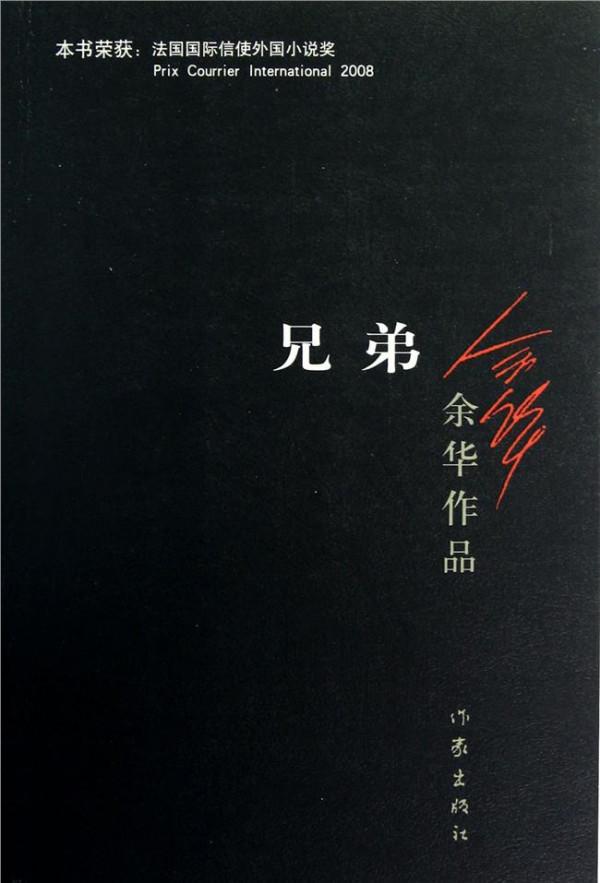在细雨中呼喊余华 余华《在细雨中呼喊》:自我凌迟的艺术
《在细雨中呼喊(2012年版)》内容简介:余华的第一部长篇力作。小说描述了一位江南少年的成长经历和心灵历程。作品的结构来自于对时间的感受,确切地说是对记忆中的时间的感受,叙述者天马行空地在过去、现在和将来这三个时间维度里自由穿行,将忆记的碎片穿插、结集、拼嵌完整。作者因《在细雨中呼喊(2012年版)》荣获法国文学和艺术骑士勋章等奖。
余华(1960-)当代作家。浙江海盐人,出生于浙江杭州,后来随父母迁居海盐县。中学毕业后,因父母是医生,作了牙医,五年后弃医从文,进入县文化馆和嘉兴文联,从此开始文学创作生涯。曾在北京鲁迅文学院与北师大中文系合办的研究生班深造,1984年开始发表小说。
余华是中国先锋派小说的代表人物,与叶兆言、苏童等人齐名。作品有短篇小说集《十八岁出门远行》、《世事如烟》,长篇小说《活着》、《在细雨中呼喊》及《战栗》。
媒体书评:
自我凌迟的艺术
一、前言
阅读余华的小说并不让人愉悦,反倒更像是一种折磨,但又不忍释卷。进入正题前,我想先扯点闲话,说说这种奇特的阅读经验:读余华早期小说的同时最好佐以闲书以平衡心理的负荷。我从书架上抽出青木正儿《中华名物考》,因为我刚从绍兴品尝绍兴酒老酒返回台湾,想弄清花雕酒的由来,于是参考青木先生早年关于中华风俗名物的考证。
青木先生的考证丝毫不枯燥,有趣的很,你读他闲谈花雕酒的文章,从字里行间彷佛可嗅到酒香,看到酣然陶醉的青木先生。
这样轻松自在的文章正好平衡了余华小说给人的铺天盖地的不安和恐惧。青木先生安然地将个人寄托于学术,将个人融入于古典传统——这古典传统不是中国人所独享的,对青木先生而言也是他所共享的文化遗产。弥漫余华小说世界的躁郁不安正来自一种孤独的无依无靠感。
《在细雨中呼喊》(原题《呼喊与细雨》)发表于1990年代之初,写的就是人生活在无边无际的威胁恐惧之中,无依无靠的孤独感受。这是余华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余华早期小说创作的总结和颠峰,其成就颇受评论家肯定,如陈晓明表示:
……我却又不得不认为,《呼喊与细雨》在某种程度上是近几年小说革命的一次全面总结,当然也就是一次历史献祭。这样的作品,标志着一个时期的结束,而不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陈晓明称为这部是余华的绝望之作。日后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几部长篇小说读来虽顺畅舒服多了,但也失去了紧张感,减却了对历史、存在困境的敏锐感受。
表面上来看,《在细雨中呼喊》故事以1960、70年代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为背景,有着家族小说的架构支撑,但余华淡化小说里的历史社会内容,仅剩一个历史轮廓。这部小说其实可说是由几篇中短篇的人物故事拼凑连缀而成,小说人物的境遇主要透过叙事者孙光林“我”个人的心灵而得到反映。
余华写作的兴趣偏于人物内心而非历史现实。洪治纲概括余华等在内的六十年代出生作家,认为他们“从一开始就自觉地撇开了对宏大历史或现实场景的正面书写,自觉地规避了某些重大的社会历史使命感,而代之以明确的个人化视角,着力表现社会历史内部的人性景观,以及个体生命的存在际遇。
”余华关注的正是小说人物饱受屈辱、苦难折磨的过程,他一笔如同一刀,用凌迟的方法细致深入描写人物承受的痛苦,但这种凌迟对写作者又非愉悦,反倒是一种自我凌迟。
以下是我个人阅读余华小说的感触或疑惑,我希望尽量轻松而谈以平衡阅读中的不安。
二、自我凌迟的写作
写作是重新体会他人的苦难,写作之极致则是在写作过程中的自我凌迟。最能展现余华这种倾向是他的暴力写作的颠峰之作〈一九八六年〉,余华叙述故事中的疯子(历史老师)从文革回到八十年代,他最后将各种古代酷刑施加在自己身上。
余华对于疯子自我凌迟的细节描写可说是极其铺张细致,这其中展演的意味浓厚,但也透过这种夸张的展演,余华将读者拉进那一段已经被遗忘的历史,充满血腥暴力的文革历史。对于余华而言,写作并不愉悦,写作更多的是痛苦的重新体验,他自陈1980年代后期写作充满暴力的小说时经常是现实和恶梦交织让自己搞不清生活和梦境的界线。
余华小说充斥人物受苦的故事,他对这类题材似乎情有独钟。关于余华好写苦难,郜元宝曾表是困惑,他说:“我们确实很难断定余华对自己笔下的苦难人生究竟有怎样的想法和感受。事实上,余华越是将人间的苦难铺陈得淋漓尽致,他寄寓其中的苦难意识就越是趋于某种令人费解的缄默与暧昧。
”在铺天盖地的苦难之前,余华的立场的确不清楚,甚至有些暧昧,他回避了一般的政治评断或世俗的道德标准,他反对对人物、对历史进行僵化、概念化的认识。郜元宝认为:
余华的方式,直观地看,就是一种不介入的方式,也就是在苦难人生的呈现过程中拆除我们的文学作品习见的那道理智和道德防线,让苦难以苦难的方式而不是以经过种种包装过的形态,不加节制地呈现出来。这样不仅加强了苦难描写的刺激效果,也使苦难的呈现获得了某种纯粹和透彻。
我想余华面对人间的苦难并非漠然,反之,我们不难看出他对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冷酷深感憎恶、对亲友之间的背叛相残深感愤怒,〈一九八六年〉、《在细雨中呼喊》等诸多作品都对冷眼围观的看客进行批判。余华的不介入是否定、怀疑世俗陈见、道德概念,他摸索一种人与人之间、写作者与被描写的对象之间更深刻的同情共苦的趋同心。
只是余华擅长以荒诞滑稽的笔法叙述,他对人物的博大同情隐藏在可笑的细节之间。近期余华谈到自己的写作时不断强调“痛感”这个关键要素,他说:
这样的感受刻骨铭心,而且在我多年来的写作中如影随行。当他人的疼痛成为我自己的疼痛,我就会真正领悟到什么是人生,什么是写作。我心想,这个世界上可能再也没有比疼痛更容易使人们相互沟通了,因为疼痛感的沟通之路是从人们内心深处延伸出来的。所以,我在本书写下中国的疼痛之时,也写下了自己的疼痛。因为中国的疼痛,也是我个人的疼痛。
我想这是余华最直接表露驱使自己写作的疼痛感受,刻骨铭心的痛感。中国的苦难也是他个人的苦难,余华的写作和现实的苦难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他的小说不仅小说形式的先锋实验,而是将国民性论述包含在其中。这种当代中国的国民性论述,与鲁迅式的启蒙主义国民性论述相似,但还是有明显区别,余华显然不以知识分子、先进的启蒙者自居,他不忍中国人像他小说世界的人物那样活着,但他又要以什么立场来关切批判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