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永中事务所 吕永中:器物与场所精神
我的背景是1986年到上海,然后在同济大学读了设计。1990年留校当了老师,差不多20年。2010年我辞职了,现在的状态就是干点儿自己的事儿。为什么今天谈这个器物跟场所精神呢?当然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新的命题,因为我受的教育是装潢师的设计教育,是德国的一种方式,现代设计某种意义上都是从那儿来的。
但是我在不断的设计跟教学的过程当中,不断反思我们还可以干什么,我们所有的功能都如此完善,我们还缺把椅子吗?我们还缺一个杯子吗?这些命题一直在我脑子里反复问自己,或者说中国还可以干点儿什么?后来我发现一个很重要的命题,我们做的这把椅子它实际上不仅是一个产品,它应该是跟你生活密切相关的一个东西,它跟这个空间会发生关系。
一个非常小的器物它同样具备一个场所的精神,或者一个场所精神它需要若干有次序的、合乎某种道德逻辑的方式去组织,以至于让它的能量更大。
这跟软装陈设也有很多的关系,我觉得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美学问题,一定涉及人心的问题。当你涉及到人心最重要的部分,或者最软化部分的时候,你一定完成了一个系统上的商业的事儿,所以从这个地方来说,人最需要的在当下中国这三十年以来的状态,最需要的是什么东西?其实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命题。
当我们没有安全感的时候,当我们今天不知道吃的什么东西都有问题的时候,当我们碰到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没有诚信的时候,当科技越来越发达,人与人之间没有信任,非常冷漠的时候,我们恰恰需要温暖,需要诚信,需要周边事物给我们带来的能量。
突然觉得说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重新去思考这是把椅子吗。或者这把椅子这个器物除了它的功能以外,它还可以给我们带来什么,如果我们这样去想的话,我们把设计从现代往中国拉一点,可以从古代往当今拉一点。从我们设计师个人的高度可以拉得跟社会的角度近一点。
设计师的工作更多是在翻译
中国人对物的态度它是有天地在的,所以有时候我的工人——木工,我发现他最懂天地之道,他知道木头如何生长,知道如何去选材,知道这个材料会带来什么。比如说形变、音变、伸缩,知道如何跟它去玩。所以我忽然发现,中国的木匠他不是一个简单的工业的生产方式,更多的是在讲究天地之道。
所以我更愿意用物来解释我的东西。所以第二个命题是说我们是在创造一种东西吗?我更感觉我们是在做翻译,或者说我们把这个物给我们的消费者做某种连接,通过这个物的改造,通过这个材料的改造转换成消费者当中所需要的部分东西。
所以我不敢说,我们在创造东西,我觉得只有上帝在做创造,我们只是做一些翻译的工作,我们的周遭,我们的生活环境,我们的过去,设计的所有理念,如果你仔细倾听的话,你会找到它无穷的来源。
另外一点是人跟物之间的关系。我们为什么会去玩一个紫砂壶?我们为什么去玩一块太湖石?实际上那石头单独从材料的运用来说它就是一块废石,根本没法用,做台阶,它还有窟窿。但如果换一个思路,变成另外一些价值存在体的时候,它可能会影响我们精神的层面。
先聊聊半木吧,因为半木到今天差不多八年,其实这次家具展里面也看到我一个朋友,包括去年他们做的一个新的牌子,我也特别开心。我们一帮设计师从不同的层面去阐述当代中国家具应该往哪儿走,我们去探索还有多少种可能性,我们并不是去定义它,我们只是去研究。
半木的核心是这个“半”字,当然它里面藏着木,就是木跟聪慧的意思。所以所有的材料本身是可以转换成人文语汇的,就像江南的园林,或者我们城隍庙的一个建筑,你看那些房子都是勾心斗角的。其实是一个建筑语汇,它表明了一个人的状态。所以我很愿意把这些材料当成另外一个视角去看待它。
第二个问题是“满”跟“半”的关系永远是扯不清的,它直逼了一个核心问题是所谓度的问题。我们有些时候眼前跟长远之前要找到一种平衡,实际上忽然发现中国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在动态当中把握那个度的问题。下面举几个所谓翻译的工作。
1、有形的时间。时间是我们经常会忘掉的东西,空气我们有些时候也会忽略它,当它出了问题的时候,我们才感觉到它的存在。实际上在我们周遭,特别是在中国,我们更在乎那种关系,我们更在乎虚空的一面。那个窗花格带给你的东西,除了格子的图案以外,还重要的是光影。
一个白墙之所以在你的眼中是白墙,是因为那棵树在前面。太阳从东面起来,西面下去,树影也不断地在变动,所以白墙就应该是白的。这是我较早做的一个器物,是有关于时间的我的理解。这个器物很简单,就是一根管子剖了两刀把它通起来,上面12个孔。烟从一个个孔里面随着时间的燃烧的进度好像时间在流逝。所以当你用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似乎感觉到时间的存在。
2、声音。我们说石头会唱歌,木头也会唱歌,万事万物都有它的语言,万物有灵。所以我觉得作为语言转换,就是一块像方方的有点斜角的石头,用木头制成,当中切掉木头让其下凹,这形成一个曲面,木纹随之展开,发生了变化,好像声音从里面可以传出来,这是一个八音盒,非常简单的一个东西。
我想木头确实会说话。我们所有的问题都来源于我们的生活,来源于我们在当下不同地方的不同人的生活,它可以是一个很宏观的事儿,它也可以是一个很微观的事儿。而这些未被咀嚼的,隐藏在生活当中的东西,往往成为我最关注的点。
3、光阴的虚度。有些时候我们真的需要停顿一下,需要虚度一点,也许我们会找到一个更大的天空。2007年我去了安徽的一个金寨的贫困县,一个业主说要去买一个岛,造一个会所,他为什么会买这个岛呢?就是前因后果都有,所有的事物都有因果的,因为他原来是部队里做通讯兵的,是有点文化的人,后来到了上海以后,他从商搞装修。
这么动荡的差不多在上海待了十几年,我想起他是从金寨那里出来的,那个乡愁勾着他。所以有的时候乡愁会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因子,乡愁不是简单的逃避,而是另外一种情结,跟他的人生阅历也有关系。
所以他回去要买一个岛,说接待朋友。我跟他回去了以后,发现那个岛不能买。那天晚上我跟他说,别买岛了,那边有片湖,我们就造艘船吧。
我们造艘船,我们不就是来这儿放松的吗。所以这艘船并不是说这个船一定要到什么地方去,因为当下的中国,当下的状态我们永远是说我们要去那个地方,赶快用什么地方,用什么手段我们到达那个地方,这就是我们无法享受这个过程的最重要的原因。所以我说这艘船,它的任务叫漂,它不需要去一个确定的目的地。
我做了这么一个方案,就辟了一座茶室,非常简单的一个东西。然后这个里面的功能是可以转换的,我按照一天的时间早上是干什么,中午干什么,傍晚干什么,深夜干什么。然后我觉得这样一天的时间里面,希望他能感觉到这个时间的流逝。
甚至我希望是说,这个东西给他带来的是若干年以后他一直在想念这个东西,就是把这个“因”能种到他的脑子里面去。所以他可以坐在边上,当然因为那边湖域是一个水库,特别安静,没有风浪,基本上是用一个小的建筑来造的。
但是这个方案最后没有实现,设计这个东西已是5年之前了。每次我碰到很多人,他们都问我,这个东西造了没有。有一次一个朋友说我有一个水域在阳澄湖,能不能把这个东西造过去。我说还不是它最佳表现的地方,因为在阳澄湖上我们肯定喝着黄酒,吃着螃蟹什么的,我觉得不需要这样一个东西。
那怎么办呢?回来以后我做了另外一个产品,就是这个扁舟可以做成一个凳子的东西。我想没关系,我就做一个家具吧。做船也好,做家具也好,做空间也好,它是承载我们一定的内容,不一定要做这个东西,也可以用另外的东西去表现它遵循的属性。
所以钢跟木是有关系的,金木是有关系的。钢通常给人以强壮的感觉,让人联想到力量、钢筋水泥,但它也可以非常的柔软,当然这个柔软里面是存在着力量,就像水一样,水可以很柔软,也可以很刚。
上面一片木头是扁舟的意思,用了一点榫卯的结构拉住它,然后不同的两边因为是一个曲面,它的弹性表达出来了,所以有些时候你看一个场可能就跟微妙的一个指向有关系,跟一个比例有关系,跟一个材料有关系,跟它所放置的空间有关系。
另一个命题是记忆
另外一个命题是记忆,这个是因为都市的发展,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逃不过这么一个进程,这个进程给我们带来很多哀怨,带来很多不如意,但恰恰是这些不如意帮助我们寻找更好的方式。年纪大一点会多想起记忆的事儿,在国外也有人专门设计这个命题,就是记忆。
古徽州是我经常喜欢去的地方,当然离上海也比较近。这个天井院落,还有那点筋骨,还有那个气质,我觉得它正正好是我们那种都市里面所缺乏的。我比较过南方的安徽的古徽州跟北方的山西大院,作为中国古建里面特别有代表新的民居的房子。
做过一个演讲叫中国古代被动式环保,我就比较它跟土地有关,跟这个状态有关。历史会不断的重复,相信我们习主席上台以后,或者说执政以后,他会推崇的东西跟之前十年、二十年会不一样,大家一定要把握这个方向。
有一次有一个品牌,马爹利的一个名士品牌来上海说我拍我,因为我上海待了二十几年,我说你要在上海拍我,我说那要离开上海才能拍出上海。他不明白,我说必须要离开上海,我们找到一点我们能够未来为上海解决的一个方向,来拍上海才有意义。
后来我们去了古徽州,他说为什么。我说你看古徽州那个年代,大家都知道徽商那个年代,他们的土地很贫乏,所以外出打工对他们古徽州来说,就是出国,就到处打天下。中国也一样,中国前三十年都干这事儿,开放、工作、打天下。
好了以后他们回了家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叫光宗耀祖。我觉得我们中国很多经历过一段时间的人也会干这个事,在南京其实我有一个项目,有一个人造一个别墅,六千平方。我说要这么大干什么?他说我希望这个房子世世代代传下去。
我说什么叫世世代代传下去?是用很好的材料吗?是用很贵的东西吗?其实我们后来讨论下来的时候,他对家具不是使用的概念,回到的还是中国人的传统观——光宗耀祖,所以他们重新建房子,不惜工本,所以他们造了很多祠堂。
第二个是什么呢?重文兴教,就是还是要有文化,所以他们造了很多私塾,考了很多状元。这是中国儒家的那套东西,在我们的文化大革命也好,在我们这一百多年不断的努力当中,我们其实已经丢掉了,我们到了一百多年以后,突然意识到我们需要的时候,已经找不到了,但会有那么一个记忆。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设计,比例也就是1:2这样的一个关系。它浓缩了一个书院的感觉,它的功能是模糊的,它可以放书,也可以置物。因为当我们在不断向现代主义行进过程当中,我们不断地去精确一些东西,我们忘了我们实际上很多东西是因势而变的。
刚刚看见一个盒子,当你能动的时候它会变掉,每个格子之间有气场可以穿越。然后放的东西也可以随着自己的成长而放,这个我觉得是半木最重要的核心,是如何找到控制那个度,控制那个东西以后,以至于它产生更多的可能性。
其实我也做了一张桌子,这个桌子很简单,为什么外面是方的直线呢?我后来想直线跟曲线的最大的本意是什么?或者格子的本意是什么?那是规矩。谁要规矩?社会要不要规矩?社会要,我们的心里就可以给它做规矩。所以这张桌子外面是方方的,下面从腿部一直到桌面这个横梁一刀把它斜过来。
我又把它变成了一张台子,而这张台子现在是非常受欢迎的一张台子,我把它叫大班台。当然它就是一个工作的地方,工作的状态一定会发生变化,今天我们这样的交流可以说是一种工作,我们在一个咖啡厅坐在那个地方对文学家来说就是个工作,不一定在工作台上,不一定在这个定势上,它需要的是功能,可能不需要那么多的文件,因为我们有了电脑,所以它给我们设计带来一些可能性的空间。
由此一点点东西,一个方跟圆,方圆的理解对我来说,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什么事,一个符号。因为方我觉得是代表了规矩,圆代表的是另外一个天空,圆代表的是某种逻辑。所以有时候说这个老外有点儿方头方脑的,谈得死,规矩很多,说中国人特别圆滑。
但是如果只有规矩,圆滑是因时而动,随着时间的变化去相应调整。所以这一款有一个概念我们把它做成了另一个家具,它自成了一个体系。4个抽屉可以打开,前面这2个抽屉是一个箱子,左面是一个箱子,右面是一个抽屉,箱子跟抽屉一大一小,一轻一重它像秤砣式的平衡,有的时候我们永远突破不了这种所谓对称的方式,我们都是那样一个平衡,为什么?难道是完全均衡的吗,不可以找到一种秤砣式的平衡吗?后面有两个暗藏的抽屉,这两个抽屉是因这结构况且形式而定的,所以它不易被发现,我觉得我们需要有一份自己的空间,每个人心里都要有。
前面可能是为了应付某种工作,但后面完全可以对着自己的世界。
我的空间做的方式通常比较简单,因为我觉得我们从人的角度,回到人的角度来想的话,我们今天来第一我们是穿着衣服,第二跟我们周边的家具更近,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去读懂那些诗人、文学家他们写的一些小说、诗歌里面,他们经常会谈到器物,他们不把它当成一个简单的用具,他们更觉得这些器物陪伴着他。
然后第三部分才是空间,所以我想能不能从离你最近的,最经常用的,再到大的。所以如果从这个思维里面去看,可能就牵扯到很多很微妙的东西,或者说有些时候这个器物摆在你面前的时候,它会修整你的关系。
所以这种我认为是器物给我带来的一个场所的内容。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再仔细想想,宇宙是什么构成的?我觉得是因为再造了空间场而构成的。从无限大来说,比如说我们现在认同一个理论叫宇宙大爆炸,宇宙大爆炸拉出了这些东西的关系,谁跟谁动,再回到最微小、原子、电子也是一个宇宙,也是拉出了一个关系。
如果我们一直从这个思维去想很多问题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们的水泥地板能不能多造一点空,让它可以呼吸,呼吸的目的是让蚂蚁的宇宙不要失掉。
蚂蚁来说那个小的挑起来的部分,那个天地它还能存在。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造物,我们在设计,我们在创造的时候,我们需要深刻地或者说尝试以言简的方式去想一想这个是什么、为什么。我们对照我们的历史也要这样去以科学的精神,用一种求证的精神、思辨的精神去探索一下,我们不可能盲目地去相信什么。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前一段时间我从一个信息里面看到说,我们古代描述的恢弘的阿房宫实际上是没有造起来过,不是一把大火烧掉的。当然这个是不是准确我不知道,它的说法是基础是在,那个时间都在,但是从这片区域里面没有测到一点点炭或者说被烧毁的痕迹。
如果是一把火烧了这么大规模的话,这个土壤里面一定会有这个痕迹。所以对待历史,对于我们周边的事物,我们能不能不从一个制式的角度,能不能从个体的体验角度,去分析、思辨去尝试找到我们的态度跟方式。
若干这样的个体,若干这样的方式一定会建构一个新的视角。我跟易中天很熟,我跟他经常聊很多事儿,我们有一个共同点是我们永远去格服的东西,古代说“格物致知”,或者“格物造物”,如果一个造物者不尝试用格物精神的话如何造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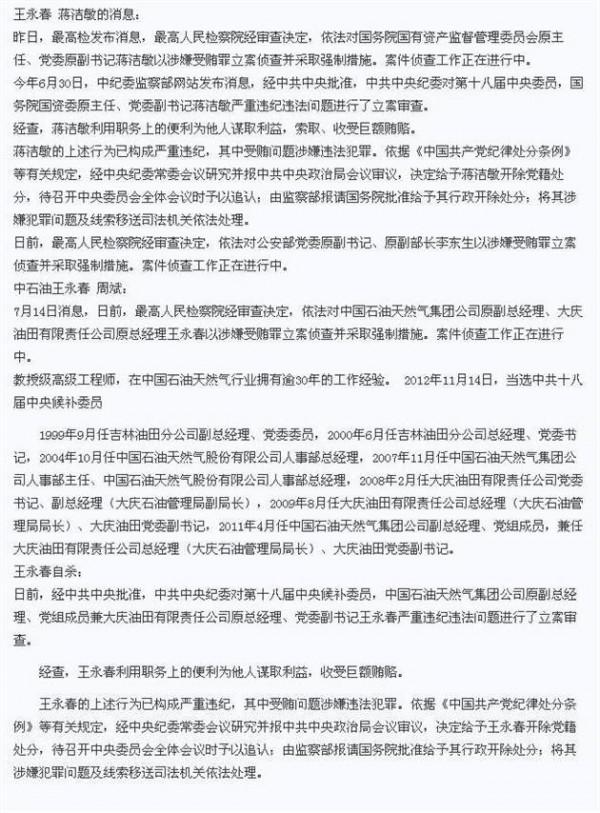


![>王永春什么级别干部 [股市360]中石油王永春被调查 级别在内部排名第五位](https://pic.bilezu.com/upload/d/ad/dadaf914c57affd31c27f0a8038041f1_thumb.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