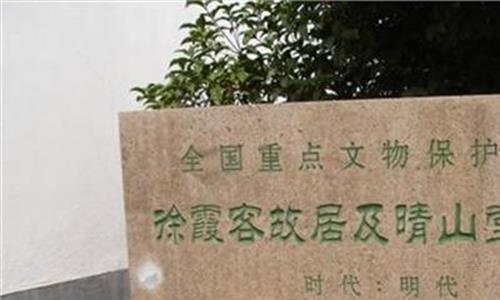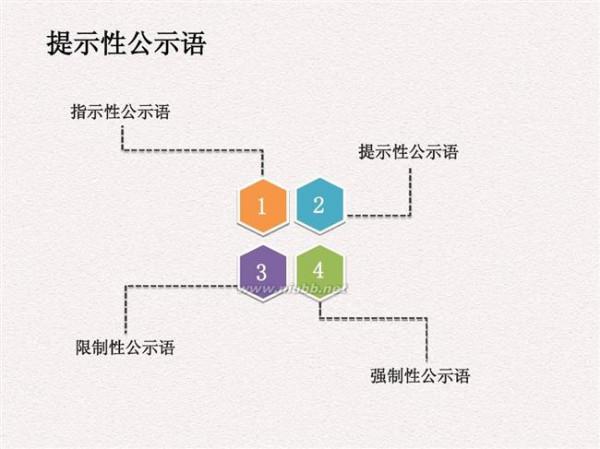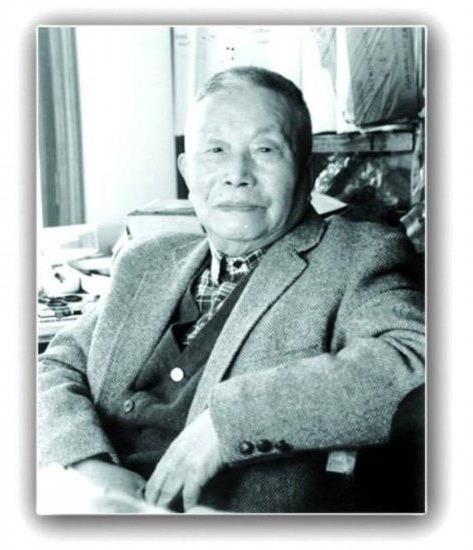林琴南尊师文言文翻译 林琴南:不识一句外文的中国翻译第一人(组图)
林少华还说他曾看到钱钟书对林琴南作出过这样的评价,“现在人都讲究翻译得要准确,但我宁可看林琴南这种翻译得不准确的,他的东西看了很有意思。别人翻译得很准确,但读起来很无趣。”
他的译作滋养了鲁迅、郭沫若、矛盾等新文人
他翻译外国小说,并不拘于原小说的格局与传统,而是将西方的创作方法、写作技巧、文学理念,统统渗透进中国小说的创作中
1901年夏,即译本《巴黎茶花女遗事》问世后两年,林琴南的忘年交魏易兴冲冲地叩开了林琴南的家门,手里举着一本书:“畏庐兄,近来得到美国斯土活氏所著的《黑奴吁天录》,心中怒涛汹涌。”随后魏易向林琴南介绍了书的故事概况,对于“汤姆叔叔的小屋”这个故事,林琴南当即表示愿意与魏易合作译书。
经过连续多日的奋战,他们将这本《黑奴吁天录》从英文变成了中国的古文。同年该书的译本以“武林魏氏”这一译者名发行。在日本求学的鲁迅,于1904年收到友人寄来的中文版《黑奴吁天录》,一气读后感慨万端:“漫思故国,来日方长,载悲黑奴前车如是,弥益感喟。
”20世纪初的东京,《黑奴吁天录》被改编为话剧,一群热血的中国留日学生,在异国的舞台上演出。
此后,林琴南对外国文学的翻译热情一发不可收拾:法国阿尔弗雷德·富耶夫人以笔名沛那著的《爱国二童子传》;英国狄更斯的《块肉余生记》(现译为《大卫.科波菲尔》);《伊索寓言》、《美洲童子万里寻亲记》、《迦茵小传》、《撒克逊劫后英雄略》、《斐洲烟火愁城录》……由林琴南翻译的外国作品数量之巨,质量之高,影响之大,在中国堪称第一。
而他翻译外国小说,并不拘于原小说的格局与传统,而是将西方的创作方法、写作技巧、文学理念,统统渗透进中国小说的创作中,滋养了新一代文学大师,如鲁迅、郭沫若、茅盾、郑振铎等人,可以说林琴南对中国新文学的促进居功至伟。
林琴南不仅是评介外国作品的先驱,本身还是一个擅用文言文写小说的中国作家。辛亥革命后,林琴南创作了第一部长篇小说《京华碧血录》。而后又有长篇小说《金陵秋》、《劫外昙花》、《冤海灵光》、《巾帼阳秋》等,或写清初历史,或写清末民初的时局。《金陵秋》和《巾帼阳秋》这两部小说和《京华碧血录》放到一块,简直就是一部清末民初史。
不读书,则入棺
林琴南的文学造诣并不是如传说的那样因为天赋异禀而得来,一直以来他都是一个非常刻苦的人。虽家境贫寒,但林自幼嗜书如命,5岁时就在私塾当一名旁听生,受孰师薛则柯的影响,深爱中国传统文学,从此与文学结下不解之缘。
后终日为生计奔波之时,他也不忘苦读诗书,13岁至20岁期间校阅残烂古籍不下两千余卷。因为买不起书,他只好向友人借阅,为了“留下”这本借来的书,他就自己一字一字地抄下书里的内容,待日后可以细细再读。他曾在居室的墙上画了一口棺材,旁边写道:“读书则生,不则入棺。”这奇怪的“棺”铭,就是林琴南激励自己发愤苦学的座右铭。
对于读书,他还有一套自己独特的方法“抬头不见低头见”。 坐着,拿起桌上的一本书,闭上眼,随意翻一页,指一个地方,睁开眼瞄一下所指的段落,然后就背出上下文他要求自己对课文熟悉到这个程度。如果从书中寻章摘句挑出一二,问他出处,他也能答上来,又往往上串下连将整段背诵,如流水喷涌;看了文章,他将词汇整理归类,数数全篇用了多少好词佳句,然后掩卷思考,细细琢磨,加以领会。
儿童少年时养成的严谨的治学态度、良好的学习习性,使林琴南终身受益,也是他成为一代大学者的坚实基础。
但由于长久的积劳,别人18岁的大好年华,到了林琴南这儿竟成为了肺病患者,连续十年咳血不止。但他卧病在床期间还坚持刻苦攻读。到22岁时,已读了古书2000多卷,30岁时,读的书已达1万多卷了。
以寡敌众力挺古文,
沦落为新文化殉葬品
伊始:让古文与白话文并存是林琴南的真正观点
林琴南这位在文学和翻译史上都名留青史的人物,却因为一场论战成为了一个颇受争议的人物。
1915年,由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受西方先进思想的影响,高举起科学与民主的旗帜,而要将西方崭新的思想介绍给国人,就必须有适于表情达意的语言形式。1917年初,《新青年》相继发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提倡白话文和新文学,反对载封建之道的文言文和旧文学。当时,许多坚持旧文学观念或坚持使用文言文的人都三缄其口,唯独林琴南心直口快,不假思索就披挂上阵,与之争锋。
他作《论古文之不当废》一文,对胡适、陈独秀之文加以反驳。“知腊丁不可废,则马班韩柳亦有其不宜废者。吾识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此嗜古之痼也。”林琴南认为要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无论如何是不能废弃古文的,难道反对旧思想就必须抛弃古文?
但就当时的情势来说,已经极为落后的中国,要迎合世界潮流,接纳先进文明的东西,必须对一切旧文化(包括语言在内)重新审视、评价。其实,让古文与白话文并存是林琴南的真正观点。在苦心孤诣钻研古文的同时,林琴南早就着手推行白话文了,1897年,他创作的《闽中新乐府》,即是用白话写童谣的尝试;后来,林白水办的《杭州白话诗报》等,也发表过林琴南的通俗白话体歌谣。
升级:一场“双簧戏”
争辩伊始,林琴南态度还比较温和,论战波澜不惊。到了中期,按捺不住的两位青年钱玄同和刘半农,终于以《文学革命之反响》为题,演出一场“双簧戏”。1918年3月,钱玄同托名王敬轩,在《新青年》发表《给新青年编者的一封信》假旧文学的卫道士面目出现,发表了一通鄙视贬低白话文学的议论,而故意把林琴南推为反对派的领袖。
很快地,刘半农以《新青年》记者的身份发表《复王敬轩书》,抽丝剥茧地把对方驳斥批判了一通。文章故意讥林琴南的古文为不通之文,将林琴南归为桐城谬种,捎带把林琴南译的小说也挑出许多毛病来嘲笑一通。
林琴南果然上当,心中无名火陡起,着手反击。1919年2月4日,设在上海的《新申报》特辟“蠡叟丛谈”专栏,发表林琴南的文言短篇小说。2月17日至18日、3月18日至22日,《荆生》、《妖梦》相继抛出,影射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及新文化大本营北大,并对白话文进行了尖酸刻薄的嘲讽。李大钊随即以守常为笔名,在《晨报》发表《新旧思潮之激战》,对林琴南进行毫不留情的讨伐。
林琴南一边写下《劝世白话新乐府》,一边继续撰写与新文化运动针锋相对的文章,在4月5日的《公言报》发表《腐解》一文,阐明了自己的立场。而他的一系列文章,引来了新文化运动倡导者更猛烈的抨击。
结局:口众我寡,沦为倒退复古人物
陈独秀的《林纾的留声机》、《婢学夫人》,鲁迅的《现在的屠杀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杂文,从不同角度对林琴南的观点进行了义正词严的驳斥。在强大的火力面前,孤身作战的林琴南似乎招架不住了。1919年4月,《文艺丛报》发表了林琴南的《论古文白话之消长》,承认“然今日斥白话家为不通,而白话家决不之服。
明知口众我寡,不必再辩,且古文一道,曲高而和少,宜宗白话者之不能知也”。虽倔强如他依坚持:“文字须有根底,即谓古文者,白话之根底,无古文,安有白话?”但文章的最后写下了这么一段话:“吾辈已老,不能为正其非,悠悠百年,自有能辨之者,请诸君拭目俟之。”如此的结束语凄婉而又无奈。
不久,五四运动爆发,新文化运动的潮流摧枯拉朽,势不可挡。不合时宜的坚持,不合时宜的言论,使最早尝试用白话写新乐府的林琴南一下子沦为大家心中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倒退复古人物。林琴南成为了一个旧文化终结的可悲人物,又是新文化发端的殉葬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