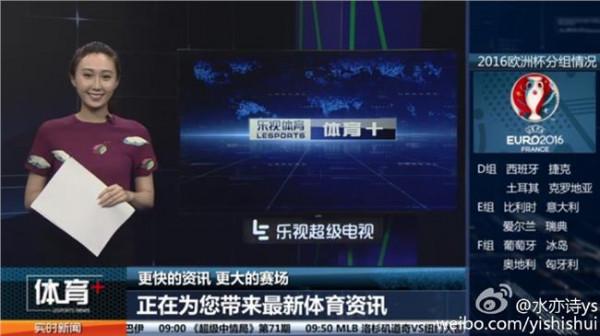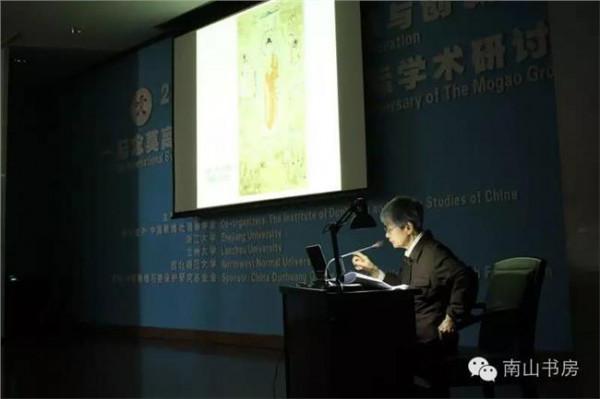樊锦诗儿子 敦煌女儿樊锦诗:守望祖先遗产让快乐遗憾交织
“敦,大地之意,煌,繁盛也。”(《汉书·地理志》)敦煌,位于甘肃省西部偏南,前有阳关,后有玉门,南枕祁连,襟带西域,是古丝绸之路的咽喉。
20世纪40年代,被誉为“敦煌艺术保护神”的常书鸿来到饱受创伤的敦煌莫高窟,在 -->异常艰苦的条件下成立了敦煌艺术研究所(1984年扩建为敦煌研究院),对莫高窟进行清理和保护。随后来了段文杰。然后又来了一个有些腼腆的柔弱女子——樊锦诗。
初入敦煌
1963年夏天,一个瘦弱的年轻女子在北京火车站背着大大的背包,头戴草帽,满怀理想,整装待发。她就是樊锦诗,那一年她25岁。不久后,敦煌研究院以她为原形,制作了一个雕像,取名《青春》。
樊锦诗1938年出生在北京,成长于上海,1958年考入北京大学考古系。见识了大城市的繁华与江南的旖旎,当时的樊锦诗根本不会想到自己会到戈壁沙漠工作,更不会想到自己一去就是41年。
回忆起当时的抉择,樊锦诗把它归因于一次“偶然”。“1963年,我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的时候,报效祖国、服从分配、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等都是影响青年人人生走向的主流价值观。1962年,经学校安排,我和3名同学曾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实习,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毕业时,研究所去学校协商要人,我们4个实习生全要。学校当时只答应给两个,我是其中之一。”
还有一个因素促使樊锦诗来到了西部,那就是常书鸿的精神。“当时《人民文学》有一篇作品,叫《祁连山下》,写的就是常书鸿。我觉得这个人太了不起了,他留法,喝的洋墨水,回来当教授,他居然把教授放弃了,把大城市生活放弃了,去保护这么一份遗产。我又看了精美的壁画,所以我有了深深的印象。”
实习结束时,她是拖着病躯回到北京的,父母非常心疼。在毕业分配的时候,她父亲还为此专门给学校写了一封信,但是这封信被樊锦诗扣了下来。
回忆起当年的这一举动,樊锦诗哈哈一笑:“那还有啥可说的呢?一个有事业心和责任感的女大学生,碰上一个思想纯粹的年代,最终的结果只能是扛起铺盖卷儿,义无返顾地上路。”
虽说对大西北恶劣的自然环境早有心理准备,但当她真正住进莫高窟旁边的破庙里之后,才确切地知道了什么叫“反差”。首先交通就很不便利,樊锦诗清晰地记得当初他们从敦煌到莫高窟的情景,他们在敦煌东大桥花了好大工夫才拦截一辆过路车,让其顺路捎带一截。那时候敦煌保护研究所只有一部手摇电话,通讯困难。晚上只能用蜡烛或手电照明,上趟厕所都要跑好远的路。
“本来以为,敦煌那么漂亮一个地方,肯定是窗明几净,那些专家们肯定都很气派。结果都穿着一身干部服,洗得淡淡的,一个一个都跟土老帽似的。”樊锦诗很坦诚:“说没有犹豫动摇,那是假话。和北京相比,简直就不是一个世界,到处是苍凉的黄沙。”
“当时我只是名个子不高,敏感而细腻的女孩子。”半夜里,当房梁上的老鼠吱吱叫着掉在被子上时,当因为水土不服整天病恹恹的时候,樊锦诗望着透过窗纸的月光,还是掉了泪。但她平静下来后,又想,反正还年轻,还能在这里呆一辈子?有机会再调出去不迟嘛。
但每走过一个石窟,都会使她惊叹:“哎呀,太好了,太美了!”前辈们的执着以及锲而不舍的精神也令她非常钦佩,“常书鸿、段文杰先生已经在这里呆了漫长的20多年,无法想像,是一种什么力量在支撑着他们,又是什么力量,把研究所的其他五六十名职工吸引到了这里?”
3年后,“文革”开始,整个“文革”期间不可能谈调动的事情。“文革”后,岁月倏忽,人已中年。这时候,要走的话纯粹就是为了孩子,为了家庭。但女人又是异常感性的,“十几年磨合,我早已习惯了大西北,爱上了莫高窟,把研究石窟保护石窟当成了一份终生的事业。”因为丈夫支持,她留下了,直到青丝变成华发。
愧对家庭
樊锦诗和丈夫彭金章是大学同学,在学校谈的恋爱,她笑着回忆道:“在当时,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挺酷的。”彭金章家在河北农村,毕业后被分到武汉大学,于是两人只好千里鸿雁传书,遥寄相思。他们1966年结婚,两地分居19年。
她每隔一两年会回去看望爱人孩子一次,“表现表现,给他们做点好吃的”。
“1986年,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最终我先生妥协。”由甘肃省委省政府出面,把彭金章调到敦煌研究院。“应该说是我先生下的决心。他一直希望我到大城市去,起码是为了孩子,受教育也是去大城市好,但是他可能也看出来了,我粘粘糊糊没走,是因为我实在喜欢这里。”
那时的彭金章在武汉大学也创了一番事业,创办了一个专业,还负责系里的一些工作。“可是最后他把这些全都丢了,大概也是为了我吧。”樊锦诗对丈夫的理解与支持深为感动,“我先生是少有的好丈夫!真是打着灯笼也难找啊!”
她认为自己在家庭和事业的两难选择上,更倾向于家庭,“如果说爱人不支持我,那我肯定就要走了,肯定离开敦煌了,我还没伟大到为了敦煌不要家、不要孩子。我不是那种人。”
尽管樊锦诗的同事说她是少有柔情的人,但她说起孩子时依然充满慈祥与母爱:“我至今对这个家怀有深深的歉疚,尤其是对孩子。”
彭金章回忆说,“大儿子出生在1968年底,当时敦煌条件太差,就准备到武汉去生,樊锦诗的母亲、姐姐,准备了很多用品,什么奶嘴、奶瓶、奶粉,什么小孩衣服、尿布等。我的母亲,从河北农村,准备了红枣、小米,鸡蛋等等,很多东西,也到了武汉,等着她过来呢。”
可是,樊锦诗却因为工作不能离开敦煌,彭金章只好挑着东西反复倒车,等他到了敦煌,孩子已经出生一个星期了,光着个屁股什么都没穿。
过完产假后,樊锦诗照常上班,孩子没人照顾,就把他锁在屋子里。“屎尿什么的都弄在一起了,有时嘴上都抹着屎,他妈妈回来以后,还在那里笑呢。”彭金章说。
大儿子的学习“一直够呛”。樊锦诗自责道;“我只能责怪自己。”
他们有两个孩子,老二小时候生活在河北农村,5岁时,樊锦诗把他接到敦煌,两年后又把他送到上海的姐姐家。但孩子性格孤僻,沉默寡言,在亲戚家并不适应。她只好把孩子送到武汉,后来孩子又随父亲到了兰州。由于从小缺乏母爱,又内向倔强,这让他在兰州一中始终与同学没法好好相处。
樊锦诗时常在心里念叨:“对不起呀,孩子们,妈妈守着莫高窟,你们只能守着孤独。”
守望莫高窟
“莫高窟几乎所有洞窟都不同程度存在着病害。”樊锦诗从踏上敦煌土地的第一天起就意识到了这一点。1998年,已经60岁的樊锦诗从前任段文杰手中接过重担,成为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长。“这是整个世界的宝藏,担子交在我身上是很重,我知道自己的能力和分量,但是我不能退缩。”
她上任不久就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情:1998年左右,全国掀起“打造跨地区旅游上市公司”热潮,有关部门要将莫高窟捆绑上市。当时樊锦诗坚决不同意,“硬是把压力都顶了回去”。现在说起来,樊锦诗还是坚持当时的立场,“文物保护是很复杂的事情,不是谁想做就可以做的,不是我樊锦诗不想让,你要是做不好,把这份文化遗产毁了怎么办?全世界再没有第二个莫高窟了。”
她觉得自己有责任保护好祖先的遗产,“如果莫高窟被破坏了,那我就是历史的罪人。”
“现在的敦煌,连种蔬菜的农民都会感觉到旅游的重要性。”敦煌市旅游局局长龚瑛强调旅游业已经深刻触及到了敦煌的每个角落。而樊锦诗与敦煌市民“希望游客越多越好”的想法恰恰相反。
樊锦诗非常矛盾,“我觉得敦煌作为世界独一无二的遗产,我们应该给大家服务好,给他们看。可是这些洞窟最少600年,最多有1600年,而且这些壁画是用泥巴在石头上涂的,经过这么长的时间,你说它还经得起过多的参观吗?”
樊锦诗的担心是有确凿根据的。“我们找到同样地方1908年的照片和2002年的照片进行对比,不看还好,看了之后就觉得担心,本来很清晰的但现在有点模糊,有的地方就起斑驳了。”这给她一个警示:敦煌在不知不觉中老去。
研究院曾做过测验,检测数据表明:40个人进入洞窟参观半小时,洞窟内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就会升高5倍,空气相对湿度上升10%,空气温度升高4摄氏度。在这些因素作用下,会加速壁画产生酥碱、变色、霉菌等多种病害。
文物保护越做越难,樊锦诗经常会踯躅在一个个精美的洞窟外,不停地问自己:究竟怎么样才能保护好莫高窟?
为了保护莫高窟文物和缓解游客过多给壁画、彩塑带来的影响,敦煌研究院在2003年初开始筹建多功能、具有国际水准的莫高窟游客服务中心。樊锦诗认为,“建设莫高窟游客服务中心的提案,就是为了在保护的前提下实现最合理的有续利用。”
敦煌莫高窟目前还使用传统的由讲解员直接带游客进入洞窟参观的导游方式,这给本已十分脆弱的壁画、彩塑带来了潜在的威胁。
建成后的游客服务中心将由影视演播厅、洞窟虚拟漫游厅、展示陈列厅等设施组成,在未进入洞窟之前,游客首先可以直接通过影视画面、虚拟漫游、文物展示等,全面了解到敦煌莫高窟人文风貌、历史背景、洞窟构成等,然后再由专业导游带入洞窟做进一步地实地参观。“这样做不仅让游客在较短的时间内了解了更多、更详细的文化信息,而且极大地缓解了游客过分集中给莫高窟保护带来的巨大压力”。
樊锦诗另外一个大胆构想是建立“数字敦煌”。在2003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樊锦诗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提交了一份《关于敦煌莫高窟保护利用设施建设》的提案。
樊锦诗这样对《时代人物周报》解释她提出的概念:“准确地说,数字敦煌有两层含义,一是将数字技术引入敦煌遗产保护,将洞窟、壁画、彩塑及与敦煌相关的一切文物加工成高智能数字图像;二是将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献、研究成果、相关资料,通过数字处理,汇集成电子档案。”
“壁画这个文物不可再生,也不能永生啊。另外一个它要退化怎么办?”这促使樊锦诗考虑要抓数字化,永久保存敦煌信息。
樊锦诗对促进敦煌文物的保护事业做出的贡献,得到了学界的一致认可。学术大师季羡林在2000年敦煌百年庆典上极力称赞樊锦诗,他用了一个词:功德无量。
渴望回归
为了汇融着千年文明的492个洞窟,樊锦诗的一生活得像一张拉满的弓。她永远有操不完的心。人才引进,学术交流,设施建设,人事统筹等等让她一刻也不得闲。
岁月的磨砺以及西北广袤天地的锻炼,樊锦诗的性格变得坚韧而执着。年轻时的樊锦诗是个内向沉默的人,“上台说不出话,照相的时候就往边站”。但现在的她说话直来直去,在风沙中大声与人争论着,“很多事情逼着你,就是非常的急,急了以后就会跟人去争了。”
她苦笑着说,她的“严厉”和“不近人情”就是因此出了名的。由于工作雷厉风行,说话单刀直入,有人在背地里骂她“死老太婆”。人都走光了的深夜,她常常独自在办公室紧锁双眉来回踱步,慢慢吞咽那些尖利刺耳的话。
她说,将来我滚蛋下台的时候,大伙能说“这老太婆还为敦煌做了点实事”,我就大大满足了。
樊锦诗是个渴望平凡与温馨的女人,内心深处有着单纯的梦想,在交际场上,她往往左支右绌。“不怕你见笑,以前,我连搓手指这个动作表示给人送钱都不知道,现在我终于明白了,这叫处世哲学,人情练达即文章。”
为了莫高窟及其研究机构的发展,她在激烈的心理碰撞中,逼着自己学会“适应”。如今,她不仅知道“搓手指”这个动作的含义,还懂得了抓大放小、能屈能伸。她无奈地请客吃饭,陪自己讨厌的人聊天。她说,这样做必须以对莫高窟有益无害为前提。
她这41年,一直回味咀嚼着一种令人热血沸腾的精神,这种精神来自于莫高窟里跃动着的震撼人心的民族创造力和自信心,来自于一个人和一项事业长期血脉相连患难与共的情怀,更来自于莫高窟的先期守护者常书鸿、段文杰等一大批赤胆忠心的学者、艺术家鞠躬尽瘁的榜样力量。在大漠边陲,在这种不可思议的精神呵护下,从上世纪40年代初开始,满目疮痍的敦煌莫高窟,度过了安稳幸福的60年。今天,它早已巍峨耸立,游人如织。
在这60年的守护中,一个坚持了41年的女学者,也将拖着她疲倦的身躯,走向幕后。在僻远恶劣的大西北度过了青春年华,她打算退休后叶落归根,重回故乡上海。
如果明天就能退休,她说:我将高高兴兴卷铺盖走人。她惟一的希望是,“啥时候再来敦煌,还会有人微笑着请我吃顿饭。”
配文
敦煌:璀璨的明珠
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一位禅僧在距敦煌25公里处的鸣沙山东麓断岩上,开凿了第一个洞窟,此后开窟造像的僧人络绎不绝,一直延续了千余年,这就是后来举世闻名的敦煌莫高窟。它以其举世无双的石窟艺术、藏经文物成为人类最伟大、最辉煌的历史文化遗产之一,被称为“中国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古代学术的海洋”。
至今保存在编的洞窟仍有492个,彩塑2415尊,壁画45000多平方米。敦煌莫高窟在1987年12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这一璀璨的艺术明珠在一千多年的岁月长河中历经兵燹,随着古丝绸之路的日趋没落,敦煌莫高窟静静地沉睡在朔风凛冽的山麓。20世纪初叶,一批批外国探险家、考古家找到了这里,并在这里大肆劫掠与破坏,使莫高窟遭到了自建成以来最大的损失。据悉,敦煌5万件文物中,有近4万件流失在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