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启泉课程改革 钟启泉:课程改革要突破“三个瓶颈”
钟启泉,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所长,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所长,课程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比较教育研究会会长。
教育周刊:我国当前开展的第八次课程改革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有声音说:课程改革目前正面临着种种困惑,甚至有举步维艰的感觉。对此您怎么看?是什么诱发了这些问题呢?
钟启泉:在我看来,下面三个瓶颈导致了当前课程改革的种种困惑,需要抓紧解决。第一个瓶颈,高考制度滞后。尽管教育部已经明确了改革方向——“下放、多样、扩大大学自主招生权”,但至今缺乏一个强有力的研究班子来具体地落实这些原则。
中国的教育人口庞大,加上应试教育积重难返,如果缺乏指导性的、具体的操作规程的研究,那么,学科教学改革和综合实践活动难以推进,普通高中的课程改革可能崩溃。而高中课程改革一旦崩溃,会影响到初中、小学,导致应试教育全面复辟。
第二个瓶颈,教育立法滞后。《义务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教育法制不到位。义务教育的要件是如下四个义务:就学义务、办学义务、就学保障义务、规避义务,原则上不分种族、性别、社会身份、经济地位,以所有儿童为对象实行免费教育。
现行的义务教育在实践中尚不够完善,因此,修订《义务教育法》等教育法规乃是理所当然的。第三个瓶颈,教师研究滞后。在新课程实施中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教师即课程”。
但要把这个口号化成每一个教师的专业成长,需要改变教师被研究的状态。“作为研究者的教师”是当今国际教育界新出现的一个热潮,越来越多的教育学者和一线中小学教师以各种形式积极从事教育教学研究,包括“教育叙事”、“教学研究”“行动研究”,等等。我国缺乏教师研究的积累,如何帮助教师转换角色是我们面临的严峻课题。
教育周刊:要突破这三个瓶颈似乎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在长年积累下来的诸多问题面前,什么才是课程改革关键的“突破口”呢?
钟启泉:我国的教育发展缺乏资金、人员、技术,但更缺的是思维方式的变革。课程改革的前提和关键,就在于变革思维方式,重建话语系统。长期以来,我国基础教育课程的发展,在课程规划、基础理论、课堂教学等方面,占主导地位的都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
在课程规划方面,我国以往缺乏“课程意识”,把课程理解为少数人研制、多数人被动实施的过程,造成了分科主义课程的格局。这次课程改革则迈开了回归专业的第一步。从纲要文本来看,体现了国际教育界倡导的教育发展的基本准则——“国际视野”与“本土行动”。
“国际视野”与“本土行动”原本不是二元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不汲取先人的成就,缺乏国际视野,理论和行动就不可能有高度。我们在思考教育问题的时候,需要兼顾两个维度——“现实维度”与“未来维度”,这两个维度也不是二元对立的。我们需要求得“变”与“不变”两者的统一,而两者的统一只能通过改革实践本身来解决。
在基础理论方面,综观世界各国课程文本的历史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里程碑:“行为主义→认知主义→建构主义”,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而“建构主义”也已经从“个人建构主义”发展到“社会建构主义”。社会建构主义知识论的基本立场,就是要消解个体与社会文化的二元对立。
在我看来,这种社会建构主义兼容了“反映”与“建构”两种机制,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我们当然不能原封不动地照搬照抄外国建构主义的一套,但是,为什么不可以在立足自身改革实践、博采众长的基础上,建构我们的建构主义呢?
在课堂教学方面,我国的课堂教学模式几十年一贯制,从“满堂灌”到“满堂问”,课堂教学的本质并没有改变。这是因为,我们缺乏“教学觉醒”,把教学归结为单纯的技术操作过程,导致了面孔单一的教学。“教学觉醒”意味着教学主体的回归,意味着教学过程是一种对话过程。
这种课堂教学的过程是超越二元论的。“接受学习”与“探究学习”作为人类的两种基本学习方式,在具体实践中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并非势不两立。因此,新课程凸显“探究学习”,并非全盘否定“接受学习”,而是旨在改造学生的学习方式,以“探究文化”取代“应试文化”。
教育周刊:观念转变是一个必要的前提,但毕竟从“树立观念”到“贯彻实施”之间还是有一段距离的。正确的观念在实施过程中,往往会因方法欠妥而“走了样”。怎样避免这一现象?不知您对此有什么好的建议。
钟启泉:新课程本身有一个成长、成熟的过程。加上缺乏强有力的跟进措施,确实产生了一些偏差。比如,各门学科之间的衔接不到位;精英主义、功利主义的倾向;教科书编制中的克隆现象,等等。因此,在“总体设计—课程标准—课堂教学”的设计链中总会有两个落差需要克服。
从“总体设计到课程标准”之间的第一落差,需要通过对话、讨论,即概念重建过程来解决。大凡付诸实施的重要举措,不宜朝令夕改。每一个人的见解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有深度未必有广度;有局部未必有整体。而课程问题是一个整体的问题,需要整体的、全局的思考;也需要善意的批评和理性的响应。
教育是一个公共文化的领域,需要作为公共的论题加以思考和讨论教育,其公共性呼唤的是“对话文化”。学会主张,学会倾听,学会宽容,学会分享,这才是和谐社会所需要的。
从“课程标准到课堂教学”之间的第二落差,需要通过教师培训来解决。课程实施是一种教育实践过程,是教师行动研究的过程,亦即教师专业成长的过程。新课程实施强调“教师培训”、“校本研修”,但是,实际中的教师培训除了国家级、省市级培训之外,县级以下的培训往往由低层次的教师进修学校或是一些公司把持,培训质量成问题。
综观国际教育界,近年来,美国有不少教师团体潜心“教学实践”的研究;日本有的大学尝试“教师养成课程”的开发,在教师教育的课程中引进“体验性学习”、“实践性课程的开发”,值得我们借鉴。
归根结底,新课程的实施呼唤教师教育制度、教育评价制度、问责制度、中介性监管机制等一系列教育制度的确立,呼唤教育科学的重建,还需要有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和配套的经费支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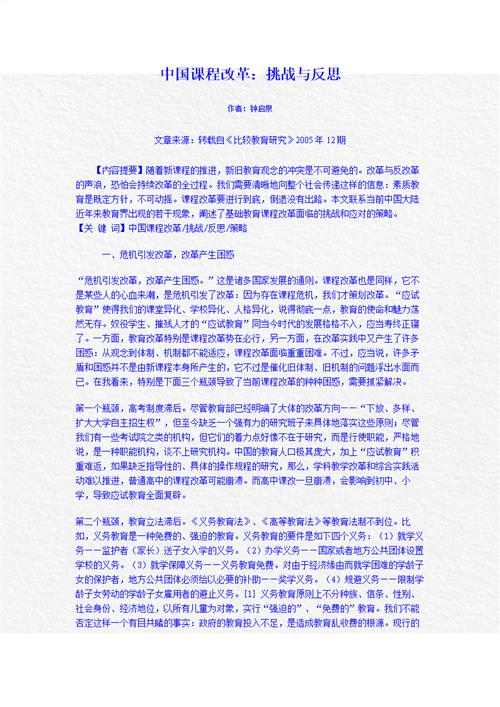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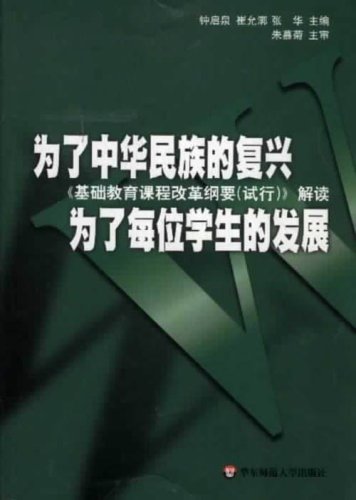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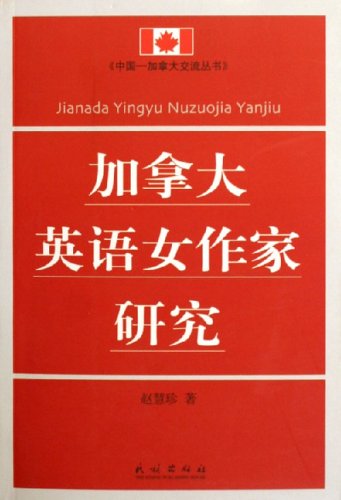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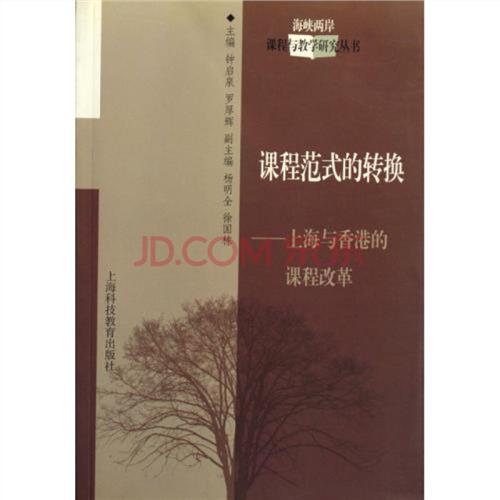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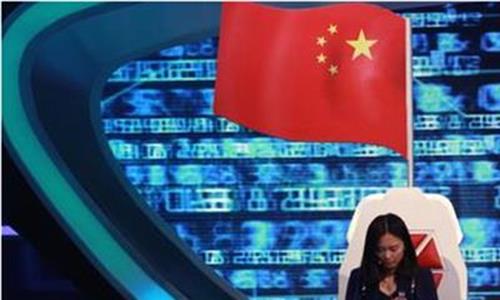








![>钟启泉第8次课程改革 [钟启泉杨明全]普通高中课程改革的国际趋势](https://pic.bilezu.com/upload/5/fb/5fb9785e25fae68add749057150bcef2_thumb.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