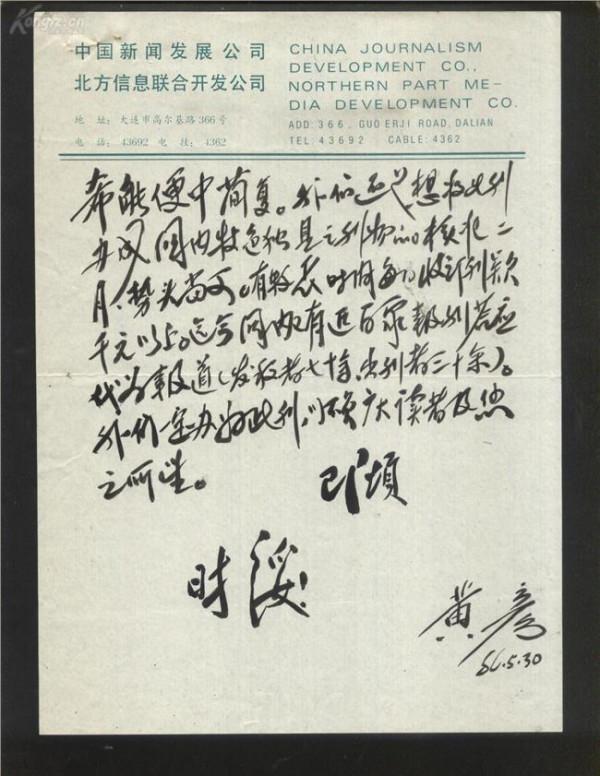蒋子龙拜年 讲台下专访著名作家蒋子龙:30年关注改革风云
蒋子龙,1941年生于河北省沧县,1965年发表第一个短篇小说《新站长》,1979年以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引起社会轰动,此后创作致力于改革者形象的塑造,在《一个工厂的秘书日记》、《开拓者》、《赤橙黄绿青蓝紫》、《燕赵悲歌》及长篇小说《蛇神》、《子午流注》、《人气》、《空洞》等作品里,他把改革者的个性心理、精神风貌及他们为现代化建设进行的可歌可泣的奋斗表现得极具感染力。
前不久,他又出版长篇小说力作《农民帝国》,第一次把笔头指向农民。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天津市作家协会主席。先后曾获天津市鲁迅文学奖,当代、十月、芙蓉等文学奖。
10月大讲堂的主题是文学艺术月,11日上午,深圳这个改革开放的先锋城市迎来了以擅长描写改革开放人物著称的作家蒋子龙。
蒋子龙主讲的题目是《改革开放与市民文化的发展》,他表示,谈谈市民文化是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因为几十年来我们这个国家政治运动曾经一场接着一场,很多基本上是反文化的,而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经济品位有赖于文化。我们的经济改革遇到了一个瓶颈,现在必须要文化的开放才能打开出路,这是必然的趋势,只有文化改革跟上,然后群众才能接受你的经济。结合这一话题,蒋子龙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文学触角一直关注农民
记者:改革开放之初,你创作了《乔厂长上任记》等工业题材小说,塑造了乔厂长等系列个性鲜明的改革派人物,但作为中国作协首批签约作家之一,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又选择写农民,人民文学出版社刚出版了你的47万字长篇小说《农民帝国》,这被认为是你文学创作在题材上的一大跨越。请问这一转变的原因是什么?
蒋子龙:当时写《乔厂长上任记》,可以说老乔是不请自来。当时我在一个1300多人的大车间当主任,副厂长是我的同学,对改革开放有不同认识,他遭遇了许多困难。于是,我就想假如我当厂长该怎么办。
乔厂长是我自己的想法,我认为必须这样办才能打开局面,所以,我用了三天的时间写这部小说,一共三万三千多字,基本上没改就全文发表了。结果小说一出来,社会的反映有赞有弹,极端尖锐。工人日报、人民日报等报还发表文章讨论。实际上是我对生活的感受触动了当时社会的神经,一些地方的厂长对号入座。有的人欣赏这个人,有的人不欣赏这个人。
《农民帝国》的创作过程是一个很特别的经历,其中的感悟也很特殊。这本书是我文学创作生涯中花费时间最长、投放精力最多的一部长篇小说。为什么写农民呢?——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农民问题。我的童年也是在农村度过的,童年会影响乃至决定人的一生。
我一直觉得自己骨子里是个农民。尽管已经在城市里生活了半个多世纪,每天看气象预报时,脑子里总是先想到对农村的影响,很自然地想起了庄稼的生长。眼下是什么季节?地里缺不缺雨?……因此,我心里很清楚,早晚会写一部关于农民的小说。
而眼下要反映中国现实,就没有比选择农民更合适的了。被邓小平称做是“第二次革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农民像以往一样又成了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原动力。所以,我的文学触角一直关注着现实,不可能不为其所动。
记者:能不能谈谈这部小说的创作过程?小说的主要人物和故事,以及你想表达什么?
蒋子龙:我不算多产作家,近几年来每年出一两本散文,这些散文反映了我的人生思考,我的人生态度、生活情感经历和思想历程。至于写长篇小说,应该是一种缘分吧,既然命中注定要写农民,就一定要完成它。
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开始的,我又熟悉农村,题材、人物是现成的,关键是氛围。为了写这部小说,我在河北、河南几个地方把自己“关”在乡下七个月,个人生活如同地地道道的农民,后来又在没有任何干扰的情况下在乡下写成了这部小说,语言、氛围、故事完全是农村的。
这部小说是以主人公郭存先的成长经历、人性蜕变及最后毁灭为主线。他想创造一个农民帝国,但结果是他自己导致了“帝国”的衰落,实际上是他的毁灭促使了“帝国”的变化和新生。应该说郭存先的悲剧不是偶然的,是必然的,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他的结局是中国农民的宿命。不过在当今复杂的历史条件下,表现形式及其结果更诡异罢了。
当代社会缺乏有震撼力的作品
记者:与当年相比,文学的力量似乎在衰退,文学对社会的影响力大不如前。你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蒋子龙:这是文学的尴尬,也是现代人的尴尬,但这不能归咎于文学本身,也许文学本该如此。我认为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当代社会缺乏有震撼力的作品,不能抓住人心;二是现代人看的东西多了,经历的也多了,网络时代人们更聪明了,对文学的要求也更高了。这在历史上是一个规律,在欧美等国的文学作品,读者也是有限的,当然永远有那么一些人有文学情结,愿意从作品中感受文学气息。
记者: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前几天已经公布了,以前期待很多,现在国人对中国人获奖期待好像很少了,有些作家就认为诺贝尔奖对文学评价到底是不是权威产生了疑问。你怎么看呢?
蒋子龙:现在诺贝尔情结是中国人的一个要命的情结,一到这个季节,中国作协、中国的作家走到哪里都有人问,什么时候中国有获诺贝尔奖的。这当然是一个话题,但不要太认真,我觉得中国的作家里真正有诺贝尔奖情结的不会超过十个人,大家都很清醒。倒是文坛以外的人愿意借着这个话题来谈一谈我们的文学现状,谈一谈我们作家的心态。诺贝尔奖已经让我们尴尬,我揣摩,也让诺贝尔奖评奖人尴尬。
网络文化有点急功近利
记者:你现在也是靠电脑写作,你怎么看待网络文化?
蒋子龙:网络文化简直是令人感慨万千,一言难尽。我通过网络获得资料,发稿也通过网络。目前是全民写书时代,人人都在网中。可是这个网络常常有点急功近利,就是还没摸准就乱炒。但是网络代表一种取向,很有生命力,我每天都得上网感受一种信息,但是,如果在网上没完没了,就被网网死,像一条死鱼一样,出不来。
所以,网络文化应该重视,应该研究它,应该感受它,甚至学习它的那种生气,但是也不要一味地听命于它,服从于它,为它所左右,那就惨了。网络文化目前毕竟有生气,还有肤浅,还有浮躁,出了许多好东西,那些好东西还是经过文字加以过滤一下更精致,所以对网络文化中的泡沫还要有所认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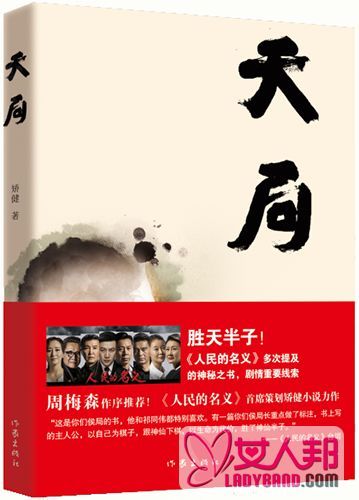





![>蒋子龙作品 《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作者:蒋子龙[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获奖作品]](https://pic.bilezu.com/upload/3/f6/3f6a6eee0fd75f277c46e913db4d3c33_thumb.jpg)
![>蒋子龙拜年 《拜年》作者:蒋子龙[1982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获奖作]](https://pic.bilezu.com/upload/b/fb/bfbc979289c15470bb9f4d9d96110386_thumb.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