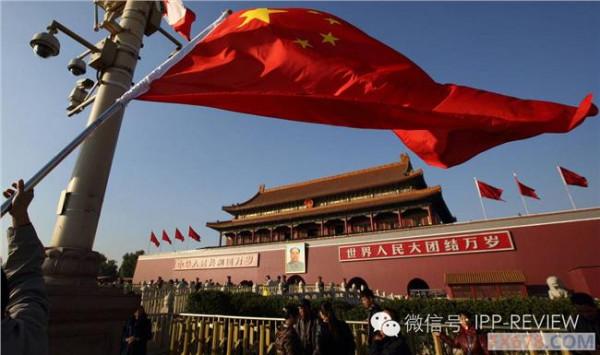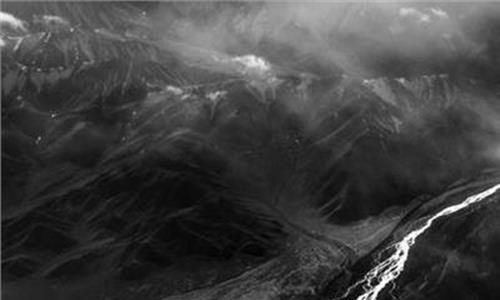郑永年党争 郑永年: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党争”及其恶果
近来,中国在意识形态上呈现出来的“党争”趋势使得人们对中国的未来抱有越来越大的不确定性。在社会层面,意识形态领域的“党争”已经有年,只不过是没有对执政党本身造成巨大的影响。或者说,社会层面的“党争”和执政党本身的权力和政策运作是分隔开来的,也就是一种“你说你的,我做我的”的局面。
但今天,有很多迹象表明,社会层面的意识形态“党争”开始向党内逼近。这不仅因为执政党及其政府的研究机构和智库开始卷入,更重要的是一些政治人物也开始有意识地展示其意识形态上的偏好,给予各种社会意识形态机会,试图与权力运作关联起来。
社会层面,意识形态的多元性不仅不可避免,更是中国社会进步的标志。除了传统没有利益分化的社会和近现代那些严格意义上的专制社会,所有国家的意识形态都会呈现出多元性。但意识形态的多元性并不意味着意识形态领域的“党争”。
出现“党争”表明各种意识形态之间已经缺乏了任何妥协的空间,各自原教旨主义化,各方努力把自身道德化,而把对方妖魔化。既然自己是道德的化身,而他者是妖魔的化身,那么自己和他者的关系便是水火不相容,结果便是党同伐异。
中国现在就出现这种趋势。各种意识形态的信仰者拼命占据道德高地,从意识形态、理论到个人品德和生活,给对方扣帽子、怒骂、诅咒,非常类似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各个派系之间的纷争,所缺的只是现在还暂时停留在文攻层面,还没有到达武斗层面。
尽管中国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但至少在社会层面,中国意识形态上的分化远超西方多党制国家。例如,西方多党制国家也有左、右派,但左、右派之间在大多数问题上是有很大的共识的,或者说“同”的地方多于“异”的地方,只是一个左一些,另一个右一些。
在这种情况下,第三条道路成为可能。当然,左、右派之间达成共识的可能性是基于大多数西方国家拥有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这一事实。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的存在制约着社会大多数的极端化,避免社会的激进化。
但在中国,左、右派之间没有任何共识,双方各说各的,各做各的,没有任何的交叉和交流,激进化和极端化是左右派之间的最大特征。尽管也有人一直在呼吁超越左右,寻求中国的第三条道路,但从近代到今天,第三条道路在中国实际上没有多大的空间。
当然,这也和中国的中产阶级非常之小这个社会现实相关。中产阶级很小表明社会极端分化。因此,一旦意识形态上的“党争”和其所代表的社会力量结合起来,社会冲突甚至是政治冲突就会变得不可避免。
“拥毛”和“拥邓”之争
改革开放以来,党内外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党争”实际上并不新鲜。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中国经历了第一次重大的意识形态上的“党争”,主要是围绕着对毛泽东的评价,出现“拥毛派”和“反毛派”。这次“党争”以1981年执政党出台《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而告终。
尽管激进的左派和激进的自由派对这个决议有不同的评估,甚至严厉的批评,但对大多数社会成员来说,这是一个可接受的妥协。这个文件的最大特点就是把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本身所犯的一些错误区分开来。毛泽东思想被定义为那一代领导人的集体结晶,而毛泽东则是主要贡献者。即使是对毛泽东本人也有公正的评价,把其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贡献和其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分开来。
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中国经历了第二次意识形态的“党争”,这次主要围绕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争。这次“党争”以邓小平1992年“南方讲话”和随后的中共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而告终。这也是一次妥协,是传统社会主义理想和市场经济之间的妥协,所以称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和前一次一样,激进的左派对之不满,激进的自由派也对之不满,但这种妥协则为社会的大多数所接受和认同。
那么,今天的中国为什么会再次发生意识形态领域的“党争”?近来的“党争”主要是对改革开放前后三十年的不同评估。左派倾向于肯定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而自由派倾向于肯定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左、右派之间的互相否认,导致了两个三十年之间的互相否认。
对前后三十年的“党争”进而又导致了对毛泽东和邓小平这两个政治人物的“党争”,出现了“拥毛派”、“拥邓派”和与之相对的“反毛派”、“反邓派”。现在,在改革开放前后三十年这个基本面上的“党争”开始迅速向其他所有重大领域扩展,包括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宪政与政治改革、国家权力与执政党合法性、市场经济、私有化、政党制度等等领域。
意识形态领域的这种“党争”,如果从经验的视角来看,毫无意义。人们所处的现实社会既非左派想象的世界,也非右派想象的世界。很简单,出现“党争”仅仅是因为双方都不敢正视历史和现实的产物。无论是左右派所热衷谈论的价值观、信仰体系、概念理论,还是他们所向往的社会,所拥戴的政治人物,在现实生活中都是异常复杂的,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道德判断、一个简单的否定或者肯定所能了事的。
当然,对这些简单的道理,左、右派也不是没有认识的。左、右派之间的“党争”背后更有其复杂的因素。这里,既有其社会背景,更有其对现实利益的追求。社会背景主要是中国社会的分化,财富分配的不公,社会正义的缺失。但出现“党争”显然不仅仅是对诸如政治自由、社会正义等价值观、信仰体系的追求。通过表面上的意识形态的“党争”,左、右派实际上追求的是物质利益和政治权力。历史上历次“党争”如此,今天也如此。
意识形态多元化不可免
今天的中国,因为经济和社会利益的多元化,意识形态的多元化不可避免,但意识形态领域的原教旨主义化则是必须加以避免的。人们必须对党争的恶果具有深刻的认识。一旦“党争”变得不可遏制,最后谁都会成为牺牲品,而执政党本身也不可置身事外。
历史经验表明,一个特定领域的“党争”如果处理不好,就会波及和影响到其他各个领域。在西方多党制,一些领域如同性婚姻、堕胎、环保等不时会出现“党争”,造成社会和政治的高度分化。但因为民主机制的存在,西方的“党争”不至于瘫痪政府。
中国的情况不同。尽管现在的“党争”还没有深入到执政党的高层,但一旦波及高层,后果便会不堪设想,搞不好就会瘫痪政府的议程,甚至演变成为权力之争。中共历史上历次路线之争都是意识形态和实际利益、权力交叉作用的结果。
那么,如何在最大程度上避免恶性“党争”的产生呢?中国历史上每每“党争”发生,皇帝便是决定因素。因为皇帝可以超越任何特定的利益,最后对“党争”做一个决断。在毛泽东和邓小平时代,是政治强人来最后解决“党争”问题。
无论是王权时代还是强人政治时代,“党争”的解决往往要不依赖于暴力机器的使用,要不依赖于重新把官方认定的意识形态加于社会之上,或者两者同时使用。但是,现在时代不同了,中国已经进入一个常人政治时代。
很显然,没有人会相信现在使用暴力机器可以消除意识形态层面的“党争”。在这样的情况下,要逃避少数社会群体之间的意识形态上的“党争”,就要从建设新型的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意识形态入手,也就是说,要做“加法”,或者增量改革。而重建意识形态正是今天执政党最薄弱的地方。
那么多年来,执政党本身在意识形态上可以说一直处于哑口无言的状态,没有任何建树。不仅如此,执政党在意识形态领域已经完全沦落为只会思想控制,而没有能力进行思想生产。现在所谓的“意识形态”至多也就是一些口号的积聚罢了,对此有多少人信呢?不用说在社会群体中了,就连党内能有多少人信呢?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如果没有人信,那么就是说,这个社会处于意识形态的真空下。
而任何社会是需要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是凝聚一个社会的软力量。一个缺少宗教信仰的中国社会尤其需要意识形态。传统数千年,意识形态实际上扮演了一种准宗教的角色。
鸵鸟政策再也行不通
意识形态上没有建树,首要的原因就是这个领域的高度不自信。在概念上,人们都知道应当如何“求同存异”,实现“和而不同”式的和谐。但在意识形态方面,人们一直所做的则是相反的事情,做的不是“求同”,而是“扬异”。
实际上,包括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和邓小平等近代以来数代政治精英所追求的目标和价值有很多共同的地方。当然,他们在追求这些目标的过程,往往因为历史和个人的因素,选择了不同的途径,一些成功了,一些失败了,而失败了之后再去使用新的方法。
这些成功和失败的故事都是历史的一部分。无论是失败还是成功,历史都有其自身的延续性。现在人们不去正视历史,而是各取所需,做着互相否决的事情。这种相互否决发生在不同历史的阶段、不同的政治人物、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文明和文化。
在普遍互相否定的情况下,要确立一种社会大多数能够接受的意识形态变成一种不可能的使命。这是中国的现实:只有分化社会的少数人的意识形态,而没有整合社会的多数人的意识形态;只有极端的原教旨主义,没有具有妥协精神的普世主义;边缘社会群体占据着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而主体社会则处于边缘状态。
没有思想的自由也是缺乏普世意识形态的原因。在中国,思想和意识形态没有区分,一切过于政治化。社会思想对意识形态当然具有影响,但仍然有很大的距离。思想史表明,当人们对一特定的社会问题进行思考的早期阶段,必然具有很大的争议,但随着思考的深入,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共识。
这种共识的很大一部分就会具有政策意义,可以为政治所用,转化成为政治和政策共识。在缺失思想自由的情况下,社会没有共识,意识形态也就没有根基。自己没有自由创造和生产思想的机会和能力,只好到外国去搬用,结果使得社会更加分化。
意识形态领域愈演愈烈的“党争”局面说明,执政党已经不能象传统王权或者强人政治那样来管控社会意识形态,而执政党一直所秉持的“你说你的,我做我的”的鸵鸟政策也已经显得不可持续。如果不能改变这种局面,总有一天,今天意识形态领域的“党争”延伸到政治权力领域,将酿成社会和政治的双重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