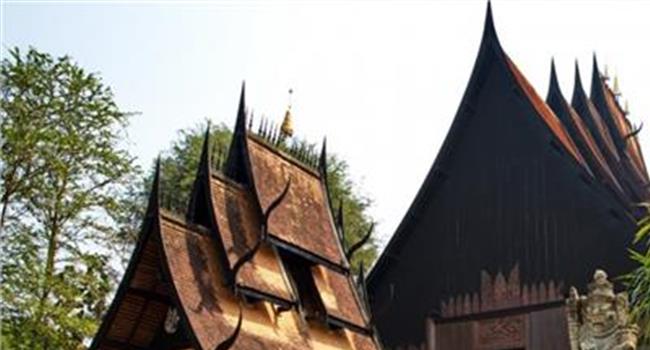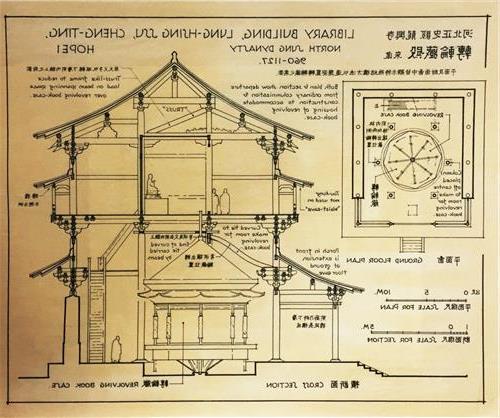梁信的夫人 第43章 梁信:白云山脚的“红色娘子军”之父
去采访电影《红色娘子军》的编剧、著名军旅作家梁信老师,我们出动了一个娘子军三人小分队:一是因为工作需要,除了采访还得拍照;二是出于对梁老的敬重,都想当面聆听梁老的教诲。
去之前我知道82岁高龄的梁老身体不大好,说了只和他谈半个来小时。怕耽误他休息,便想赶早,又不大认路,只晓得他住在广州白云山下的部队干休所,三位“娘子军”坐在车上一直听梁老“遥控”发指示。还不放心,梁老亲自向开车的师傅做了交代,那师傅年纪不过二十七、八,从农村出来打工,比1960年诞生的电影《红色娘子军》小得多,却也知道这部片子:“我听说过”。
我这才彻底相信曾经流传的说法:当年8亿中国人,有6亿看过《红色娘子军》,这还不算后来看的和听说的……说这部片子影响了几代人,没有半点夸张。
靠梁老一路阶段性的指点,车开进了干休所。下了车,再问清楚具体地点,于是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山路径直走去,坡的尽头有一个小院子,便是梁老的家。
梁老的夫人殷淑敏已经迎出门来,热情地把我们带进小院让进屋,只见房间里摆着一张桌球台,铺着桌布,围着几张椅子,成了我们的临时采访处。而梁老原先坐在隔壁的客厅里,这会儿已经站起来,只是腿脚不大灵便,拄着一根小拐棍,缓缓地向我们走来。
连忙抢上前去,握住梁老的手,请他慢慢坐下。
阿姨端上几种饮料,让我们各自挑,细心的梁老怕我们中有人喝不惯王老吉凉茶,阿姨又拿来了矿泉水。
家里没有其他人,我以为保姆准是买菜去了,一问才知道先前一直有保姆,前些日子回老家不来了,新的保姆还没有请到,梁信总结为:“一个孤家,一个寡人,就两老”,真正的相濡以沫、互帮互助——当然,说到家务事,梁老动口为主,殷阿姨则是家里家外、锅碗瓢勺地动手实干。
但梁老从来不曾闲着,就在我们去采访的那天早上,他也像平时一样,坐在他简朴、明亮的书房里伏案写作,用300个格子的稿纸,顶头一行是“东坡居士曰:‘三国周郎赤壁’”,第二行跟着——“然而,三国无周郎”。殷阿姨说:“他有瘾,天天看啊写啊,吃饭都要叫好几次……”
这太正常了,50多年里,梁信最大的爱好就是阅读和写作,叫他放下书和笔,又如何可能!
而在50多年前,梁信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四六师武装工作队队长,并兼广西柳江县百朋区、进德区两区区委书记,20出头的青年领导当地的清匪建政。他1945年19岁时参军,然后从北到南一路打下去,出没枪林弹雨,参加过不少著名战役,说他的青春是战火中的青春,说他为人民打江山浴血奋战,说他是残酷战争的幸存者,都千真万确,没错。
从梁老的脸上,似乎看不出《激情燃烧的岁月》中那个不打仗就找不着北的石光荣的影子。他戴着眼镜,依稀可见当年的潇洒、英俊,更多的是文气、是淡定,只有眉宇间与慈善交融的坚毅,明显带着军人的痕迹,而且他实打实是“我党我军从‘扫盲’培养起来的一代作家”。
对那段把生死置之度外的战争岁月,梁信在他的文选中称之为“无忧年代”,——不是没有危险,没有畏惧,而是那样目标明确、同仇敌忾的日子,让他和战友们铆足了劲,顾不上害怕,心里满是光明的前景。
人民的天下是打出来的,打天下的功臣人民不能忘记。当大地回春、和平降临后,不想做文人的梁信在1953年被调入中南军区部队艺术剧院,任中南部艺创作员兼支部书记,他既然走上了这条路,也就天经地义地开始了他以部队生活为基调、充满战斗激情和情谊的文学创作。
《红色娘子军》是这样诞生的
窗外,小院里静悄悄,叫不出名字的一串串小红花开得热火朝天、旁若无人。早就听说梁信管他这个寓所叫“一步庐”,最初这里还只是他的“草创未成的准寒舍”,他晓得离休后即将搬来这里。于是趁开会间隙,把三位誉满中外的朋友谢晋、范曾、于是之带到小院“观光”。站在院门前,他告诉朋友,今后这里“就叫个‘一步庐’吧”
“何解?”众人问。
梁信叹道:“碌碌红尘,从此‘身后门’走出,离那生命终点,只有一步之遥了。”
坦然,无畏。从那以后,梁信的这“一步”已经走了20余年,并且还将继续走下去;他和“一步庐”相依相偎也已经20余年,平房、小院,简单却十分亲切。但最近要和它分手了——梁信接到通知,要搬迁到附近一幢公寓楼去。房子绝对新,却是四楼,小院子没了。
“我就要被‘摞’起来了,不过还不算高。”——梁信就有这个本事,说得一本正经,旁人却忍俊不禁。
采访梁信的人大都言必电影《红色娘子军》,可梁老直言:“我自己并不欣赏我的电影剧本,我欣赏我的中、短篇小说”。
梁信的话让我意外,回来后我拜读了他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写的中篇小说《八帧女子肖像画》等作品,才多少明白他为何出此言。——那一篇篇小说多以军队和战争为背景,以军人和军属为主人,故事情节曲折,人物个性鲜明,文字干净生动,读来引人入胜。
就拿《八帧女子肖像画》来说吧,那位经历了多年战火考验,从中国的东北辽宁打到苏联的远东地区,又从欧洲的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打回故乡的红军指挥员,有着传奇的战斗生涯和凄美的感情经历。一生中有三个女人,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男女之欢;有一儿一女,却都不是自己的亲骨肉。
他没有倒在硝烟弥漫的战场,却在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历次运动中饱受摧残。但直到生命之火将要熄灭的时刻,他依旧怀着一腔痴情,对他的祖国,也对他的爱人……我一边读一边不断地随着故事的发展,在脑海中变换着一个个场景一幕幕画面,我想这要是拍摄成一部电影,一定非常好看,催人泪下。故事在今日看来有几分离奇,但放在当时的环境中就可信得揪心。
或许《红色娘子军》的热映与成名离不开特定的历史原因,但只要提起梁信,我觉得还是要说那部红色的经典影片,因为看似偶然的东西往往有它必然的原因。
梁信是穷人家的苦孩子,没读什么书,到了队伍上真刀真枪地打了七、八年仗,1953年离开战场,才有个安定的环境在工作之余学习文化知识,又拜师前辈学怎么写作,还尝试着写了点小东西发表,这就有了1956年赴北京中央文学讲习所进修半年的机会。由于成绩优秀,他被留下来写长篇。不久,总政创作室调他去“安心写作”。
但没有想到的是,梁信很快就无法“安心写作”了。
1957年整风运动中,梁信从北京写信给所在单位广州军区战士话剧团,谈了对一个处理不当的问题的意见,竟被认为是右派言论,是向党进攻。鉴于“右派分子”名单早已上报,给梁信补了个保密的内部“中右”,对本人不公开。
现在想来,也幸亏这个“不公开”,使梁信在没有太大政治压力的情况下创作了《红色娘子军》的电影剧本,并在天马电影制片厂(即上海电影制片厂)打算拍摄该片时,得到军区政治部的同意,顺利去上海修改剧本。否则,全国人民什么时候才能看到这部电影,就是个未知数了!
上世纪30年代创建于海南岛的那支红色女子连队的情况,梁信是1958年出差海南岛,在翻阅军史书时无意中看到的,内容比较简单,无详细记载。但他军人的热血立即沸腾起来,他仿佛回到了祖国灾难深重的过去,他钦佩这南方的群体花木兰,为她们感到骄傲,同时也敏锐地意识到:当时曾经发生过多少悲壮甚至惨烈的故事。
梁信原本准备那次出差回去就到武汉高级步校改行学军事,可这会儿再也坐不住了。他四处找资料,查挡案,到海南岛采访健在的娘子军连指战员,在她们战斗过的热带的深山老林里穿行,在她们驻扎过的贫穷落后的黎村苗寨中流连……一呆三个多月后他熬了四天四夜,写完了剧本初稿。
回广州后,梁信把剧本拿给部队首长,首长看完说了一句话:“你别去步校学习了,还写下去吧!”
梁信果然写下去了,一直写到今天。但个中艰辛,一言难尽。也有被迫停笔的时候,文革劳改四年,言尚且不自由,更惶论写!
还是先回到1958年吧!《红色娘子军》的剧本分别寄往五个电影制片厂,是天马厂文学部的老艺术家沈寂把这个本子推荐给了谢晋。当晚谢晋一连看了两遍,第二天一早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立即去厂长办公室要求接下这个拍摄任务。两天后,请求协助修改剧本的函件寄往广州。——这样的速度可以和多年后的“深圳速度”相媲美了。
由于这次合作,梁信和谢晋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友谊。就在我们采访梁老后不到十天,谢晋在睡梦中溘然长逝,这个消息带给梁老的悲伤我们完全可以想见……
那时,梁信和谢晋都正当好年华,两人一见如故。为了选片中的女一号,谢晋隔三差五给梁信寄美女照,梁信看了总说不行,——不是不漂亮,而是不合适。谢晋在中国大陆几乎跑了一圈,女主角还没有定下,心中很是憋屈,那日去上海戏剧学院找人想办法,没料想被院里一个吵架的女孩所吸引,特别是那双“火辣辣的大眼睛”让谢晋满意,火速把梁信请来确定,谢晋却领来11个女孩,说:“我挑中了一个叫祝希娟的,你看是哪一个。”
结果如何,读者诸君肯定想到了:梁信一眼就认出来了,指名道姓地问:“你是祝希娟吧?”得到对方肯定的答复后,他对谢晋说了三个字:“就是她!”
《红色娘子军》火了,导演和演员火了,编剧梁信也小小地火了一把,但几年后他就被铺天盖地的文革潮卷进了劳改场。
自有作品来说话
从劳改场“解放”回到家,已经是1972年。
“文坛大盗”的帽子、“剽窃作品”的罪名,都未能使梁信屈服。即使在铁窗内,他也深信:“我们的党,终有一天会回到马列主义立场上来,调动起浩浩荡荡的知识分子大军,推动物质与精神文明的两个历史车轮,为人民造福。……”
回家不过两个月,梁信就打点行装出了门,他要重返20年前的广西剿匪战场,他要让那一段战争史化作小说跃然纸上。
从广东沿海到广西,从友谊关零公里处,北上直到湘、粤、桂三省交界,梁信一路走一路看一路回忆一路思考,春节前返回广州,不等过完年他就拿起了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