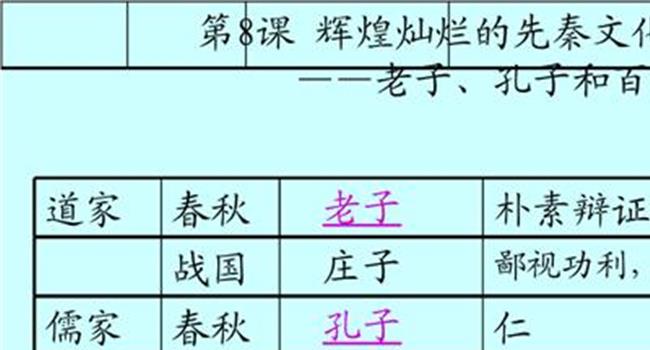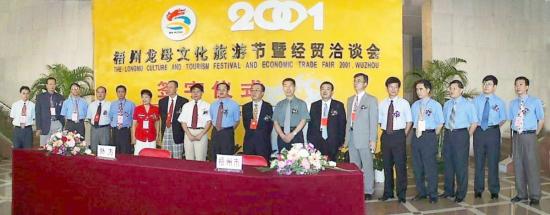谢有顺的文章 谢有顺:文化大散文的高峰依然是余秋雨
出生于福建长汀的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文学评论家谢有顺,是本届高研班的学术主持,他对比了祖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两地在文学语言上存在的差异,他强调散文要有“节制之美”。“我们越来越反感于直抒胸臆式的,感情无端喷薄而出的散文,我们称之为滥情。相反对于那种隐而不发的,非常节制有度的散文,会给予更高的评价。”
■大陆的话语慷慨,台湾的话语感性
谢有顺说,对比大陆普通话和台湾普通话的差异,就可以看出两地散文的差异。“大陆的普通话,尾音是上扬的,铿锵有力,一定会有很多硬的、慷慨的、广场式的语言,台湾的普通话,比较软,尾音比较柔,相对比较感性,大词会少很多。”谢有顺认为,这跟革命话语方式对大陆语言的改造有很大的关系。
谢有顺回顾了自五四以来现代文学中两套话语方式演变。百年来,它们一直处于此消彼长的状态。一套是以陈独秀、鲁迅、左翼文学等为代表的话语体系,具有广场话语和扩音器色彩,革命性强,一直处于主流地位。
另外一脉是以胡适、梁实秋、周作人、张爱玲、沈从文、钱锺书等为代表的话语体系,他们关注日常生活,同时比较感性,话语细碎,语态柔和。谢有顺把前者概括为“硬话语”,后者概括为“软话语”。
“大陆肯定把革命的、硬的话语发挥到极致,完全成了广场式书写的,也不乏其人。软的、日常性的这套话语,在台湾得到发扬。”谢有顺说,台湾传承的是自胡适开始的那套软话语,影响了台湾的几代作家。这种语言上的差距,深藏着两地文学审美的差距。
■大陆和台湾语言风格互补
作为本届高研班的大陆学术主持,谢有顺认真研读了福建作家和台湾作家所提交的散文作品。他发现,参加高研班的台湾80后作家,他们的散文更日常化,笔下的生活场景富有质感,有更多的来自日常生活的细节,语言方式更平实。
福建的一些作家,则容易或者愿意去关心一些更大的话题,同时也容易把哪怕是很日常的事情,愿意或不自觉地进行升华,试图为自己的书写找寻一个更大的坐标,来提升文章的整体高度。他认为这是很多大陆作家在不知不觉中就会有的潜意识。
“大家尽可能要警惕这样的倾向,即所谓的‘大词主义’,很容易把一个事情向另一个事情过渡,不太会审慎地过滤这些词,而是轻易地让这些词出现在我们的笔下,甚至有一些全称性、绝对性的判断。比如我们经常会用到,中国几千年来怎么怎么样,华夏文明怎么怎么样,中国人的一生怎么怎么样……”谢有顺说,类似这样的表述都是没有经过过滤的语言惯性。个体和社会之间的互动,
不能以丧失自我和个体为代价。
“大陆的散文也有它的优势,视野的宽度广度,思考的问题比较大,也比较深,这一点是台湾作家未必写得来的,或者是不愿往这方面努力的。”谢有顺说,很难简单地比较大陆与台湾的散文孰优孰劣,但大陆以“硬”为主的语言风格与台湾以“软”为主的语言风格,恰恰具有互补性,在此背景下举办两岸中青年散文作家交流会,更凸显了交流的意义。
■贬损余秋雨的散文一文不值,至少我不赞成
在当前的时代语境下谈论余秋雨,是个有些敏感又有些复杂的问题。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直到新世纪十几年,文化散文写作在大陆散文界蔚然成风,提起文化散文,不得不提余秋雨。近年来,余秋雨的形象急转直下,谢有顺认为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话题。“这个问题我觉得很复杂,如果因为对余秋雨这个形象不喜欢,就贬损他的散文一文不值,至少我是不赞成的。”
余秋雨在1988年左右开始在《收获》杂志上写专栏,即《文化苦旅》这一系列文章。“回想一下,在余秋雨写这些文章之前,大陆的散文是什么样的状况,至少当时大部分作家写的散文,无非就是登泰山有感、黄山看日出、雨后赏荷花,或者养只鸟,或者登个山……基本上就是这样一种模式。
余秋雨前,没有人想过,散文可以写到几万字。余秋雨后,人们意识到,散文也可以做鸿篇巨制,也可以承载文化、家国、历史这些重大问题的思考。
”谢有顺说,从文革结束到1988年,这期间几乎没有出现余秋雨式的散文,有也是零碎的,没有人像余秋雨这样做得成规模。从这个角度上讲,余秋雨散文的出现,对当时的散文写作潮流是一种纠正。
“后来,这样一种文化散文写作在大陆散文界蔚为壮观,1988年开始到新世纪十几年,不夸张地说,80%的人都在写文化散文,诞生了一大批余秋雨的模仿者。”谢有顺评价,尽管余秋雨的模仿者众多,但直到现在,没有哪一位余秋雨的模仿者超过了余秋雨。“文化大散文作为一种写作潮流如果成立的话,高峰依然是余秋雨创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