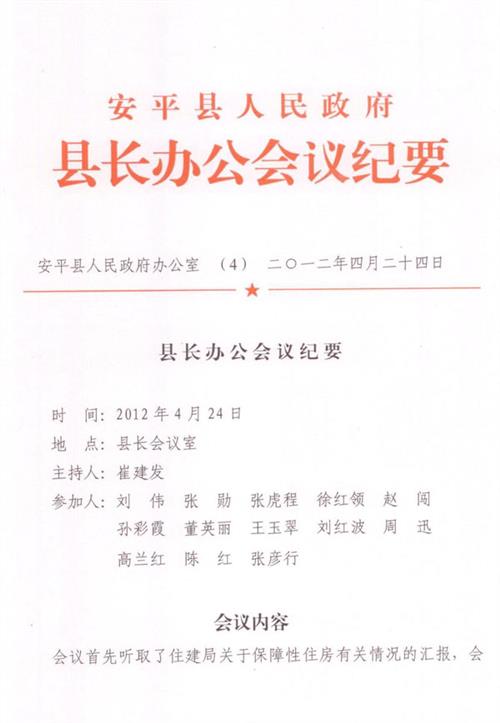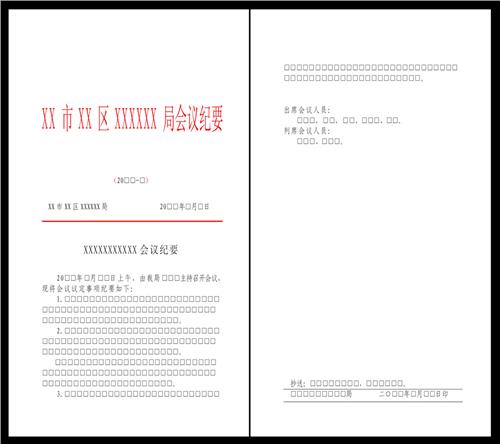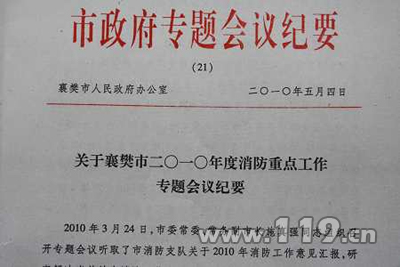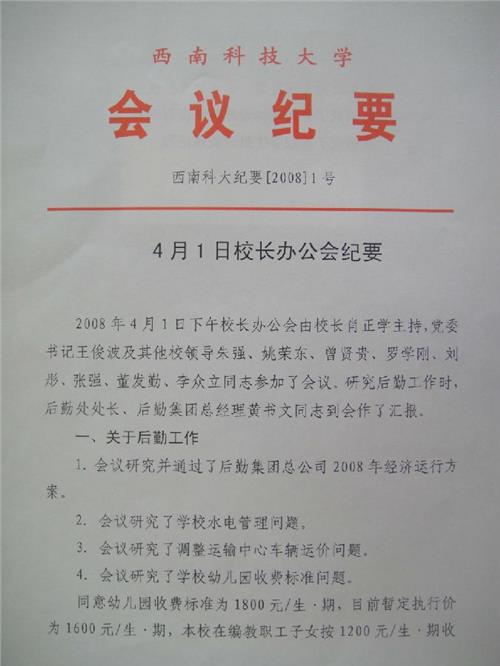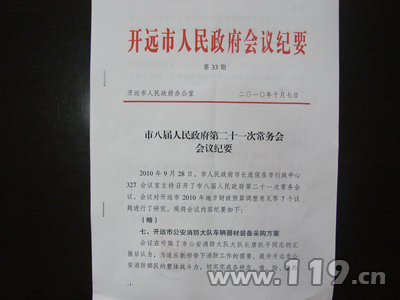朱大可华夏上古神系 全民腐败:朱大可著作《华夏上古神系》尝新会纪要
朱大可著作《华夏上古神系》尝新会纪要
本月22日下午,多年来从未搞过个人作品研讨会的朱大可,破例在其个人工作室,举行了新著《华夏上古神系》的尝新研讨。上海文化界名宿云集。
该会由学者刘擎主持。
朱大可的“文化研究”涉猎广泛,从大众文化到精英文化,从当代文化到上古文化,从世俗文化到神学文化,均有见地独到的著述。而当人们还在其批评文本中徘徊时,朱大可又出人意料地完成了“变脸”和“转身”。
他新近推出的专著《华夏上古神系》,长达40万字,上下两册。该书酝酿20多年,闭关写作3年,在东方出版社编辑近2年,以“慢炖”的方式,重新梳理华夏上古神话体系。
全书充满大量原创性观点,对传统学术体系构成鲜明挑战。
朱大可在书中提出“神名音素标记”概念,并以此为工具,建构宏大的“巴别神系”,对上古全球神谱做出史无前例的系统性描述,他“亚洲精神共同体”概念,深入描述上古亚洲各地之间在人种、商贸和文化三个层面的交流盛况,不仅揭示了中国先秦文化的成因,而且对当下中国调整与亚洲各国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有学者指出,这种“共同体文化”(东方智慧),将成为中国和亚洲各国对话、和解、达成共识的文化基石。
朱大可表示,他写作本书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试图击碎“国粹”陋见,证明开放、吸纳和再创造,是中国文化精神的核心和生命力所在,也是中国文化的最高传统。
朱大可认为,从高度开放、博采众长,继而实现超越,完成原创,是华夏文化精神的伟大特性,也是其卓立于世界文明之巅的主因,而这为未来中国文化复兴,提供了重要的精神支点。
朱大可:
我们现在开始进入议程,我首先对大家的到来表示衷心感谢和热烈的欢迎!今天的主持是刘擎,我跟他的交情是很好的,将近30年了,他在大学期间是少年天才,做话剧很成功,所以那个时候声誉鹊起,现在是华东师大政治学系的主任,在政治学的研究方面有很独到的见解和影响,今天请他做主持人。
刘擎(政治学者,华东师大政治学系主任):
很荣幸受大可的信赖委托,主持这样一个高朋云集、牛鬼蛇神云集的活动。朱大可先生从事文化研究30年,现在又亮出两卷本著作,好像是一种学术转型、升级换代的节奏。我的感觉是,大规模杀伤性的武器终于出笼了。首先有请出版这本书的东道主——东方出版社总编辑、《人物》杂志社社长许剑秋先生致词。
许剑秋(编辑家,东方出版社总编辑):
我今天感到很荣幸,参加朱大可先生的新书尝新会。我们社在北京9月份的时候,还要搞一个这本书的首发式。
我们有两个编辑上的关键词,第一是“联系”。什么联系呢?是我们的中华的文化与西方文化建立了更紧密的联系,借助朱大可的“亚洲精神共同体”概念,跟亚洲各国乃至西方做更好的文化对接。第二是“源头”,中华文化的源头到底从哪里去挖掘?中华文化的复兴从哪里开始?这本书从这两个角度都有重要意义。
第三点,这个本书对文化产业是有价值的。今天我们发现了内容的贫困,已经成为困扰许多文化产业投资人的难题。朱大可的研究成果,可以为文化产业提供新的广阔的内容空间。
邢和祥(华东师大校友会秘书长):
我代表华师大的20多万的校友,向大可的这本新书表示最热烈的祝贺,这本书不不仅仅是一个神系,应该是一部神曲,一部神书。神人出神曲出神书,这是必然的。
査建渝(上海华侨基金会秘书长):
今天走进会场第一个感觉是回到了80年代了,看到吴亮、孙甘露、王小龙这些人,当年都是非常活跃的知识分子。
可还有一件事可能知道的人不多,我们91级的学生江南春,搞了一个分众传媒集团,做了一个40多亿美金的上市公司。他自己说,他之所以做得那么大,主要得益于大可先生的一堂课,这堂课讲了端午节的起源,讲了屈原的死因。他因此有了一个新思路,找到了分众传媒上市和发财的路径。
钱文忠(学者,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我有几点感受想跟大家求教一下。第一,这是一本开放性的书,也提出了许多问题,朱大可主要是在制造问题,他是一个“麻烦制造者”。
大可提出了很多问题,他像一位号手,但吹响的是究竟什么,我们要等到以后才能听清楚。在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上,凡是要出现大变动,往往就是神话研究变热的时刻。第二,我觉得这个书还有一个很大的突破,因为他在书里对“中国文明西来说”做了很重要的梳理。
清朝末年以来,中国第一流的思想家,甚至包括鲁迅先生,都是信奉“中国文明西来说”的,甚至认为人种也是从西方来的,盘古、西王母这些神话人物都来自西方。
大可对此做了一个梳理,但他的梳理跟过去有很大不同,过去的“西来说”强调直线式的来回,也就是两条平行线,西来,东去,很简单。但大可是用一个多元、跨文化和和全球化视角去看待神话体系的,这是个更复杂的矩阵,而不是简单的线性。
另一个方面,过去研究神话的大量精力,往往用在琐细的考据上。大可在这部书里面做了很多考据,有的考据令人非常惊讶,比如说谈到印欧语的词尾、后缀等非常专业的问题,包括探讨原始印欧语是不是共同语,这是非常艰深的学术难题。
因为现在这几年大家在找汉藏共语,这方面上古音韵的构拟,取得了重大突破。大可做了很多不是其专业领域的考据,我觉得考据得非常细,而且所引用的图书很得当,无论版本还是学术史地位,都无可争议。
整本书给人的印象是,经得起通、达、观、照四个字。
朱大可的这部著作现在刚出,它引发的讨论会持续生发出来。我认为一本真正的好书,一定是提出问题最多的书,而不是解决问题最多的书,解决问题是一种终结,提出问题却是一种生长和拓展。对这部书我用四个字概括:功德无量!
吴亮(批评家,《上海文论》杂志主编):
朱大可的写作特征,是把符号作为他的意象去分析,有时它本身不是一个意象,但朱大可总是先把它变成一个意象。
比方说,他最早论上海的城市文学,形容他们是“都市中的老鼠”,他先把这些作家变成了文学老鼠,然后再去谈这种老鼠的特点。还有他做文化批评,谈麻将,他是不懂麻将的,但是他把麻将变成了一个喻体、一个象征、一个符号,然后在这个层面上展开他对整个时代的看法。
他的《流氓的精神分析》,居然把庄子、李白和都称之为“流氓”,他先先把他们流氓化,然后开始重新加以阐释。他有非常好的转化能力。朱大可是制造概念和符号的高手。
我还没来得及读完这本书,但我觉得整个框架是非常稳健的,这不是他过去的风格。我不知道是什么力量在起作用。他在叙事上变得很克制。他在重构一个历史。
孙甘露(作家,上海作协副主席):
刚才我一直在想,为什么大可开这样的一个会,会找不同的领域的人来说话?按理说大学的学术研讨会不是这样开的。
我于是想到一件事情,当时刘擎的好朋友、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马克里拉来上海做《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一书的尝新活动,我们一起吃饭聊天。饭桌上大家谈论各自读什么书,交换对读小说的看法,刘擎的一个女学生在被问到读什么小说时,她回答说我不读小说,小说很没意思的。
当然她可能指的是中国的小说,这时马克里拉说了一句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你不读小说,你怎么做思想史?我觉得这就是大可找我们大家来聊他新书的原因。我们可以通过不同门类的思想、学术和艺术活动,来研究这个时代的文化特征。我们所置身其中的时代,变化多端,汇聚了各种有价值的声音。
张献(独立艺术家,自由撰稿人,艺术策划人):
有一段时间我是很确信大可是一个行动者,我也跟很多的朋友讲,我始终认为他是一个剧场的人,是以自己的行动构筑一个剧场的人,这个剧场他不需要一个固定的演出场所,打上灯光,不需要通过每次一两个小时的表演来实现他的剧场效应。
他是熟悉人的肉眼之外的眼睛的这么一个人。
当我拿到这本书时,我看到的是一个诗人的回归,又是一个行动者的回归。
书里虽然全是学术成果,但我却不认为这是一部学术著作,我把它视为一件诗人的作品;其次,这个作品是一个行动的连续。这使我如释重负,因为这本书像一个手册,我们放在书架上索引,看到了我们已经读过的那些书,在这里得到了有智慧的总汇。
张荣明(华东理工大学文化研究所教授):
我看了大可先生的专著,把中国古代神明进行了完整的梳理,并对世界上的各个古老文明进行了比较研究,这是一个全新的尝试。
对一门学科来说,我们需要各种不同专家从不同角度来对研究,对于神话,可以从考古学、历史学、宗教学和人类学的神话原型批评入手,用的材料也非常丰富,在这方面,大可先生做了很可贵的尝试。
我跟大可不是一般的朋友,我记得大概有30多年了,我们气味相投。有一次他请我吃饭,不知道是用印第安人还是犹太人的什么东西来帮我占卜,说我有一本书马上要出版了,结果很灵验,这个方面我们气味相投。
他到澳大利亚之前,我们每个星期都要讨论生命学。没想到30多年后他从生命学走向了神话学,所以这也是一个渊源,从生命学到神话学,应该说他修成了正果。
周圣伟(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
评价这样的书,至少需要三个条件,一个是相应的知识储备,第二是相关的学术视野。第三个是必需的思想阅历。
这三个方面我都有所欠缺,所以不敢横加评议。
我这人看书有个坏习惯,喜欢看人家引用的参考文献和资料,朱大可的这本书知识很扎实。
他引的文献非常有眼力,包括他对比较神话学的概括式的评论,确实是深入其中的,而且也是能出之其外的。
我过去当过大可的辅导员,从他第一篇文章开始我就特别担心。
也不是说我担心他逃课,因为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也逃课的,我担心的是他的写作方向。大可第一次给我看了一篇小说,好像写北京的什么什么,我说会枪毙的,不行。第二次他给我看了一首诗歌,我还记得结尾讲树叶飘落下去,落下去,下去,去。
我说你在玩马雅可夫斯基阶梯诗游戏,只是倒过来玩。我说这也不行。但没几天,他又拿一篇文章给我看,论述的是诗经《蒹葭》与现代主义作品的神合,我顿时眼睛一亮。
马上把他推荐到中文系的学生杂志上去。我跟大可说,你就是搞这个的料。因为他有做学术和理论的敏感性和悟性。在1980年的时候,《蒹葭》跟现代主义还扯不上关系,但你现在来看,它确实就是一篇非常经典的现代主义象征之作。
后来他给我看的一篇文章,好像叫做《论艺术媒介系统的演进》,那天毛时安到我寝室玩,而我有什么事情被学校叫去了,朱大可的文章就放在桌子上,等我回来时,毛时安还在那里等着,我说你怎么还没走呢?他说我在看这篇文章,到底是谁写的?我说是我们79级的一个学生,他说写得好。
我说当然好,你写不出来的,当然我也写不出来。
这篇文章写得非常好,从整个内容到篇章结构,甚至每一节章节的开头和结尾,都用了很多心思,就像装修一间房间,他各方面都弄得非常精致。后来我们的学报编辑把它发表在学报上,大可那时还是三年级的本科学生,在学报上发1万多字的文章,是非常罕见的。
但是到毕业时,三个老师因为看不懂,要给他这篇论文打不及格,我是非常不舒服的,我跟他们讨价还价,一个个做工作,三个人有两个还是很有分量的,最后妥协下来,打了一个“中”。
我这次看他的书,感到他学术上的大气,还有就是学术度量比以前大多了。在书里,他有一种非常雍容的学术态度,他把自己的学过的东西全部装进去,文采飞扬。
这是一种从文化的基因上面的寻根工作,很难的,做这种工作,需要非常广泛的知识面。我搞古典文学,所以我知道中国神话本身的断线接网,就已经非常困难了。但他能高屋建瓴,搭建一个很有规模的谱系。尽管这本书的成就还有待于学界的认可,但这份勇气和前瞻性令我非常佩服,我为有这样的朋友感到骄傲,我相信各位也有相同的感受。
刘巽达(文化批评家,《采风》杂志主编):
我觉得朱大可有一个特点是语言洁癖,同样的评论家,我看了很多的文章,往往文章的意思说出来了,但是文采不够,朱大可对自己的文采非常苛求,就是说有一个字用得不精准他不会放过的,另一方面,他还有探求真相的洁癖。
我看这就是朱大可的学术动力。
从表面上看,朱大可的研究结果,对狭隘民族主义者是一个打击,什么从非洲来?从印度和波斯来?这让我们大中华民族情何以堪?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却证明中华民族的文化是高度开放和博采众长的。
朱大可的结论是建立在严谨的学术研究的基点上的。为什么华夏文化精神在日益萎缩?导致这种萎缩的原因,究竟是民族性格使然,还是我们的制度使然?朱大可的书明白的揭示出,善于吸纳和高度开放,才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本质,但我们现在却越来越走向保守和自我封闭。所谓“爱国主义”,骨子里就是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国家主义,这是自我封闭和自我中心,最终只能断送中国文化的未来。
刘擎:
我也想说两句话,大可的书有一个潜在目标,就是针对“民族精神病理学”。每个国家都是靠一个故事生存下去的,我们国家也有一个冗长的故事,但是这个故事现在讲不下去了,变得很乱,成为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工具,这就是我说的“民族精神的病理学”。
中国文化以前曾经有很好的兼容性,比如说韩愈解释的那个华夷之辨,所谓的夷狄入华夏而华夏之,华夏入夷狄而夷狄之。
就是说文明和野蛮的区别,不是种族和地域的概念,是理念和生活方式的概念,谁的好,我们就用谁的。晚清的民众,多炫耀自己家族“三代在欧美”,那个时候的人有这样这种大世界的情怀。
但到了现在,我们却反而在纠结什么是我们的,什么是别人的,而不是好的和坏的。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民族精神的病理学问题。我觉得大可他一直有对精神分析诊断的深层愿望,他对文化的病理学和民族精神的病理学,有一个阐释和解构的冲动。所以看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他是在做民族精神病理学分析的准备工作。
李西闽(小说家,新概念恐怖小说领军者):
我没有准备要发言的。我跟大可是正宗的客家老乡。我们曾经有一次我陪他回他的老家去过。
我对神话这个东西一直很感兴趣,因为我们客家人的家族里面都有一个小神保佑我们。我今天才拿到这本书,但我特别兴奋,因为我也准备写一本书,是关于蛇的故事,这个传奇故事会应用到一些神话素材。我觉得这本书会影响到我的恐怖小说或是神话小说写作,因为它将给我提供很多精神上的养分,我没上过大学,读书也不多,主要靠自己的灵感写作,这本书可能会成为我的精神支撑。
张念(女性主义批评家,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副教授):
我觉得他研究神话不仅仅是神话,而是要重新寻找文化建制的合法性问题,也就是说,合法性的建制,借助于一种对神话的回忆,以追根溯源的方式,重新叙述事情本来面貌。
这就是神话学和其他所谓学科的区别。我觉得大可在写作时是一头“大灰狼”,他面对一个对手,这个对手就是他所生活的处境,还可以是那个被叫做“中国”的地方,或者是叫做“中国文化”的东西,他有他自己的一个观察的角度和洞见。
我觉得要充满信念才有一种动力去推动他去写。大可是如此憎恨,这憎恨是充满辩证法的,他憎恨我们现在的这个样子。他要去谱写文化的异托邦。大可的性格里面有赤子之心,有爱,另外也有妖的成分,那个成分今天我们就不谈了。他更适合贴切地去聆听来自本源的声音。
刘擎:
刚刚有人提到了大可的客家人出身,他自己也是很在意这种出身的,这在全球文化里有一个可以相比,那就是犹太人在欧洲的影响,这是很有意思的。
文化如果没有这些有点讨厌的、异端的东西加入进来,它就会变得很完整很同质,但那个完整却是死亡意义上的完整。人们通常说的这个“客家”,可能并不是指一个狭隘的种族或血统上的族群,而是一种气质上的文化反对派和异端,它使这个文化变得更加有趣,它有时候是危险的,但危险也是有趣的一部分,这是文化传承和发展的内在动力。
我觉得要是做DNA测试的话,朱大可在血缘身份或许很可疑,但在精神气质上,他却是一个永不屈服的客家人。
于奎潮(诗人,江苏文艺出版社副总编):
我是一个做书的编辑,任何一本书都有一种气息和手感。我觉得这本书是我很喜欢那种,这跟它的编排制作是有关系的。
今天我要向出版方表达敬意,因为现在大家都强调图文书的概念,而这本书把图的功能和价值非常好地凸现出来。用这样的好纸,把彩色的图印得这么精美,是非常值得尊敬的,这些图都非常清晰,而且色彩还原得很正。它的内容的宏大精深,加上制作的精良,这两个方面的结合,保证了它的优秀品质。
廖增湖(作家,《收获》杂志编审):
朱大可建立了自己的神话谱系。这是一个我们原有的儒家神话体系的终结,也是一个现代朱氏神话谱系的诞生,这完全是一个新天地。
朱老师实际上是一个跟主流文化分庭抗礼的人,他完全掌控了民间话语,并且运用这些话语化为无数飞刀,随便运用一个词语,就可以打遍天下。
面对所有这些传统文化的秩序和伦理,朱老师一直在搞消解的工作,他写到屈原被杀之谜,勘察在谋杀的现场。还有嫦娥的失踪之谜等等,他每一个神话做得非常细,也有一些人攻击他说资料做得不太好,但我觉得适合我们这些人去读。
我的看法是,这个上古神话谱系,把所有的传统神话重新排列了,比方说我们会说炎帝、黄帝,这个我们说得很顺的,普通人都这么说,可是他写立刻替你切开,称为炎神,黄神,看起来很别扭,但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方式,在符号学层面进行拆解,立刻把它的原形给呈现出来了。
夏洁秋(同济大学文化产业系副主任):
神话是很重要的命题,我们从小受的教育中有很多的神话,它不仅切中了我们的历史,也能够切中现实和对未来。
我是学历史出身的,过去学考古经常说要做考据,我的老师高华,当时上中国近现代史,给我们讲了很多考据方法,我吓坏了。我没有学会考据,所以不学无术。历史学的考据,是要还原一种历史的真实面目。
大可老师的神话,做了很多的考据,也是要还原他希望构筑的神话体系。大可的书是很新奇的,有很多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朱大可老师最近成立了他的工作室,我祝贺他不只是内容的生产者,也将成为奇妙思想的传播者。
刘旭俊(青年批评家,《艺术世界》编辑):
我是在座嘉宾中年纪比较小的,我想谈谈朱老师的写作方法对我们这一代的影响或启发。虽然朱老师是第一次系统性地阐释神话,但是他之前有过很多的零星文章,哪怕写当下发生的事件,也是在用一种解读神话的视角写。
朱老师对我们影响较大的有两个方面,第一,朱老师的神话学考据,做得跟别人完全不同,他先会把一个现象文本化,然后自己再去拆解那个文本。
还有是朱老师的写作风格,他之前也写过诗,他的词语搭配是错位,像“文化口红”之类,这不是一种常态的语词搭配结构。
朱老师写过很多中国古典文化的分析,包括这本神学巨著,我也看到过把这本书跟“文化寻根”做类比的,但我有几次跟同学开玩笑说,我把朱老师的这场写作比喻为“刨根”。
这刨根的意思,一方面是刨根究底,一方面是把原来的东西加以颠覆和重构。我还有一个比较新的看法,是觉得朱老师把神话当作当下的镜像,他书里的世界是远古的全球化,而跟当下的全球化产生了紧密的呼应。
他还借助了上古神学模型,来建构一个现在都无法达成的人类共同价值的根基,他建立起一个来自远古时代的庞大镜像,折射着我们这个当下的世界。
朱珐(青年学者,上海师大古籍研究所副研究员):
我本人也是文献学和神话学的学院派的背景。从学院派的角度看这样的一本神话学著作,可能会造成在学理上对专业学者的挑衅。
我觉得朱老师作为作家、作为学者或是作为思想家的身份是同样重要的,我非常注重他的拆解和建构的双重意义。在这本朱老师的神话学著作上,这种建构的意义最终显现了出来。在这样一本书里,我们看到了那些属于学院派、学理上经得起推敲的东西,至少是让人可以产生学理上的共鸣。
在这本书里我读的最仔细的、最有感触的,是前面的那部分关于“巴别神系”的谱系,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洞见的建构,这里面所下的功夫很让人敬佩。
其中老师提出的神名音素标记,我觉得完全可以画成一个口腔舌位发音图,变成我们所谓的“口腔里的神坛”。
朱老师的野心是要建构人类初期在非洲时的那种“巴别语”,这不仅是“变乱”前的人类语言,同时也是一种神语。当然,它的建构过程是非常艰难的,但朱老师对神名体系的营造,让我们看到了曙光。这是一个非常基础的框架,我们可以通过它的发音部位,把诸神名字在口腔里的那个分布状态,有趣地展现出来。
薛征(青年学者,苏州大学凤凰传媒学院讲师):
对朱老师的这本书以及他的神话学研究,我试着讲一下自己的理解。
我觉得最值得注意的,是他把最古老的对象,跟当代的激进方法结合在一起了,所以我更关注的是他对神话的阐释策略。他在提到自己的精神谱系的时候,跟很多解构主义思想家在精神气质上有些相似。比如说朱老师写过一篇文章叫《流氓的精神分析》,德里达也写过这样一本书,名字就叫《流氓》,朱老师这样的一篇文章是1994年发表的,德里达的发表在2003年,这种精神气质的相似,实际上构成了他与众不同的阐释方式。
我觉得在这本书的重要收获,是提出了世界神话起源的同一性以及中华文明来源的多元性。
因为世界具有共同起源,而使人类共同价值成为可能,更因为整个中华文明的来源是多元的,使封闭的民族主义观念变得非常可疑。
有一幅很著名的画,叫做我是谁?我们从何处来?我要向何处去?如果我们要回答我们是谁,从何处来和向何处去这样的基本问题,朱老师对此做出了自己的有力的回答。
魏英杰(专栏作家,杭州日报评论部主任):
政府花了很大力气搞了一个夏商周断代工程,但许多学者都面临一个很大的困惑:先验地预设二里头遗址为夏王朝遗址。
但这个夏王朝遗址有多大呢?30万平方米,也就是3平方公里的这么大的场所,这难道是一个庞大王国的规模吗?朱大可认为夏只是一个酋邦级别的政治组织(一种部落联盟模式),还没有进化到王国,这就很容易地解释了夏代考古所面临的困境。
总而言之,我觉得这本书重绘了一个上古文明的图谱,对现今的历史学将会产生不小的冲击。
但作为一个有吸纳性的体系,我们不能忽视这种原创声音的存在。我们现有的学术界,很多学者就像工匠那样,总是在学术流水线上寄托着自己的愿望,他只要在一个很小的学术点上取得成绩就很满足了。许多人甚至只是学术搬运工,而且还把非常有趣的研究,变成了很苦逼的活儿,这又有什么意思呢?这本书不仅打破了多学科的壁垒,而且给学术界留下很多原创性的研究方向。
它是一个完全开放的学术共享平台,很多的人可以从中找到灵感和问题点,结合自己的专业再继续走下去。我想它的开放性是不言而喻的。
刘擎:
谢谢魏英杰先生。今天的场合不是一个专家讨论会,但我觉得跟专家一起讨论,会有一场很有意思的对话,说不定会是一场恶战。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夏商周的断代工程出了很大的问题,原因是它是钦定的框架,是为了论证某种政治合法性而做的工作。但大可的东西放在那里,就成了另外一种参照系,它暗示你整个框架可能是错的,你不要自我欺骗了。
朱大可:
刚才大家说了许多,受教了。自己写的东西,大多数已经忘了。我特别容易遗忘。经常会回过头来看:这个是我写的吗?出现了某种距离感和陌生化效应。
我在后记里面说这本书肯定会有很多问题,它是一个公共平台,它不会成为一个自我终结的体系,谁都可以在里面找到自己关注并需要解决的问题。我用粉笔画了一个大大的问题空间,这个地方是大家都可以进来玩耍的。
对我来说,这就够了。
时间有限,我们大家都很疲劳了,我简单说一下,首先是我的写作立场,这是一个自我“他者化”的过程,我经常跟学生说,你不要老是以“我”的立场去想问题,比如“我国”、“我省”、“我市”、“我区”、“我家”之类,只要把自己从狭隘的习惯性思维的空间里释放出来,你就会获得一个全新的世界,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在“他者化”之后,以跨文化的角度去观察、分析和书写。
如果说有什么诀窍,那么这就是我的诀窍。这是我不管做什么的特别重要的一个出发点,没有这个出发点,我几乎无所作为。
第二点想说的是,这本书的第二章大约有5万多字,用一大堆表格,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巴别神系”,这是我整本书的核心,也是最重要的原创。
朱珐刚才说得很好,我的砖头抛给你了,目的是为了勾出你的那个玉来。我只是为你和你们敲开一扇新时代的大门,而那时代的主人,还没有真正起身。
我寄希望于未来。
第三点,整本书的逻辑起点,基于我20多年前的想法。当时我发现了遍及全球的神名音素标记,确信各个文明一定有个共同起源,但我始终找不到足够的证据。
直到看了1988年美国人做的关于人类起源于非洲的论文之后,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我的想法有来自生物学的依据,因为线粒体的研究告诉我们,全世界的人类都来自非洲。生物学从界外给了我一个巨大的支持。
没有这种支持,就没有本书的问世。
我是一个普世宗教论者。无论文明、文化还是信仰,曾经有过全球一体化的时代,它如此辉煌地存在过,以后却破裂和崩溃了,但它终究还会重现。
这是我个人的精神乌托邦,这本书不过是这乌托邦的肤浅的文本表述。它很肤浅,只能触及真相的表层。因为时间有限,我不多说了,再次对大家的到来,表示衷心的感谢,也感谢大家给我这么多指教和鼓励。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谢谢大家!(本文本据录音整理,因篇幅原因,对发言内容做了删节,特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