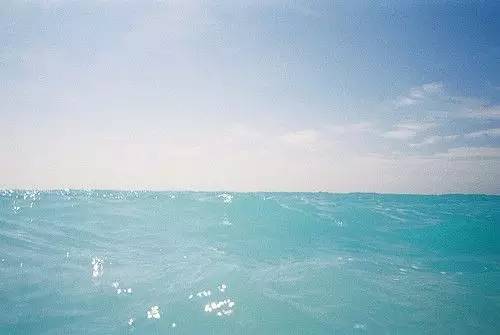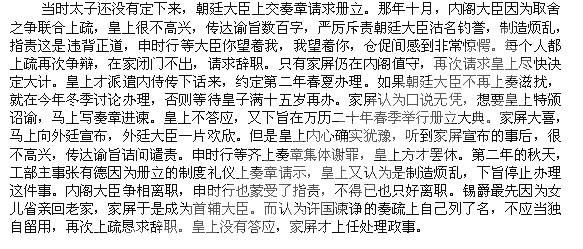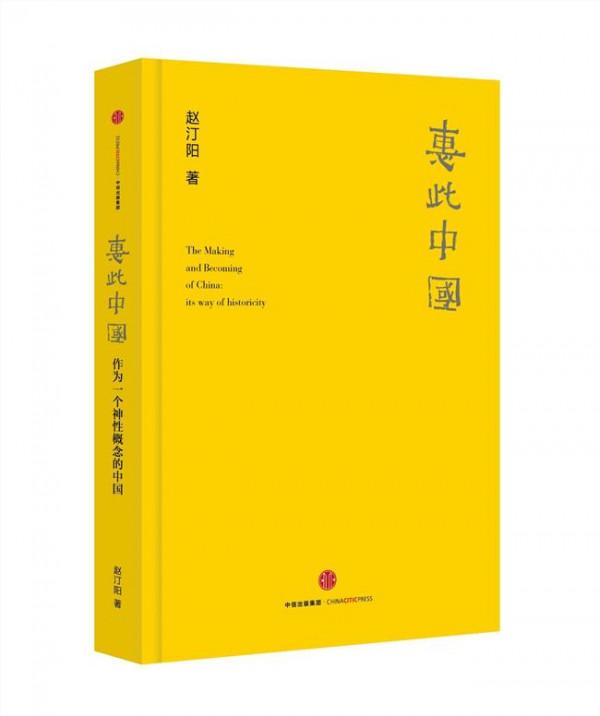赵汀阳是怎样的人 哲学文摘 | 赵汀阳:哲学怎样才是有用的
令人惊讶的是,哲学家们并不去想这些问题,他们按照既定的哲学传统盲目地谈论哲学。按照一般的说法,那些曾经受惠于哲学的各个学科已经从哲学中“独立”出去(这一说法本来就包含着对哲学的误解,其实哲学从来没有包容过各个学科而只是为各个学科做过一些工作),尽管如此,哲学家却总以为,总有一些特别大的而且几乎注定是解决不了的问题为哲学空想留出余地,所以哲学家继续构造纸上的世界和生活。
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这“只不过是不同地解释了世界”。更糟的是,精疲力竭的哲学的想象力已经如此贫乏以至于只不过是不同地解释了对世界的解释。
并非所有问题都值得一想。尽管哲学的确思考一些“大问题”,但值得一想的哲学问题首先是因为有用而不是因为“大”。可以说,哲学问题是有用的问题中的大问题,仅此而已。因此,哲学的首要工作是考察一个提供给哲学的问题是否是一个有用的问题,其次的工作才是考察对一个问题的解答是否有意义,哲学不能由于一个问题是“大的”就盲目投入工作。
强调哲学的有用性就是要求哲学恢复它对人类行动的积极意义而不再只是一种可有可无的“高级的”精神修养。
当然,哲学的有用性不是直接的。有一句众所熟知的口号可以用来表达这种有用性,这就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对于哲学来说,我把这一口号具体地理解为:一个哲学问题如果是有用的,而且仅当它是在人类实践中被提出来的;对一个哲学问题的解答如果是有意义的,而且仅当它是人类实践所必需的。
前一种有用性可称为“来源上的有用性”,后一种则可称作“应用上的有用性”。这两种有用性都是哲学思想必不可少的。缺乏这两种有用性的“哲学”就是平白无故的无聊思想,也许那种无聊的思想可以被美化为纯粹精神上的闲适游戏,但毕竟是不重要的而且还往往助长人类思想中混乱荒谬的倾向。
长期以来,哲学沉溺于无用的思想,其中很可能有一个原因是哲学一直就没有能够确切地表明哲学是为了什么而进行工作的,这一点很容易使哲学滑向某种无节制的谈论,而且其中有一部分谈论的意义仅限于谈论,例如就一些人们关于世界和生活的看法表表态或者制造一些“抽象的”神话。
当哲学不能表明哲学为了什么而工作时,它就会盲目地遵循其历史传统而进行习惯性的工作。对历史传统的崇拜使得人们似乎只能从哲学史去理解哲学,甚至去定义哲学。哲学史的确表明了,在“哲学”这一名下,人们做了些什么事情。
但是,这并不等于表明了所做的这些事情都是恰如其份的,而且,由过去所做的事情尤其不能推论出现在仍然必须做这些事情。因此,哲学不是由其历史传统所定义的,而是由它所发挥的作用所定义的,或者说,哲学史仅仅表明了哲学在过去的作用而不能表明哲学在今天必须发挥的作用——哲学的作用不是由哲学自身设想出来的,而是人类整个思想发展状况所要求的,于是,在不同的时代和条件下,哲学的工作任务是不同的,哲学决不能被埋葬在一些千年不变而且永远解决不了的问题中。
可以说,哲学自身根本不能自己给自己制造问题(那些糟糕的哲学已经制造了太多的精神乌托邦而且比社会乌托邦要荒谬得多)。任何一个有价值的哲学问题都是某一个具有实际意义的思想领域所产生的问题,这种问题特别之处在于它本来不是一个哲学问题,但由于它不能在实际的领域中被解决,因此转变为一个哲学问题,所以确切地说,所谓“哲学问题”其实指的是必须在哲学中被解决或者说只能以哲学的方式去解决的实际问题。
哲学根本不是一个精神地主,它不会有自给自足的一些财产,而是一个精神工人,它只有一些特殊的能力(方法和技术)。
哲学在形式上虽然高度理论化,但在实质上必须是应用性的,所以说,任何一种有价值的哲学都是一种应用哲学。哲学不是一切胡思乱想的保留地。
一开始我就提到哲学曾经是有用的,这既意味着传统的哲学思考在过去的思想背景下恰当地发挥了作用,又意味着这种思考传统在当下已经失去作用。在人类早期的知识-思想背景下,各个知识-思想领域中的问题仍然是被含糊地提出而且被含糊地回答,其中暗含着许多一时不能克服的混乱和矛盾,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哲学在各个思想领域“之上”给出一些所谓“总的”、“根本的”或“整体的”原则可以说是有用的,因为在实际问题尚未被清楚地揭示出来之前,哲学式的含糊恰恰是清晰思想得到发展的一个条件。
如今,在各个知识 ̄思想领域已经清清楚楚得到发展的情况下,哲学式的含糊也就不再有用,哲学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原先的那种随便发言权。哲学关于世界的那些“总的”看法注定只能有这样一些遭遇:(1)如果这些总看法与科学一致,那么是多余的,因为科学比这些看法更清楚更确实地表达了世界;(2)如果这些看法与科学不一致,那么是无用的,因为科学被证明是有用的;(3)如果这些看法被认为是在科学之外的对世界“本质”的独特见识,那么只不过是文学的,因为对无法触及的东西的见识只能是想象。
既然关于世界的“形而上学”(即元科学)是无用的,传统哲学的知识论和命运也就被注定了,那种关于世界知识的一般性质和结构同样是多余的或者无用的。
至此已不难理解我为什么认为哲学必须由“元科学”(metaphysics)转变成“元观念学”(metaideololgy)。在其中我丝毫没有贬低哲学过去的作用,所以所要求的不是对传统哲学的否定而是告别。现今的人类思想状况要求哲学从事另一种有用的工作。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不得不改变“哲学”这一概念。这种改变只不过是要使哲学以新的思考方式成为有用的思想。比较简单地说,传统哲学是在观念中面对世界问题的思考,是观察者的哲学;新概念的哲学则是在世界中面对观念问题的思考,是行动者的哲学。
既然人类已经拥有科学这样一种清晰有效的表达世界的方式,传统哲学方式就退化为就一些无关紧要的困惑进行无关痛痒闲谈的方式,这种老化了的哲学也许可以作为一种文学继续存在,但由于缺乏必要的艺术性因此只是一种价值不高的文学。
新概念的哲学虽然不再谈论那些不着边际的关于世界的本质和存在的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老式知识论,但决非脱离世界去进行思考(“面向观念界”这一主张的确很容易引起误解),恰恰相反,新概念的哲学更实在地对待世界,它把世界接受为一些显然的经验事实而不作出胡思乱问,并且在这样的世界中去审问那些决定行动的观念。
人类的真正存在主题不是作为观察者去猜想存在,而是作为行动者去制造存在,因此,人类的真正思想主题就是如何制造存在,更明白地说,就是怎样行动。
在这其中,哲学作为思想的一部分,所从事的工作应该是对决定行动或者说对行动有用的基本观念进行反思。
我们必须意识到,哲学并不等于哲学史或哲学传统所表明的东西,而是人类思想当下所需要的某种特殊的反思方式。由此也就可以看到,没有哪一个哲学问题是“永恒的”谜。有时人们喜欢说,哲学问题是一些“最大的”永远不能完美解答的问题,其实,我们很难想象那些大问题到底是些什么问题,或者说我们根本不知道那些问题到底问的是什么。
这些不恰当的问题之所以看上去是一些“大”问题而且似乎总能通向无穷多种解释,恰恰是因为它们是含糊不清地被表达的。
另外更重要的是,我们也不知道那些问题即使获得某种解释又会有什么用。哲学作为一种特殊的反思方式,它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把一个问题改造为一个显然可解的问题,甚至可以说,所谓解决一个哲学问题只不过就是改造这个问题。
对哲学的这种期望与现代流行的分析哲学态度几乎是相反的,分析哲学所能做到的事情仅仅是消解哲学问题——放弃关于世界的胡思乱想而面对现实世界——这种做法无疑表明了清醒的头脑但却根本没有尽到哲学的职责。哲学必须能够进行对行动有用的思想决策,必须建设性地解答问题而不仅仅保持一种袖手旁观的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