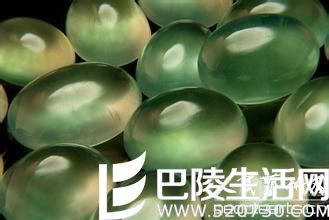朱良志的作品 千年石上苍苔碧 落日溪回树影深丨朱良志谈生命的态度
松尾芭蕉那首著名俳句有助于我们说明这一问题:“当我细细看,呵!一棵荠花,开在篱墙边。”在一个偏远的乡村小路上,在一处无人注意的篱笆墙边,诗人发现了一朵白色的野花,没有娇艳的颜色、引人注目的造型、诱人的香味,但却独自开放,它没有羞怯,没有哀怜。
一朵野花,就是一个宇宙。从人的角度看,这朵野花和这篱笆角落一样微不足道。但野花可不这样“看”,它并不觉得自己生在一个闭塞的地方,也不觉得自己的形象卑微。在人的眼光中,有热闹的街市,有煊赫的通衢,也有人迹罕至的乡野,我们给它分出彼此,分出高下。我们眼中的花,有名贵的,有鲜妍的,也有浓香扑鼻的,像山野中那些不知名的小花,我们常常以为其卑微而怜惜它。
其实,大和小,多和少,煊赫和卑微,高贵和低下,灰暗和灿烂,那是人的眼光,是人的知识眼光打量下所产生的分别。中国哲学强调万物齐一,诸法平等。或者可以说,中国的道禅哲学,是将被人的知识剥夺的世界意义还给世界。
在“人为世界立法”的眼光中,我们站在世界的对岸看世界。这样的世界是被人的理性、情感等过滤过的,而不是世界的真实相。像文徵明《水墨山水轴》的题诗说:“密树含烟暝,溪山过雨青。诗家无限景,都属水边亭。”⑩在纯粹的体验中,此在就是全部,当下就是圆满,没有缺憾,一个黄昏下目对青山的空亭,就是无限的宇宙。
像吴历“一带远山衔落日,草亭秋影淡无人”诗中所呈现的那样,无人即是有人,落日山影,草亭空阔,与我心如如自在,没有分别,更无别虑,就是一个圆满的世界。明姚绶曾画《秋风晚笛图》,自题诗云:“船头晚吹笛,雁冲芦荻秋。风高柳枝脆,江水空悠悠。”笛声浸被了一个世界,一天的秋意,皆从这笛声中领取。
人不能成为这世界的暴君,将世界上一切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或者居高临下地“爱”它,或者悲天悯人地“怜”它。一朵小花也有存在的理由,也有存在的价值,它不因人的存在而存在,不因人的评价而改变,只是自在兴现而已。“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青苔石上净,细草松下软”,等等,人淡去了,但随那空花自落,细草芊眠。当你以物为量,你就会有王维等诗人那样的感动,就会在一朵微花之中,发现一个宇宙,一个有意义的世界。
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中,我们可发现“创造一个与自我生命相关的宇宙”的真实意义。在这样的“境”中,诸法平等,人不是观者,不是知识的裁判者——或判它有无实用价值,或给它贴上科学的标签,或细致地审视它是否符合美的形式感,像沈周诗中所说:“我来亭上已春深,渐见飞花换绿阴。
犹有啼莺相慰藉,数声春赋惜春吟。”人融入了世界,没有了世界决定者的角色,一切都自在兴现,物获得了意义,物变成了非“物”,人所坚守的能所关系随之解体。像李日华《竹》诗中所说的:“庭空月无影,梦暖雪生香。”中国艺术的“境”呈现的就是这样无影无迹的印合。
“境”并不是中国传统艺术观念中情景交融理论所能概括的。情景理论强调情中有景,景中有情,情景结合,王夫之说:“景中生情,情中含景,故曰,景者情之景,情者景之情也。”景是情之媒,情乃景之主。在这里情与景相对而生,互相关联,互相生发。而中国艺术理论中的造“境”学说,正要泯灭这样的相对而生的思想。“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的山中芙蓉,是自在兴现,没有被观之景,也没有对景之心。情景理论没有超越能所之别。
3.与世界做“游戏”。在这个境界中,人的观照对象、控制对象的主体意识淡出,但人没有淡出,在这个自由灵动的世界中,人在与世界做“游戏”。这个平等的参与者在分享活泼世界的乐趣。
如王维《书事》:“轻阴阁小雨,深院昼慵开。坐看苍苔色,欲上人衣来。”四句小诗,却创造一个寂寞而深邃的宇宙。凡常的小院,紧闭的院门,阴沉沉的天气里,寂寞的主人就坐在窗前,眼前是密密的小雨,满目的苍苔,更衬托出院落的幽深,诗人的心,宁静,寂寞,也似乎被这幽深和绿意席卷而去,带到那个无可奈何的世界中。
诗写得湿漉漉的,充满了梦幻般的感觉。简单的物事,却创造了一个无限回旋的世界。苍苔、小雨、庭草,都成了诗人的对话者,成了诗人游戏的对象。
诗人没有着意去写景,写人的情感的变化,写人的意志的控制,而是写一些与自我生命相关的存在者,由这样的存在者共同构成一个意义世界,这就是诗人所造之“境”。这是生命的吟咏,也是生命的叹息。
寂寥中透出愉悦,萧瑟中露出活泼。诗人的心似乎被这小雨和绿意打湿了。王维另一首小诗也极具风韵。《阙题二首》之一云:“荆溪白石出,天寒红叶稀。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11)很多画家画过王维这诗境(如石涛)。
漫山的空翠打湿了人的衣服,其实也打湿人的心灵。这片令人神往的世界,你一旦接近它,就会被它包裹,被它挟持;你会融入它的世界中,投入它的怀抱。诗人不是写自己喜欢这片山林,写山林的诸般美景,而是写这个与自我生命相关的宇宙,和自己彼此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