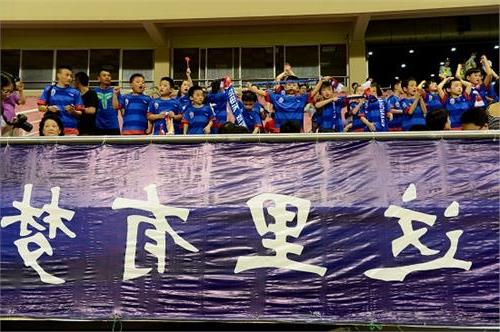郝景芳采访 独家专访郝景芳:中国第一位获得雨果奖的科幻女作家
8月21日上午,几乎就在女排夺冠的消息传来同时,第74届“雨果奖”颁奖典礼在美国堪萨斯举行。中国科幻女作家郝景芳凭借作品《北京折叠》获得最佳中短篇小说奖,成为继“大刘”刘慈欣之后第二位获得雨果奖的中国作家。
“雨果奖”由世界科幻协会颁发,被公认为最具权威与影响的世界性科幻大奖之一,堪称科幻艺术界的诺贝尔奖。
在“中短篇小说”竞赛单元,郝景芳战胜科幻大师斯蒂芬·金的提名作品《讣告》实属不易。去年获奖的大刘曾对媒体表示,“中国科幻仍处于不太成熟的阶段”。但郝景芳让我们看到,那些写科幻的年轻人正在异军突起。他们用理科生的眼光冷眼旁观这个比科幻更离奇的现实社会,再去用想象力构筑一个美好,或是不甚乐观的乌托邦。
还记得今年4月,雨果奖提名公布的第二天,郝景芳发了3条朋友圈。
一条是提名小说《北京折叠》的全文链接,来自她的个人博客;一条是一位科幻圈好友连夜给她做的采访;一条是她几年前写的《论一个清华学渣的自我修养》,来自清华大学官微。
然后她就收手了,“不要再招摇了”。
见到郝景芳是在提名公布两个月后,北京的一个周末上午,隔壁桌的两个男人在大谈 IP,有点吵。两个月间,她尽可能地推掉了大多数采访。同为科幻作家的好友陈楸帆说,不光是媒体,很多影视公司,甚至还有想做她经纪人的都找了上来,大部分都被她拒绝了。
你可以把这看作是一种理科生式的冷静克制。天体物理学出身,经济学博士,这是郝景芳大致的学术背景。博士毕业后,她进入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工作,从事宏观研究,为政府提供政策参考,“类似于智库的存在”。
起笔写科幻是大四的事情,她给一个科幻征文大赛投了篇名叫《谷神的飞翔》的小说,由此认识了《科幻世界》的两位编辑,开始为杂志供稿。这次获封雨果奖最佳中短篇的《北京折叠》便是一篇2012年的退稿,后来被她直接发在了清华大学的 BBS 上。
一篇被杂志退掉的稿子,最终却得到了世界科幻界最高奖——不出我意料,郝景芳并没有打算把这当成是一件值得大惊小怪,乃至“励志”的事情。她有这个底气。
“我在开始写科幻的时候,不断有人跟我说,你这样的风格写不下去的。那难道我现在和当时又有什么不同吗?没有什么不同,我原来写东西的缺点也都还在。所以说,我在那个时候感受到的挫败感和现在得到的称赞,其实都是虚的,我自己依然是一个连贯的个体。”
《北京折叠》并不是一部典型意义上的科幻小说,从设定以及行文来看,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部反乌托邦小说,类似《华氏451度》《美丽新世界》,以及对郝景芳影响颇大的《一九八四》。科幻作家宝树当年在 BBS 上读到这个故事后便觉得很特别,“太空未来、宇宙冒险、打怪升级这些浪漫色彩它全没有,几乎就是一个现实主义”。
除了能像变形金刚一样折叠起来以外,郝景芳笔下的北京城和当下相比,科技的发展程度表面看几乎没有任何不同。而“折叠”这样一个散发着工业时代气息的物理行为,就是整部小说唯一的“科幻元素”。
与《盗梦空间》的天马行空不同,《北京折叠》中城市的的折叠形式是机械而系统化的,且背后有着复杂的政治经济动因
上面是郝景芳为我们解释“折叠北京”的原理时,随手勾出来的示意图。在这样一个折叠地表的结构中,北京城的空间被划分成了3层:
每到清晨,空间休眠,大地反转,城市折叠。不同空间的人彼此隔绝,跨空间活动则被视为违法行为。这种物理意义上的折叠和区隔背后是现实的政治经济考量——第三空间居民大多从事的是垃圾处理的工作,为前两层空间打造“循环经济”的同时,也解决了整个城市的剩余劳动力问题。同时,空间的隔绝使得三个阶层间的物价不会彼此影响浮动,社会结构得以维持平衡和稳定。
郝景芳将这个故事定义为一个“关于不平等的小说”。与当下世界各国的现实相对照,她将小说中所构造的社会制度看作是对失业问题的一个“看上去不太美好,但尖锐,且现实的解决方案”。社会体制的变革,以及普世困境的解决方案,一直都是这位看似纤弱的女生试图在头脑中探索的宏大主题。
“在《北京折叠》这部小说中,我提出了未来的一种可能性,面对着自动化、技术进步、失业、经济停滞等各方面的问题。同时,我也提出了一种解决方案,有一些黑暗,显然并非最好的结果,但也并非最坏的:人们没有活活饿死,年轻人没有被大批送上战场,就像现实中经常发生的那样。我个人不希望我的小说成真,我真诚地希望未来会更加光明。”
——郝景芳雨果奖获奖发言
去年年初,《北京折叠》被华裔作家刘宇昆翻译成英文版,发表在《Uncanny》杂志上。今年4月底,它被宣布入围雨果奖最佳中短篇小说。与此同时,去年《三体1》获奖后的网络口水战也再次上演了:《折叠北京》得以提名,是否是因为其中的政治倾向**了西方评论界的口味,简言之,即“抹黑中国”?
这似乎是所有“墙内开花墙外香”的艺术作品所遭遇的共同尴尬——远在土耳其的奥尔罕·帕慕克们会遇到,中国的所谓“第六代导演”们会遇到,刘慈欣们也注定绕不开这个问题。
在艺术上,这种问题固然不具备讨论的价值,如刘慈欣所言,“不是每一个个体读者的意志都会受到意识形态强烈的左右”。但怎么说呢,我其实忍不住在假想,郝景芳或许可以把将这样的一场“艺术讨伐行动”写入未来的科幻作品中,其背后的社会心理越是细想,越是迷人。
Q:《北京折叠》作为一篇科幻小说,它所探讨的更多的是一个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的问题,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安排?
A:我自己确实是对社会制度非常感兴趣,包括我之前的长篇小说(《流浪苍穹》)其实也主要是在探讨社会制度。《北京折叠》也好,《流浪苍穹》也好,都是我能想象出的一系列社会制度中的某些case。我喜欢做这样的头脑实验:假如在这样的一套社会制度下,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人会怎么想,换另外一套社会制度,人又会怎么想。
Q:像是一种社会学实验。
A:对,只不过完全是在头脑中进行的。这一切的出发点都是一个“what if”的问题,在《北京折叠》中,这个“what if”的安排就是,所有的人在物理上都见不到彼此,时间上也见不到,会怎么样。当我读一些政治或历史方面的书时,我也会想,如果这样的条件当时发生那样的变化,会导致什么。这其中最有意思的就是去进行各种可能性的探索和试验,去探讨不同的可能性。
Q:那么,为什么是北京呢?你可以把这个故事架构在任何地方,在巴黎,在孟买,在冥王星,在克卜勒-452b,都没有问题。为什么一定要是北京?
A:北京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mix”的城市,既有政治的中心,也有经济的中心,还有那么多外来人因为各种各样的理由在这里居住。在这个地方呆久了,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觉,每天跟不同的族群打交道,就像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一样。
另外一点是,北京这个地方还不完全是,起码在现实生活中不完全是一个纯粹市场化决定的地方。像纽约的话,起码在市中心曼哈顿岛上,人是非常同质的,你不会在那里找到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结构,那是一种市场化到了极端的情形。但北京不是,虽然它也有金字塔形的结构,但是它还有包容性和人为安排的因素在里面,使得这里比世界上的很多大城市都要更复杂一点。
Q:为什么你会把《北京折叠》定义为一个“关于不平等的小说”?是什么样的经历让你尝试在科幻作品中表达这样的议题?
A:这个问题最早的一个来源是我上学的时候,一个学生组织带我们去一些不发达的地区支教,去的是甘肃山区。在那一个月里,对我们来说比较困扰的是,他们到底需要什么,我们能传递给他们什么。
这个其实是当时触发我的一个现实中的因素,由此延伸以后,我对这个问题更多的是一种学理上的兴趣。我在学校读经济史的时候,学的都是马克思的理论,但现实中肯定就会有一些疑问:去缩小这种收入差距,都能有哪些方法,用这样的眼光去看历史上发生了特别大的贫富差距的时候,当时的政府会用什么方法去解决。从古希腊,到中国历史,这个矛盾一直都在的,你可以观察到很多这样的case。
Q:一直到现在也都是如此,包括最近英国脱欧的事情,还有美国的川普现象,病根很有可能都出在社会内部的分化上。
A:这个问题在学术上也是我们最近经常会讨论的。全球化的这个过程,实际上一直都有这个问题,它的受益人群是不一致的,全球化往往是所谓上层阶层受益,下层阶层受损。在未来,我们能看到的前景就是,“逆全球化”一定会上演,国内的矛盾都已经上升到了不可抵挡的程度,川普也会逆全球化,欧洲也正在逆全球化,各种保守主义和孤立主义其实都是这个问题的弥补之道。
其实你要是能对比一下的话,这个过程并不是全新的,这和一战前的情形是非常相似的。
Q:在你的长篇小说《流浪苍穹》中,地球这一方的体制其实就是一个全球化发展到极致的结果,而火星一方则是一个乌托邦,这也是你的一种(社会学)实验吗?
A:其实小说里的地球也是另一个乌托邦,是一个全球化发展到极致的乌托邦。这是科技和互联网带来的一种趋势,发展到极致以后,经济的力量便足以克服各国政府的力量,所有的劳动力在全世界自由流动,达成一个商人主导的社会,当然,也有可能是网红主导的社会。
《流浪苍穹》
但是在火星上,你可以看到贫富差距最小的一个社会,但是又缺少了更多的自由,谁也不能通过这个经济系统赚得比别人多。这两个世界在现实生活中都不可能存在,但小说的魅力就在于这里,不存在没关系。小说就是唯一一个你可以撒谎还不用负责的东西。
Q:刘慈欣曾经谈到过“女性科幻作家”这个群体,他说女性作家和“软科幻”没有必然联系,中国女性科幻作家的理工科背景比男作家还深厚。那么在你看来,“女性”这个身份对你的科幻写作是否有所影响?
A:从写作的风格来看,我不是特别喜欢那种纯以技术为核心的作品。我写作也好,我喜欢看的东西也好,技术本身还是背景性的,是一个一切的“setting(设定)”,但你要讨论的是里面人发生的事情,人之间的关系,可能这种特点偏女性化。
但是其他的我没觉得有太大的不同,我也不是很喜欢专门以女性为主角,或者专门探讨女性的情感,还有女性的地位和权利。我感兴趣的更多的是普遍的关系,普遍的人的理想和困扰,这些东西在我看来是男女共通的。
Q:所以我们会在你的小说中看到更多生活化的细节,而不是技术的细节。
A:我觉得科幻小说始终是一种文学,不能把它从文学这个圈子里面脱离开去。从文学上来讲,我喜欢那些挖掘自己内心想法的作家,比如塞林格,他写东西会非常真实地触摸个人的体验,他的文字是可感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小说家的职责,他能够真正的感觉到生活中那些触感。加缪的书也是这样的,他就是那种对生活有真实触感的人。有的作家可能相对来讲观点比较多,读多了就觉得接触不到真实的生活。那种作家喜欢写的不是描绘,而是评论。
Q:《北京折叠》的英文版翻译是刘宇昆,你对他这次的译本怎么评价?
A:这件事我还蛮幸运的。我是2012年在一次科幻活动上认识他的,他这些年来一直在热心的在帮我们这些国内作家翻译。他其实是出于一种使命感在做这件事情,这件事情中,他自己的收益真的很少,付出的精力却是巨大的。他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译者,会和你来来回回地沟通。更重要的是,他的语言能力很强,不光中文很好,他基本可以把英文当成母语写作,两种语言都很通。如果换成其他译者,可能不会有这么好的效果。
刘宇昆是《三体1》英文版的翻译,他本人也一直是雨果奖所青睐的作家
Q:刘宇昆自己的作品,包括之前拿过雨果奖的《手中纸,心中爱》,我个人觉得有一种倾向,他对科技高速发展的未来似乎抱持一种非常悲观的态度,你觉得呢?
A:这不光是他的态度,应该可以说是一种集体思潮。你看19世纪,凡尔纳的那个时代,大家对未来是一种比较乐观的态度。但是到了黄金时代就已经有点反讽的味道了,也有很多反乌托邦的小说。到了最近这几十年,确实大家对未来的悲观会更强一点,科学的进展虽然很了不起,但是解决问题的同时,带来的问题也很多,它不可能解决人类的所有问题。因为不存在这样的科技,不存在永远的乌托邦,所以总会有一些悲观的情绪。
Q:那么你对当下中国现下所谓的“科幻热”怎么看?
A:我觉得“科幻热”很大程度上就是《三体》热。目前为止,也没有其他作品像三体那样得到广泛的传播,所以这种科幻热能不能持续也是说不好的事情。另外一点,这其实也是一种资本热,现在资本太多了,值得投的项目也比较少,所以才会翻来覆去地炒IP。所以这也不能说是科幻本身的热,只不过是市场使然。我觉得不要对这个事情太当真了,可能过几年风向又不一样了。对于作者来讲,写作还是一样的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