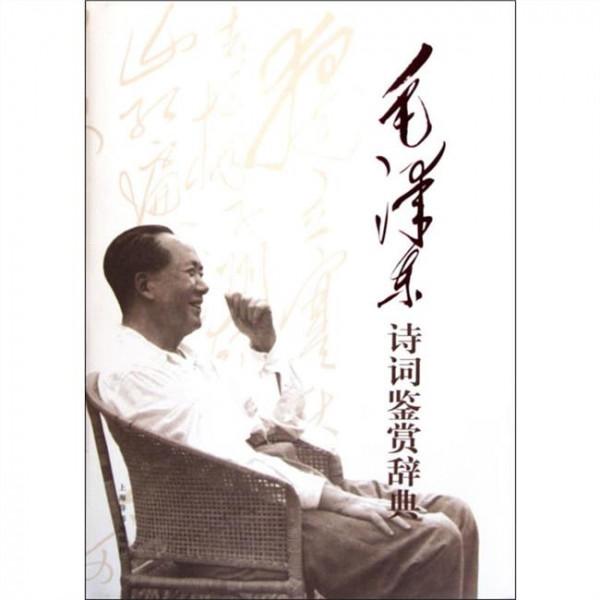丁玲与胡也频 丁玲、胡也频与沈从文的群租日子
1925年,文学青年丁玲和胡也频爱情而且同居了,他们搬到香山住,快活得如同神仙。另一位文学青年沈从文则经梁启超和北京大学教授林宰平的介绍,到香山慈幼院图书馆当就事员。这三自个,在1925年的秋天认识了。
沈从文
胡也频
丁玲
沈从文说,这时分的丁玲,俄然脸上有了那种“新妇腼腆的光芒,神情之间安静了些也温顺了些”1。他们很快成了不错的兄弟,没饭吃,便来找沈从文一同吃慈幼院大厨房的粗馒头;情侣吵架,其间的一个便来找沈从文倾诉委屈。
后来,他们三自个便住在一同,一同住进公寓,包含汉园公寓等,这好像是他们“同居三人组”的初步,后来无论是北京仍是上海,这么的合租形式坚持了很长一段时刻。李辉教师在《沈从文与丁玲》一文中说,汉园公寓主人的儿子黄伯飞多年后回想,沈从文的房间是高楼后座二楼左角的一间,他和沈从文的房间仅仅一墙之隔。
沿着左面走廊的两个房间,一间是胡也频的,一间是丁玲的,当然,这两个房间里边是相通的,胡也频和丁玲只用接近楼梯的一个门口收支。
在北京的日子看起来惊涛骇浪,虽然有很多人说胡也频从前置疑过沈从文和丁玲的豪情,但很快他便发现,实在的“情敌”当然不是沈从文,而是冯雪峰。当这三自个再次在上海团聚的时分,他们现现已历过一番“从前沧海难为水”的豪情风云。
法租界萨坡赛路204号(今日的淡水路),这是一幢值得留念的房子,在这儿,有三个青年,他们日后都变成我国文学史上主要的一笔。他们在这幢房子里创办了红黑出书社,并出书了《红黑》杂志,随后初步出书“二百零四号丛书”。
与此一同,他们还为人世出书社修改出书了《人世》杂志。施蛰存回想,萨坡赛路204号好像在一家牛肉店楼上,他有时去访问,“从文都在屋里写文章,编刊物,管家。他们三人中,丁玲最善外交,有说有笑的,也频仅仅偶然说几句,帮衬丁玲,从文是一个彬彬有礼到有些羞怯的青年,仅仅眯着眼对你笑,不多说话,也不喜爱一自个,或和兄弟一同,出去逛马路漫步”。
3赵景深则说,冬季的时分去看望他们三自个,竟然惊奇地发现,丁玲的字几乎和沈从文的一模相同,“可见他们三个是多么要好了”。
我常常写到这儿,都期望就此打住,由于这是这三自个可贵的团结友爱时刻,在这个春天,就像沈从文在《人世》创刊号上所写的“卷首语”那样:“初步,第一卷本刊,出完事,没有啥可说。几个白痴,来做这事,大的期望,若说还有,也不过期望还有很多白痴来做本刊读者罢了。”4那时,他们是美好的,虽然不久今后,他们行将走上不相同的路途,由于他们太不相同。
由于联系好,又由于这独特的两男一女联系,上海滩当然少不了有关他们的闲言碎语,无中生有的小报音讯,随声附和的八婆们兴奋地传说着他们“大被同眠”的细节。一向到好久今后,还有研究者谈起这段“三角恋”。所谓“大被同眠”,八成起源于李辉英写的《记沈从文》:“他们能够三人共眠一床,而不感到男女有别,他们能够共饮一碗豆浆,嚼上几套烧饼、果子,而打发了一顿餐食。
有了钱,你的即是我的,全然不分彼此;没有钱,躲在屋中聊闲天,支配了年月;兴致来时,逛北海,游游中山公园,又三自个同趋同步,寸步不离。
”最早的说法着重的是“不感到男女有别”,由于他们是那么好的兄弟,况且依据黄伯飞说的,他们三自个并没有住在一间房间里。而到了上海,虽然租在一幢房子里,但不久今后丁玲的妈妈、沈从文的妈妈和九妹也来到了上海。胡也频、丁玲和丁母住二楼,沈从文和妈妈、小妹住三楼。
更主要的是,沈从文和丁玲,真的不是彼此的那杯茶。1980年,夏志清问访美的沈从文,和丁玲是不是有过“罗曼司”,他答复说:“没有,仅仅兄弟。”1983年,丁玲在美国的时分被问及相同的疑问,她答复:“没有,咱们太不相同了。”
是的,丁玲喜爱的男生,从胡也频到冯雪峰,从冯到达陈明,这四自个都是那种看起来充溢革新斗志的“勇士”,而沈从文,则沉溺在他喜爱的那些花花草草中,这不会导致丁玲在情感上的认同。而后来火热寻求张兆和的沈从文,当然也不会喜爱大大咧咧男孩子气的丁玲,就像他首次看见她时的评估:“不像个女子。”
一向到1931年,这三自个的友谊都是牢不可破的,虽然他们的政治观念现已发生了极大的改动。那个转折点,来自安定铁三角中一方的不见。1931年新年,沈从文从武汉回上海度寒假,那时他现已变成武汉大学的教员,而丁玲和胡也频也在这时从济南逃回上海,他们的孩子刚刚在1930年的冬季出世。
1月17日,沈从文回到上海刚刚10天,这天正午,他见到了好兄弟胡也频。胡也频想请沈从文为房东刚刚死去的儿子想一副挽联,约好下午一同到他家去写,他从沈从文手中拿走6块钱,便和他一同上街。他们从北四川路往南走去。胡也频说要去买写挽联的白布,就和沈从文分手了。
下午,沈从文践约来到丁玲家里,胡也频没有回家,他有点担忧:“他约好我来写挽联,他这时还不回来,难道路上被狗咬了。”
丁玲毫不在意地说:“不妨碍,身上并不带啥东西。”
“他应当当心一点,他那么洒脱,我为他忧虑。”
“从文,照你这么胆怯,真是啥事都不能做!”
胆怯鬼沈从文的预见是对的,胡也频被捕了。第二天黑夜,在外面找了胡也频一天的沈从文回到家里,发现一个白叟在等着他:“把那个老家伙一把拉回房中,我就问他一些信上还未提及我却有必需知道的作业,这送信人把头仅仅乱摇,用手点拨拿在我手中那个信,‘你看这个’,我所以再看了一次,方发现那揉皱了的纸角上,水兵学生还写了一行很小的字,那行字是‘刻不容缓,从速为我主意取保。
信送到后,给来人五块钱。’”(《记丁玲女士》)胡也频的纸条上写着:“我遇了委屈作业,昨日过你住处谈天,从住处出来到先施公司,遇女友拉去东方旅馆看个兄弟,谁知到那里后就被他们误解拘捕了。
请你费心向胡先生蔡先生一求,要他们设法保我出来,请吴经雄律师,乘我还不搬运龙华时,进行诉讼。
你理解我,全部必须从速,不然日子一久,就厌烦了。奶奶处请你照料一声,告她不用忧虑。我的作业万不宜迟,迟了会生改变。我很着急!……”这和丁玲的回想有些收支,丁玲在《一个实在人的终身》里着重的是,胡也频说“要咱们放心,要我转达安排,他是决不会屈服的”。
受胡也频的嘱托,沈从文初步解救作业,这并不是他拿手做的作业,但他一向在做,他并不懂得他们的那些主义,他仅仅在用他湘西人的那股子对兄弟的热心在南京和上海之间频频奔走。他托胡适,写信给蔡元培,还去南京找一些国民党要员,他乃至还去找过任国民党中心宣传部部长的陈立夫,陈立夫通知沈从文,胡也频的案件很大,不过“假如胡也频能容许出来今后住在南京或许能够想想方法”。
(丁玲语)丁玲当下答复:“这是办不到的。也频决不会赞同。他宁肯坐牢,死,也不会在有条件底下得到自在。我也不情愿他这么。”
在这点上,沈从文的确是天真的,依据当事人的描绘,陈立夫的确有唐塞沈从文的嫌疑。在快到两个小时时刻里,他和同去的兄弟,只能听陈立夫一自个在那里大谈啥“民族主义文学”,终究他才有时机就胡也频的作业求陈立夫:“我以为政治假若皂白不分把作家捉去当土匪定罪,恰恰是和其他一种用三块钱千字的方法,带点儿慈悲性质,办杂志收留作家算是文艺方针,相同的极端不智。”
沈从文能做的,除了茫无头绪地四处托人,还有陪着丁玲去龙华监狱探监。丁玲记住这天气候很冷,空中飘着小小的雪花,是她请沈从文伴随前往:“咱们在那里等了一上午,容许把送去的被子、换洗衣服交进入,人禁绝见。咱们想了半响,又恳求送十元钱进入,并恳求能得到一张收条,这时铁门前看望的人都走完了,只剩咱们两人。
看守的容许了,一会,咱们听到里边有一阵人声,在两重铁条门里的宅院里走过了几自个,我啥也没看明白,从文却看见了一个熟识的影子,咱们断定是也频出来领东西,写收条,咱们专心致志地等着,公然,我看见他了,我大声喊起来:‘频!
频!我在这儿!’也频也调过头来,他也看见我了,他正要喊时,巡警又把他推走了。我对从文说:‘你看他那样多有精力呵!’”
这是沈从文、胡也频和丁玲这三自个相遇的终究一幕,好像也是他们友谊的终究一刻。在陈立夫那里碰了钉子今后回到上海的当天,他们便得知,胡也频等现已在2月7日被杀戮。沈从文说,丁玲在得知这个音讯今后,一向十分镇静,她没有哭,一滴眼泪也没有流。
三人组中的一自个,从这个国际不见了,剩余的两自个为了逃避风险,曾有过一段时刻短的同住。沈从文在淮海路的万宜坊邻近一家杂货铺的楼上租下一个住处,他住一间,丁玲和他的九妹住一间。丁玲很少下楼,仅仅在晚间才偶然到街上逛逛。
而沈从文由于忙着解救胡也频而耽误了武汉大学开学的时刻,他便抛弃了讲师职位,照料丁玲和胡也频的孩子,还当了一回“千里送京娘”的“赵匡胤”,陪着丁玲和孩子由上海坐船到汉口,再从汉口经洞庭湖到常德,为的是把孩子送回丁玲的娘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