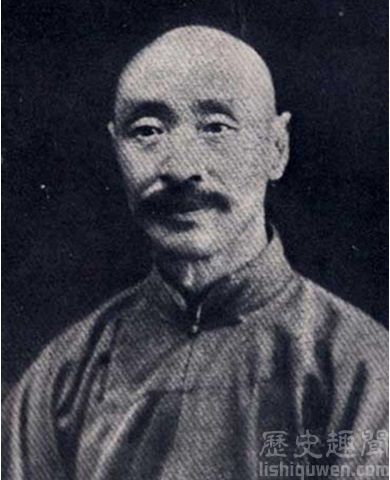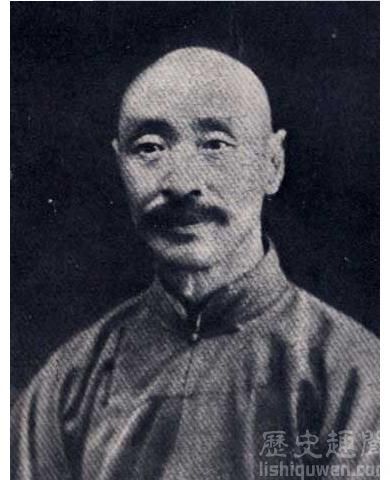郝景芳教科书 郝景芳:我不代表中国科幻 我一直是科幻圈的边缘人物
第一次见到郝景芳,是在一个和科幻写作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场合,一场关于不平等问题的公益讲座。"郝景芳"三个字后面岁跟随的身份是,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项目主任,与她一起被请来另一位嘉宾是个英国人,头衔是"英国乐施会高级政策顾问"。
那天郝景芳穿了一件淡雅的旗袍走上台,说话时有点害羞。她讲起自己正在构思的一本学术论著的提纲,书名叫《不平等的历史》,她想要在书中讨论不世界平等的现状、不平等的起源、不平等的解决方式,其中也提到了自己的小说,她说:"我写过一篇小说,叫《北京折叠》,讲的就是这几种不平等解决方式的其中一种。"
很难想到郝景芳口中的那本和"不平等"有关的小说,就在那天活动举行的不久前,被提名了雨果奖最佳短篇小说。但是那场讲座上,没有人谈论雨果奖,人们都在关注和贫困有关问题。
对郝景芳来说,好像完全不相同的各种领域可以毫无龃龉地融合在一起。比如她小学时读了《十万个为什么》,就立志要当一名科学家;到了初中,却又想当个作家,她总觉得,科学和写作两者可以兼顾。
这种融合一直持续到了大学,她考上了清华大学物理系,同时又对经济制度感兴趣,会去旁听经济学社会学的课,读相关教材和研究著作,她探究历史上的制度变迁、中西思潮比较、古今制度比较,思考乌托邦。而现在,她白天上班时进行宏观经济研究,给政府写经济政策建议报告,晚上回到家,陪女儿玩到睡下,然后早上4点起来写作。
理性和感性、工作和写作,在她生活中是互补的,似乎不需要转换。她说理性思维是由上到下从理论到细节的推导,感性思维是由下到上从体验到概念的抽象,科学能够让她把感性体验到的事情看得更清楚。对一个问题感兴趣,用一个统计公式可能只能表达一半,写一个故事也只能表达另一半,研究和写作结合起来,问题就能够更完整地表述。
但是当郝景芳总结自己的大学生活,写下的却是一篇《论一个清华学渣的自我修养》。清华牛人太多,这个从小就几乎没什么竞争对手的女孩考完试后就哭了,她找助教装可怜蹭分,助教给她一张同班同学的满分卷子,"那整张卷子那么干净整洁,写满了云淡风轻的潇洒";偶尔鼓起勇气找班里大牛问一道怎么都做不出的题,大牛对她说,这道题我觉得比较简单,就没做,你看看讲义吧。
那时,她产生了一种"觉得自己怎么努力都没有效果的感觉,而别人飘在天上的感觉"。
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她陷入自我怀疑的焦虑,"最开始起因是一些现实上的挫败感,觉得自己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是失去了自我评价的一些基本准则,去和其他人做比较,我没有办法有其他标准来自我确信",她从自己的大脑中寻找,"想找到一些什么是我自己可以依靠的东西,是我自己可以确信是自己的想法,没有,我自己可能空空如也,都是别人灌输给我的"。
越是想确认自己,就变得越加敏感,格外地关注外界对自己的评价,比如上周她跟某个人聊天说话有哪句话可能刺激到对方,她会反复地想;如果放在那段时间有记者采访,她恨不得把记者挨个采访一遍,问问记者是怎么看她的,如果记者眼里她不好,会很幻灭。
这些感受,她写进了刚刚出版的长篇小说《生于一九八四》中,那是一部现实主义的"自传体"小说,写的并不完全是自己的经历,但是一种内在精神历程的自传,里面的主人公因为找不到自我价值的定位,一度陷入抑郁。"我发现自己很大的问题,越是注意自己给别人留下的印象,越是被自己锁进一个壳子里,自己给自己造一个塑料壳子,在意别人对这个塑料壳子是怎么看的,好像有一点裂痕这个塑料壳子就要碎掉了,而里面是空空如也的。"
为了走出那段焦虑,她开始重新学习调整自己和外界的关系,她试图让自己忘掉外在的塑料壳子,去关注生活里自己真实的感受,体会自己真实的情绪,想自己的成长经历对自己的影响。"这些东西一旦触摸得越来越多,可以触摸到自己比较独特的生活体验的时候,这种焦虑会越来越淡。这样的时候世界就会扩张,从一个囚禁的状态到这个世界的每一件事、每一个人、所看到的每一样东西,都变得更加有意义。"
她也开始调整对自己的预期,她很诚实地说,之所以说自己是学渣,是因为自己心里除了爱因斯坦、波尔、海森堡、薛定谔这些大物理学家之外,其他人都是学渣,从前她的梦想就是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大学以后她承认,自己成为不了爱因斯坦,倒是对人文社科方面的兴趣越来越浓厚,慢慢发现在经济领域、社会领域也是是可以做很好的科学研究的,大四时她推了经济学直博,"把做物理学家的心愿转到了经济学方向上"。
毕业后她进入了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工作,不光做理论上的分析,还亲自实行慈善和教育项目,给贫困地区的儿童送营养餐,为留守儿童开办山村幼儿园,推进中学职业教育。现实的质感和理论的抽象高度,加上天体物理和量子力学的想象,融合成了她的作品独特的质感。
写作曾经是郝景芳处理焦虑的一种出口,"如果我不写作,我每天走在马路上会有很多想法,那些想法会侵扰到我",每天能写点什么她会不那么焦虑,只要坐下来开始写东西,就能够把自己的迷茫和困惑一点点梳理出来,除了小说以外,日记、笔记她有一大摞。但其实写作本身也没有带给她什么心理安慰,写作也让她迷茫,从2006年正式写作到现在写了十年,没太找到方向,也没什么成功经验,只是默默地在写。
她更喜欢纯文学的书,自己觉得很受打动的书往往是纯文学的,是写人与人之间的故事,写人自身的情感。也许是物理和宇宙的秘密总是让她脑中充满了奇奇怪怪的念头,脑中时常一个闪念就写下来,有人说有点像寓言,像小童话,她自己管她的小说叫做:"无类型小说",就像她在自己书的前言中这样写道:
"我经常感觉,用直接书写的方式并不容易真的反映现实,相反,用一个遥远的抽象世界作为映照,反而能将现实世界的某些特征照亮。……介于现实和虚拟之间的文学形式构筑起某种虚拟形式,以现实中不存在的因素讲述与现实息息相关的事。它真正关心的并不是虚拟世界,而是现实世界,以某种不同于现实的形式探索现实的某种可能。"
科幻给了她更多可能性,给了她一个超越现实的局限与单一,生活在形形色色世界里的机会。写假象的世界给了她更尽情的角色代入感,让她更安全地书写内心。她最近刚刚出版了三部作品,一本叫《流浪苍穹》,一本叫《孤独深处》,一本叫《去远方》。
"流浪"、"孤独"、"远方",这样的词语都有一些远离世界、远离此时的感觉,"这缘于我对科幻小说的感觉。科幻小说构想一个可能性的世界,人站在这个世界的边缘,最容易感觉到出世和异化。出离世界的感觉是最孤独的孤独"。
正因为无法定义,所以投稿屡屡受挫,她把小说投给主流文学杂志,编辑告诉她,杂志并不发表科幻作品,她投给科幻杂志,编辑又说过于文学化,不够科幻。包括翻译成英文的两篇小说,《看不见的星球》和《北京折叠》,都是《科幻世界》不要的稿子。
"《科幻世界》说过好几次,偶尔小清新一下就可以了,不要总这样写,总这样写是没有前途的",《科幻世界》大多数读者都喜欢很硬的宏大叙事的小说,故事性强,剧情激烈,"这个也是没办法的事,你的风格如果和他们喜欢的不一样的话,自己就会觉得很痛苦"。
《流浪苍穹》是郝景芳曾经出版的两部小说《流浪玛厄斯》和《回到卡戎》的合订本。《流浪苍穹》是小说原初的名字,那时出版社为了衡量市场的接受度,担心一个新人出书,这么长的小说一下定价四五十块钱会卖不出去,所以把小说拆成上下两册,上册很薄的一本只卖十几块钱。
如果上册销量超过5000本,就可以出下册。结果上册虽然销量平平,但出版社还是没有亏钱,隔了三年后还是出了下册。她当时很着急,"倒不是我想要卖多少书,而是担心一本书如果只出了一半,剩下一半就憋回去了,这样就永远没有一个完整的样子呈现出来。"
隔了六七年再次出版这部作品,"并非新瓶装旧酒以卖钱",她只是希望能还原这部作品最初的原貌。尽管现在看来那时的作品有很多不成熟之处,但她决定不去修改,"越是想呈现一部完美无缺的作品,越无法呈现,因为你在任何时刻都不知道未来的自己有哪些变化,因此永远无法让未来的自己满意。我决定不去修正过去的自己,就让它以那时那刻的面貌永远存在下去,带着所有不完美的地方存在,不做任何遮掩和修饰"。
这部小说依然用科幻的形式探讨她始终关心的制度问题。移民火星的人类爆发了反叛地球的独立战争,战争的结果使地球与火星形成了两个迥异且互不往来的世界。百年后,地球和火星开始了战后的交往,一群火星少年被送往地球,在那学习、长大。
当他们重返火星时,他们发现自己的命运被这两个相互猜忌的世界所裹挟席卷:一个世界规则严明,给予和所得都是义务,报酬由另一种方式呈现,资源高度共享;而另一个世界政府的作用和力量挤压到被忽略不记的程度,市场化进程已经推进到所有领域。
她用一群少年从一个星球到另一个星球感受到的变迁和茫然,表达她所感受到的她们这一代人经历的社会变迁的迷茫。《生于一九八四》讨论的是同一个问题,主人公和父亲两代人的寻找,个人的困惑、不适,其实都可以追溯到大的历史背景下社会制度的转变。
她用小说来呈现问题种种复杂的可能性,把它前后左右可能答案都不完美的情况摆出来。最后她发现可能没有一个完美的制度,问题的解决只能落在个体上,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解答。就像她研究经济、研究物理,最终研究的都是人,"我始终学某一两个学科而已,一个是说关于人类社会是如何,一个是说关于人类的精神意识是如何"。
如今她获得了很多认可和褒奖,刘慈欣曾经说她给常见的科幻题材洒上了一层很诗意的阳光,在国内的科幻创作中是不可替代的色彩,"感觉已经消失很久的金色夕阳从什么地方照回来了",越来越多的人认可了她作品的特点,可是她已经不再是那个为了获得外界认可陷入焦虑的小女生了。
她清楚《北京折叠》只是自己一部长篇小说的开头,尽管反映了自己的想法,但是还没有完成,她也知道自己写作的缺点还在,在主动地追求故事性和情节的曲折,让自己的写作更加多样化。
"评价一件事的时候,这件事情真的能改变我这个人吗?我出了这本书,今天的我和昨天的我就不一样了吗?或者说我得了这个奖,得奖前得奖后是两个人了吗?其实这个人本身是没有变化的,我的状态是长期连贯的。"她说。
很多人把她获得雨果奖提名看做是中国科幻兴起的又一标志,她一下子成了中国科幻文学的代表人物,可是她从来也不希望把自己归类。"我从来也不代表中国科幻。我从来是科幻圈的一个边缘人物,雨果奖提名之前,很多时候记者采访都想不起来我这个人,我到现在也不觉得自己能代表它,我就只是我自己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