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同祖夫人 陈新宇:人生何处不相逢——瞿同祖与何炳棣的命运对照
瞿同祖与何炳棣这两位近当代的杰出学人,不仅是燕京大学的校友,在西南联合大学、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加拿大的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等名校亦有相同的教研履历,通过梳理这一不为人所察觉的交集脉络,可折射出他们时代与学术、人生与人心问题。
引子
生命之树漫长却又短暂,茫茫人海之中,潮起潮落之际,有些人之间会宛若前赴后继扑上海岸的浪花,有瞬时交集,便又消逝于无痕。这种微妙的关联,或许是如小概率事件般无意之邂逅,但结合其时代背景与人生际遇,却又可以做出“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的历史解读。
有念于此,笔者不揣浅陋,试图以学术散文之笔法,挖掘法学圈外的两位广义的“法学家”——瞿同祖(1910-2008)和何炳棣(1917-2012)——梳理其生命中不为人所察觉的交集脉络,反思他们时代与学术、人生与人心问题。
说其是法律人,关于瞿同祖,法学圈的朋友自然不会陌生,先生虽是社会学出身,却以《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清代地方政府》等鸿著享誉于法学圈,其研究对汉语法学之典范意义,经诸多学者的用心推介,已成为学界常识,毋庸笔者赘语。
[1]关于何炳棣,其以人口史、社会阶层流动、土地数量、文化起源等研究闻名于世,定位无疑是历史学家。需要指出,香港中文大学曾授予其“名誉法学博士学位”,但笔者并非就此妄加附会,之所以称他为“法学家”,是因为其在求学过程中、尤其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期体现出来对法学知识的熟稔。
例如对边沁生平与理论的了解、对英国宪法及英法政治制度的掌握等等[2]。一个非常有意思、却容易被忽视的典故是,何炳棣对清代的“亩”并非耕地实际面积而是纳税单位的发现,正是受到英国法学家梅特兰(Maitland)之名著《末日审判簿及其前史》(Domesday Book and Beyond)的启发[3]——法学可以、也应该不“幼稚”嘛!
[4]
从普通史和专门史关系的角度讲,中国自近代以降,历史学受到现代学术分工的影响,呈现出“以收缩为扩充”[5]之趋势,即通过如法制史、文学史、哲学史等专门化的研究,从整体上推动历史学之深度广度。惟需要审慎的是,专业的划分仅仅是为了深入研究的需要,却不应以此为由而画地为牢、固步自封,所谓“法学的法律史”与“历史学的法律史”之分作为学科的事实存在即可,非要强加区别、优劣比较,则大可不必,因为王道乃是学者的素养与作品的质量,而非其身上所贴的专业标签。
从法学与历史学关系的角度讲,法律固然是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重要工具,但“知其然”之余,若要“知其所以然”,无疑需要到历史中去寻找答案,对于纠结古今中西问题的中国法学而言,历史不仅仅是一座博物馆,更是一座图书馆。[6]未来中国伟大的法学家,必然也是伟大的历史学家。
一、身世
瞿同祖出生于官宦世家,其祖父瞿鸿禨,是晚清政局中位极人臣的军机大臣,时有清流之誉,清季新政,正是他与权倾朝野的奕劻、袁世凯一掰手腕、一决高下,演出一段丁未政潮;其父瞿宣治是驻瑞士及荷兰的外交官。观其家世,用现在流行的话语来说,瞿同祖可谓典型的“官二代、官三代”。
管见以为,这种背景出身的人也可能是做学问的好苗子,君不见,大富大贵,可造就宠辱不惊的心态,高朋满座,利增加求学问道的机会,把握这种机缘,只能说命好人好,端的是可遇不可求。
君不见,祖父陈宝箴官拜湖南巡抚、父亲陈三立位列“维新四公子”的陈寅恪,亦是此中之例。平允而论,官宦世家,容易造就“我爸是某某”的衙内之徒,但若循循善诱,严加管束,也能培养品学兼优之人,可见此乃因人而异、因门风而异的事。
对于当代转型中国,如何消弭官、富阶层与普通人群的对立情绪,从培养学者这个角度讲,倒不无启发意义呢!优裕环境中,瞿同祖由其祖父开蒙《论语》,更有著名学者的叔父瞿宣颖指点汉赋,加上自身勤奋,奠定扎实国学基础,在中学毕业后,被保送入燕京大学攻读社会学。[7]
相对于瞿氏,何炳棣无如此显赫的家世,但也是比较殷实的金华旺族,父亲何寿权,旧式文人出身,科举废除后学习法政,曾担任过民国的检察官、法官,亦是一名儒医。[8]其父是老来得子,父子间的年龄差距有47岁之大,按何炳棣的说法,此造成其青少年时期心理和学业上长期的紧张和终身脾气急躁。
[9]笔者曾于2010年在清华聆听了何先生的讲座并有幸在丙所拜会过他,深感其霹雳血性,并不因年龄之故而有所减弱,甚至老而弥坚,在西方汉学界中,何氏亦以直言不讳、批评尖锐而有“大炮”之名。
父亲的影响是巨大的,怀才不遇的何父告之何炳棣,能够供得起其念好的国内教育,却无能力供他出洋留学,更坦言,“这种年头,如无法出洋留学,就一辈子受气。”因此,何炳棣从9岁起便以考取清华、进而留学作为两大志愿。[10]在1934年,他如愿以偿完成第一大志愿,考入了梦寐已久的清华大学,先读化学,后转为历史学并终生为业。
尽管有学人批评何炳棣的自传多谈留学、出国,未免过于功利,但若深入地看,便会发现其发愿实际上是时代的深刻缩影,和瞿同祖同庚、与之同样出自吴文藻门下的费孝通就道出大实话:
“30年代,我在大学里念书时,周围所接触的青年可以说都把留学作为最理想的出路。这种思想正反映了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青年们的苦闷。毕业就是失业的威胁越来越严重,单靠一张大学文凭,到社会上去,生活职业都没有保障。要向上爬到生活比较优裕和稳定的那个阶层里去,出了大学的门还得更上一层楼,那就是到外国去跑一趟。不管你在外国出过多少洋相,跑一趟回来,别人也就刮目相视,身价十倍了。”[11]
费孝通当年之所以从燕京转入清华,也是因为清华出国机会更多,这些聪颖的有志青年,怎敌他,形势比人强,不得不然也!那是时代冷酷却又真实的写照!
二、邂逅
1937年,日寇入侵,北平沦陷,已经在燕京完成研究生学业的瞿同祖于1938年南下重庆,同一年,清华毕业的何炳棣在上海考取了燕京大学历史系的研究生,返回北平就读,从而与瞿同祖有了校友之谊,何炳棣称瞿同祖为学长,即渊源于此。一年以后,瞿同祖到云南大学社会学系任教,兼任西南联合大学法商学院讲师,也是这一年,何炳棣来到西南联大担任历史系助教。
西南联合大学时期是两人生命的第一次交集。
在这里,瞿同祖默默地耕耘学术,他谈道:“在昆明时生活和工作条件艰苦,敌机不时来袭,在呈贡乡间住了一年,夜间以菜子油灯为照明工具,光线昏暗,不能写读,八时即就寝,于是就在床上反复思考写作中遇到的问题。有了腹稿,次晨便可奋笔疾书了。
”[12]正是在极端不便,甚至在缺乏如《宋刑统》这样重要图书资料的条件下,《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这部中国法律社会史的典范作品,直至今天仍然一版再版的不朽名著诞生了。笔者曾听到一个典故,数十年后,有学者访问瞿同祖时,略显突兀地问道:“抗战时期怎么能安心研究写作呢?”老先生轻声作答:“当时我也做不了其他事情”,真学人至纯至朴的本色,得见一斑!
君不见,与《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命运相似甚至更为坎坷的,还有同一时期金岳霖的名著《知识论》。[13]
国难时期,物质生活之贫乏与精神思想之丰富形成鲜明的对照,早在三校南迁至湖南组成长沙临时大学之时,冯友兰的如椽大笔便有传神记载:“我们在衡山……只有短短的几月,精神上却深受激励。其时,正处于我们历史上最大的民族灾难时期;其地,则是怀让磨砖作镜,朱熹会友论学之处。
我们正遭受着与晋人南渡、宋人南渡相似的命运。可是我们生活在一个神奇的环境:这么多的哲学家、著作家和学者都住在一栋楼里。遭逢事变,投止名山,荟萃斯文:如此天地人三合,使这一段生活格外地激动人心,令人神往。
”[14]或许,正是这种历史感通与文化自觉,乃维系中华民族多难兴邦、国祚不断之力量,也是瞿同祖们能安于困境、从容不迫甚至迸发出惊人能量的原因之一。
此时的何炳棣,仍处于打基础阶段,正默默地为其第二大志愿而努力,1940年第五届庚款留美考试失利、妹妹病逝、父亲去世,打击接踵而至,不得不返回沦陷区料理父亲遗产,接济家人。好在经历了“个人生命史上最不堪回首,最失败的篇章”[15]之后,命运终于否极泰来,1944年第六届庚款留美考试西洋史门一举中的,一偿平生夙愿,同榜生中,就有考取物理门,后来的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
留美庚款考试,每门只录取一人,各门总额全国不过十几、二十余人,可证其难度之高,历届考试中榜之人后来成为大家者,不知几何,可谓龙门之试也。
1945年,何炳棣来到了纽约,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巧的是,仍然是同一年,瞿同祖也来到了纽约,来到了哥大。他是受美国汉学家魏特夫之邀,担任该校的研究员。在哥大十年中,瞿同祖修订了《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并将其翻译成英文,后来出版的《汉代社会结构》,也应该是在此期间打下的基础。当然,此段时间工作的重心,更可能是配合魏特夫的研究。对此,何炳棣在回忆录中就不无深意地写道:
“(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的)书库及下一层较大的房间都被魏特夫(Karl A. Wittfogel)所主持的‘中国历史研究室’所占用……当时这研究室人才济济。冯家升燕京老学长因与魏合写的《中国社会史:辽代》业经出版,已经回到北京;瞿同祖和王毓铨两位杰出学长负责两汉;房兆楹、杜联喆夫妇在国会图书馆完成《清代名人传记》的编纂之后立即加入魏氏的研究室,负责清代。
所有搜译的各朝代资料原则上仅供魏氏一人之用,这是使我非常惊异不平的。”[16]
中国学人利用国外的优越条件,以客卿身份开展研究,写出一流作品,这种合作模式,当然值得肯定。只是其背后,也不免有淡淡的惆怅,学术固然是公器,但在“客随主便”之下,研究的独立自主性,不免要打折扣,正所谓“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一流的学人,不免且也无法避免某种“洋打工”的尴尬,这或许是大时代背景下海外中国学人命运之折射。
直至今天,海外中国研究不少高水准学术作品的背后,实际上有着无数优秀中国学者、学生所做的包括资料搜集、整理、翻译在内的基础性工作,外国学者通过这些冰人们的成果,兼以良好的学术传统与学术训练,写出好作品,自然水到渠成。心高气傲的何炳棣为何会“惊异不平”,应该是有感而发的。
据悉,此前在中国红得发紫的某美国汉学家,在阅读中文文献上不无困难,甚至需要借助翻译,我决非否定其“学术畅销书”有值得充分肯定、学习之处,当年林纾不谙外文,不也可以“翻译”出一流的文学作品吗?惟需要反省的是国人不应该妄自菲薄,设立双重标准来看待西方汉学与中国真正一流的学术著作(孙家红学兄一直强调此点)。
更应该深刻检讨的是,为何在当代中国,古文甚至近代的白话文会越来越变成一门“外语”,进而丧失对西方汉学著述优劣高下的基本判断力?可能是我孤陋寡闻,当年清华法学院的高材生、有“汉学警察”之称的杨联陞先生对西方汉学“把天际浮云误认为地平线上的丛树”[17]这种自信、中肯的批评,今天似乎难得一见了。
三、抉择
1948年,何炳棣在完成哥伦比亚大学西洋史的博士课程学习后,来到了另外一所哥大——加拿大的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BC)任教,并从1952年起进军其念兹在兹的中国史研究——“从此踏进国史研究辽阔无垠的原野”[18],在关于扬州盐商、人口史、土地问题等领域佳作迭出,进入了其学术的高产时期,一举奠定在西方汉学界的地位。
在1955-1962年期间,瞿同祖从哥伦比亚来到了哈佛东亚研究中心担任研究员,兼任讲师。在这里,他完成了另外一本重要的著作Local Government in China under the Ch’ing(《清代地方政府》)。
无独有偶,何炳棣也曾在1956-1957年期间在哈佛大学担任兼任研究员,在其1957年出版的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1368-1953(《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 1368-1953》)这本人口史名著的前言中,特别致谢瞿同祖“经常为我查考,有时甚至抄录不少这项研究所必不可少的资料”[19],恰是两人一段惺惺相惜、学术友谊佳话的注脚。
在这段时期,两个人的生活中都出现了一个相同的主题:回国。
何炳棣最初接受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一年聘书,原本计划在第二年接受美国经济史学会的资助,前往英国收集资料、访问名家以完成哥大博士论文的写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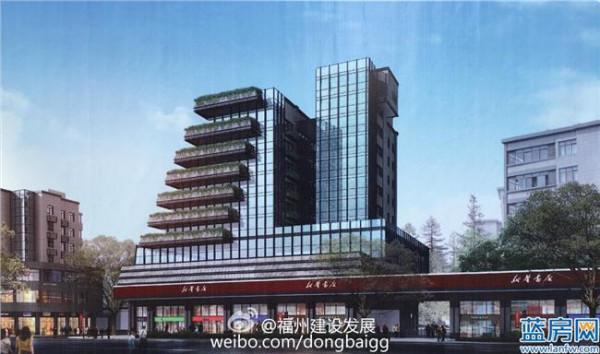
![>下塘镇陈新宇 下塘镇下塘路、振兴街污水管网及道路整治工程[正在公示]](https://pic.bilezu.com/upload/0/a8/0a8d6b60c24af8ab89cf957fd382587c_thumb.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