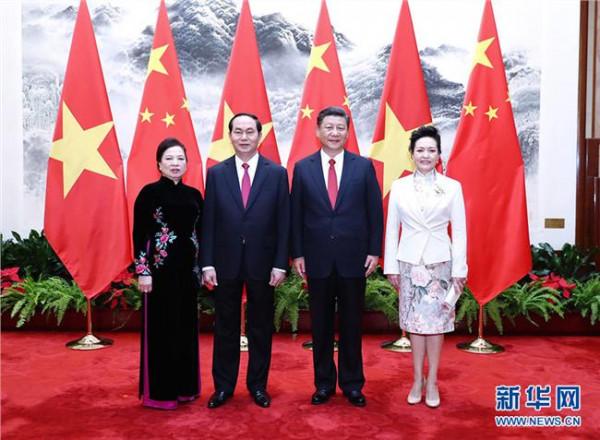陈公博夫人 "中共一大"历史细节:陈公博夫妇因情杀案未参会
毛泽东、何叔衡秘密前往上海。陈独秀为筹款而未与会。
毛泽东、何叔衡是秘密前往上海的,谢觉哉是何叔衡的同乡兼好友,也不知他去上海干什么。解放后,谢觉哉回忆说:“一个夜晚,乌云蔽日作欲雨状,忽闻毛泽东同志和何叔衡同志即要动身赴上海,我颇感他俩行动的‘突然’,他俩又拒绝我们送上轮船。
后来才知道,这就是他俩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大会。”(谢觉哉《第一次会见毛泽东同志》,《谢觉哉杂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4月版)7月4日,毛泽东和何叔衡抵达上海。
武汉小组的代表是董必武和陈潭秋,他们于7月15日左右动身,到上海时为20日左右。济南小组的代表为王尽美、邓恩铭。张国焘赴上海途中,曾在济南逗留了一天,在大明湖的游船上同王和邓谈了将召开一大的情况。在张国焘离开济南不久,他俩也乘车南下,于6月底到了上海。
陈独秀既是上海小组的发起人,也是广州小组的实际负责人,加上他在新文化运动的巨大影响,各地代表都希望他能出席党的成立大会。可是,在接到上海方面的来信时,正值他为兼任校长的预科大学争取到了一笔款子,一旦他离开广州,这笔款项就可能泡汤,便表示此时不便赴上海开会。
坦率地说,党刚刚创立的时候,陈独秀等人并未预想到,党的成立大会在中国历史上将产生划时代的巨大影响,也并未想到要以此来功彪史册。党的创始人基本上都是知识分子,开始时,他们均不是职业革命家,从事共产主义的宣传和组织活动,都是业余的,所以陈独秀等人并没特别注重这次大会。陈独秀乃提议,派陈公博作为广州小组的代表,又委派包惠僧代表自己前往上海出席一大。
包惠僧本是武汉小组的成员。1921年1月,他准备到苏联留学。从武汉到上海以后,就住在渔阳里六号《新青年》编辑部。后因海路中断,又无路费,苏联没有去成。五四运动中,包与陈独秀相识,后来又有书信来往,在上海滞留了几个月后,李汉俊因上海小组的经费没有着落,就让他去广州找陈独秀,要么请陈独秀回上海,要么把党的机构搬到广州,于是包就到了广州找陈独秀。
陈独秀以广州环境不好为由,不同意将党的机构搬来,并将包惠僧介绍到一家报馆做事,以解决生活来源。
对于包惠僧是否具有代表资格,历来有不同的说法。毛泽东、陈潭秋回忆包是会议代表。张国焘也在回忆中说包是代表,不过却说是代表武汉小组,这显然有误,因为上海通知各地小组派两名代表,武汉小组已派来了董必武和陈潭秋。董必武则在1971年回忆说,包惠僧是列席的,不是代表。李达在回忆录中也没有提到包惠僧是代表。
包惠僧自己回忆说:“有一天,陈独秀召集我们在谭植棠家里开会,说接到上海李汉俊的来信,信上说第三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派了两个代表到上海,要召开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会,要陈独秀回上海,请广州支部派两个人出席会议,还寄来了二百元路费。
陈独秀说第一他不能去,至少现在不能去,因为他兼大学预科校长,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第二可以派陈公博和包惠僧两个人去出席会议,陈公博是办报的,又是宣传员养成所的所长,知道的事情多,报纸编辑工作可由谭植棠代理。
包惠僧是湖北党组织的人,开完会后就可以回去(会前陈独秀和我谈过,还让我回湖北工作,大概他已经接到上海的信了)。其他几个人都很忙,离不开。陈独秀年长,我们又都是他的学生,大家就没有什么好讲的了。他说了以后,同意了他的意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86页)
不过,说包惠僧是一大代表也不算为过。一大召开的时候,并没有代表资格审查程序,会议也没有设立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谈不上合格不合格的问题。
包惠僧和陈公博于7月15日动身,乘海船于7月20日到了上海。陈公博还把新婚的妻子也带来了。
上海小组还向日本的留学生党员发了通知。当时,留日学生中只有在鹿儿岛的周佛海和东京的施存统是党员。施存统到日本的时间不长,功课又紧,便推周佛海作为代表。周佛海等课程结束放暑假后才动身,加之途中耗费了一些时日,到上海时已是7月下旬了。
上海小组的代表是李达和李汉俊。
上海小组是中国共产党的发动组,一大召开的地点又在上海,李达和李汉俊也就义不容辞地承担起了会议的筹备和会务工作。
各地的代表大多是教师或学生,收入有限,李达便由夫人王会悟出面,以接待北京大学师生暑假旅行团的名义,租了法租界的博文女子学校作为外地代表的住所,除了陈公博外,其余的外地代表都住在这里。陈公博是广东法政专门学校的教授、广东宣传员养成所的所长、《广东群报》总编辑,加之又是新婚燕尔,便下榻在大东旅社。
大会正式召开之前,各地代表曾在博文女校举行了一次简短的预备会议,相互交换意见,确定大会马上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