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思和北鸢 陈思和:《北鸢》是一部向《红楼梦》致敬的当代小说
葛亮的新作《北鸢》虽是一部以家族史为基础的长篇小说,但虚构意义仍然大于史实的钩沉。尤其让我感兴趣的是,这又是一部向《红楼梦》致敬的当代小说。小说名之“北鸢”,直接来自曹雪芹的《废艺斋集稿》中《男鹞北鸢考工志》篇,更深的一层意思作家已经在自序里说得明白:“这就是大时代,总有一方可容纳华美而落拓的碎裂。
”而《考工志》终以残卷而见天日,“管窥之下,是久藏的民间真精神。”暗示这部小说以虚构形式保存了某些家族的真实信息,所谓礼失求诸野。
而从一般的意思上来理解,这部小说正好与作者的前一部小说《朱雀》构成对照:“朱雀”的意象是南方,而“北鸢”则是北方,南北呼应;与《朱雀》描写的跨时代的金陵传奇相对照,《北鸢》是一部以家族日常生活细节钩沉为主要笔法的民国史。
这也是典型的《红楼梦》式的写法。真实的历史悼亡被隐去,满腔心事托付给一派假语村言。小说时间是从1926年写起,到1947年止,应该说是以半部民国史为背景。但民国的意象在小说里极为模糊。我之所以要这样来分析小说中的南京/民国意象,是有感于作者自序里的一句话:“这本小说关乎民国。
”这是一个含糊的说法,我们究竟是在哪一个层面上理解小说所“关乎”的民国?似乎可以断定,小说的故事时间虽然发生在1926年以后,但作者却无意表现国民党统治的“民国”。
小说里几乎没有提到国民政府的事情,甚至连南京被屠城都轻轻一笔带过,马上转入了山东临沂地区人民遭遇的惨案。在描写抗战岁月的篇幅里,作者林林总总地写到地方土匪活动,写到民间自卫武装,写到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游击,写到西方教会支持抗战的活动。
作者有意写了两个以自己家族前辈为原型的人物:一个是卢文笙的姨夫、直系军阀石玉璞,原型为直隶军务督办褚玉璞;一个是毛克俞的叔叔,原型为晚年困居江津小城的新文化运动领袖、第一代中国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这两个人物,一个是明写,一个是暗写。
褚玉璞为中心的故事里牵出了张宗昌、刘珍年(小说里为柳珍年)等一系列历史人物,还特意嵌入《秋海棠》里描写的民间野史,成为故事构成的一部分,这个人物在小说里对孟家、卢家都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尤其是通过昭德这一传奇形象间接地传递了这种影响。
陈独秀在小说里没有直接出场,只是通过吴思阅与毛克俞的对话,含含糊糊地暗示了他的存在。但陈独秀的存在仍然是小说里不可忽视的一个精神坐标,毛克俞他们反复说到他“一把硬骨头”,“硬了一辈子”的性格,然而毛克俞一生与政治绝缘,吴思阅最后不知所终,可能都与这位硬骨头“叔叔”的政治遭遇不无关系。
褚玉璞死于1929年,陈独秀死于1942年,他们对于中国政治的影响主要在1927年以前。但他们所代表的各不相同的民国政治,与国民党政府所代表的政治构成互相对立的力量,形成了多元而复杂的民国政治背景。
小说在这样一个民国的多元背景下,开始了北方城市几个大户人家的兴衰故事。褚玉璞与陈独秀本来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不可能发生人生轨迹的交集。偏有作者家族的奇特历史交集了两脉香火,使得风马牛不相及的民国人物,同时或现或隐地寄身于同一个故事里,象征了民国特有的文化现象:军阀势力延续了旧帝制代表的没落文化传统,又加入江湖草莽的生命力;新文化运动掀起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力量则不断以西学为武器,冲击旧传统和旧文化;这样两股力量的交集和冲撞,促使中国的文化轨道向着现代社会转型。
小说的笔墨重点落在卢氏、孟氏和冯氏家族的纠结和兴衰,通过大家族中两代人生活方式的变迁,敏感地展示了新旧文化冲突对于普通家庭的深刻影响。在某些展示旧文化的场景中,作者以平常的心态写出旧式家庭里老一代人的腐朽生活,在这里,纳妾、缠足、养戏子、勾心斗角等文化陋习,都是以常态的形式制约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但在另一些场景里,我们看到新文化的因子已在不知不觉中渗透到旧家庭,开始影响下一代的年轻人。
仁珏秘密参与抗日活动终于牺牲、文笙偷偷走出家庭奔赴战场、仁桢从不自觉地参与抗日活动,到亲身投入进步学生运动等等,这是民国历史的基本走向,也是民国时代新旧文化交替和过渡的基本特征。
然而,如果《北鸢》仅仅是这样来刻画民国时代的特征,那就过于简单了,上世纪30年代巴金的小说里就表现过类似主题。而作者在把握这样一些基本时代走向与特征的前提下,却着重刻画了在新旧交替变化的大时代里,某种具有恒久不变价值的文化因素。这是这部小说最大的看点:它展示了现时代人们对“民国”的一种文化想象。
作者没有把传统文化价值观仅仅落实在亚圣后裔身上,成为一种广陵散绝唱,而是把这种文化精神弥散在整部小说的书写空间。传统文化的因子在北中国的普通人家庭(即普通民间世界),无论贫富贵贱,均有丰富的蕴藏。中国传统做人的道德底线,说起来也是惊天地泣鬼神,在旧传统向新时代过渡期间维系着文化的传承。
如果要说真有所谓民国的时代特征,那么,在阶级斗争的学说与实践把传统文化血脉荡涤殆尽之后的今天,人们所怀念的,大约也就是这样一脉文化性格了。
这也是20世纪历尽创伤的中国要中兴复元的“一线生机”。小说取“鸢”为书名,自然是别有寄托。第五章第三节,写毛克俞教学生绘画,卢文笙画了一个大风筝,取名为“命悬一线”,毛克俞说,“放风筝与‘牵一发而动全身’同理,全赖这画中看不见的一条线,才有后来的精彩处。
不如就叫‘一线生机’罢。”其实这两个成语意思仿佛,不过是从不同的立场来理解,死与生都维系在这一条看不见的线上。小说里多次写到风筝在抗战中为扶危解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难免是传奇故事,真正的意义还是当下社会的需要,普通人的道德底线维系国家命运民族盛衰,道德底线崩溃,那就是顾炎武忧虑的仁义充塞,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了。
其实匹夫之责,不在危亡之际表现出奋不顾身的自愿送命,而在乎太平岁月里民间世界有所坚持,有所不为,平常时期的君子之道才是真正人心所系的“一线”。回想民国初期,西学东渐,传统文化在扬弃中有所保留,新文化在建设中万象更新;袁世凯恢复独裁,张勋起兵添乱,为何都陷于失败?这就是民心所向的力量所在。民国这个大风筝之命,全掌握在看不见的“民心”的一线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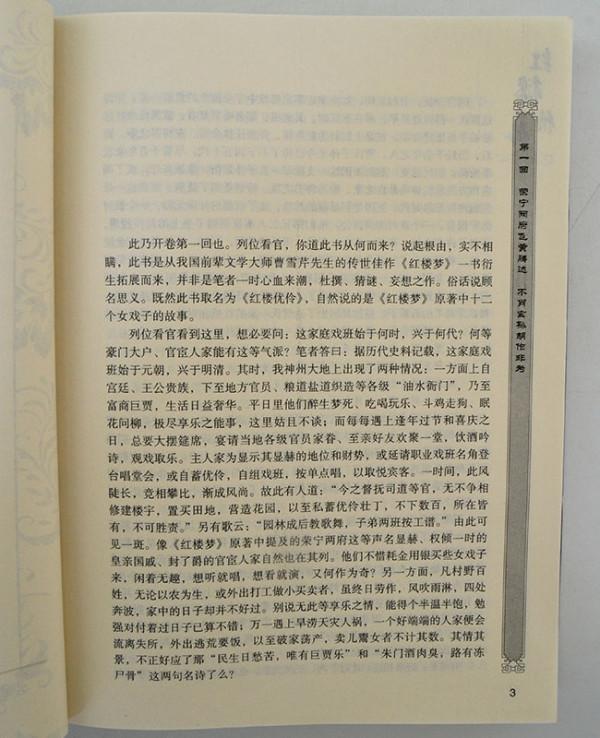


















![>陈思琪个人资料:陈思琪art微拍私房照片曝光[图]](https://pic.bilezu.com/upload/7/d0/7d0abf1d9a663d698f43b8a83c6a4956_thumb.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