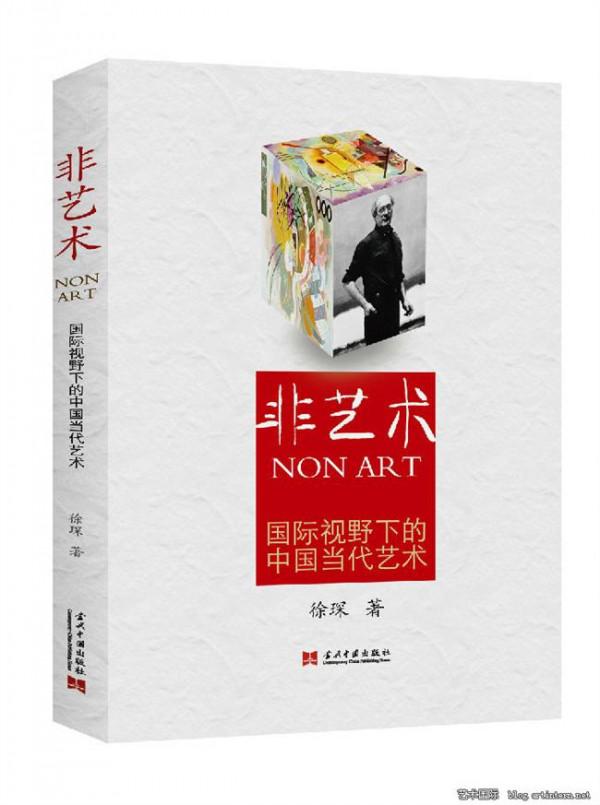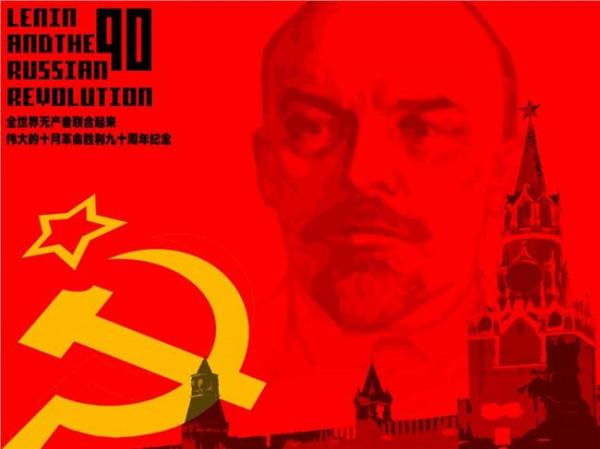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收入分配的福利化特点探析
摘 要: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在剩余价值规律依然占统治地位的同时,出现了收入分配福利化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通过税收调节贫富差距,实现“双盈”目标;全面推行社会福利制度,实施全民公共教育;兼顾劳动者工资收入增长,推出反贫困计划。但是“福利国家”的社会福利是工人劳动力再生产价值的扭曲表现,资本主义社会福利没有也不可能超出资产阶级的社会属性。
关键词: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福利制度;收入分配;福利化
战后几十年来,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在分配关系方面出现了一系列早期资本主义未曾有过的新变化。这主要表现在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体系来调节分配关系。这种变化的基本趋势是:在剩余价值规律依然占统治地位的同时,出现了收入分配福利化的特点,并且各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福利发展快,涉及面广,社会福利已从单纯的“济贫”变成了具有社会规模的公民应享受的权利。
一、通过税收调节贫富差距,实现“双盈”目标
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论是北欧还是北美,甚至一些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十分重视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多数资本主义国家都实行以个人所得税为主的直接税制度,以较高的累进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同时开征遗产税、赠予税、财产税等税种,这一方面为社会保障支出筹集资金,另一方面也适度缩小贫富之间的过大差距,削弱代际之间的不公平。
税收是当代资本主义各国对经济生活施加调节的基本手段,也是各国政府防止贫富差距过于悬殊的经济杠杆。
为了限制贫富差距过大,力求在经济利益分配方面达到尽量的公平,西方各国普遍推行了收入两次分配的政策。一次分配坚持效率原则,满足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攫取。二次分配则运用税收杠杆和福利补贴形式来兼顾劳动者和低收入者的利益。
在收入再分配的过程中,税收是调节贫富差距,实现“双盈”目标的主要工具。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税收增长非常快,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资料,1955年~1982年税收总额,美国从910亿美元上升到9232亿美元(增长9.
1倍),英国从57亿英镑上升约为1081亿英镑(增长18倍),联邦德国从561亿马克上升为5961亿马克(增长9.6倍),日本从15110亿日元增加为727160亿日元(增长47.1倍),意大利从34700亿里拉上升为187万4300亿里拉(增长53倍),法国从1965年的1691亿法郎上升为15603亿法朗(增长8.
2倍)。[1]税收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在同一期间税收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美国从23.
6%上升为30.5%,英国从29.8%上升为39.6%,西德从30.8%上升为37.3%,日本从17.1%上升为27.2%,意大利从27.1%上升为34.9%,法国从35%上升为43.7%。[2]税收比重的提高,是战后国家加强国民收入再分配调节的重要表现。
在西方一些国家的财政收入中,个人所得税收入占有最突出的地位。一方面,它是政府增加财政收入的重要途径,如1985~1986年财政年度的预算指标,英国的个人所得税为352亿英镑,占政府税收和其它收入总额的33.
1%。1985年,美国的个人所得税占联邦政府税收的45%。另一方面,它还是政府反危机的重要手段,即通过增税抑制经济“过热”,通过减税刺激经济复苏。个人所得税也是调节富人与穷人收入差距的主要税种。在西方各国,个人所得税是按照累进税率征收的。
德国是力求实现收入“均等化”的典型国家。德国的《基本法》明确规定:凡有一定收入水平的每个居民都必须缴纳个人所得税。按1988年的规定,德国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为个人年收入4500马克,最低税率为22%,最高税率为56%。
也就是说,大资本家个人收入的56%须缴纳给国家,用来进行二次分配。瑞典的个人所得税也采用了累进税制。收入越多者,上交个人所得税的比率越高;收入低者,纳税比率也低,甚至免税。
瑞典有关法律规定:月收入在1万克朗以下者不交税;月收入在1万至2万克朗者按30%的税率交税;月收入在2万克朗以上者按50%税率交税。美国在税收调节方面也推出了一系列举措。同其他西方国家一样,个人所得税是美国对社会生活进行调节的主要手段。它们的个人所得税也实行超额累进税率。
二、全面推行社会福利制度,实施全民公共教育
目前,西方国家每年通过税收能够集中起来的国民收入一般都在1/3以上,其中欧盟国家已接近50%。在以国家财政形式集中起来的这一部分国民财富中,大约有60%要用于贫困救济、免费医疗、失业补贴、养老金发放、教育等社会福利开支。
这样,在发达国家的工人和贫困人口的生活费用中,来自财政收入再分配的比重越来越大了。如瑞典工人收入就有1/3来自社会福利。社会福利制度的全面推行,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特点。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纷纷确立社会福利制度,社会福利不断增长。
到20世纪70—80年代,社会福利已从过去的单纯救济发展成了公民的一种社会权利。在德国、瑞典等西欧、北欧国家中,甚至形成了“从摇篮到坟墓”的一整套“福利国家”政策,有人称其为“生产中的资本主义,分配中的社会主义”[3]模式。
福利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增长也较快。1970年英国、丹麦、比利时、法国、爱尔兰、联邦德国、意大利、卢森堡、荷兰9国平均社会福利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8.1%,到1981年已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27%。
据世界银行1992年的数据,瑞典社会福利开支占政府总开支的50%以上,其税收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60%之多。美国不像西欧、北欧国家那样,重视社会公平和缩小贫富差距。但美国的社会福利制度也是很完善的。据《美国政府津贴百科全书》介绍,美国公民从生到死可以享受2000多种政府福利。
在婴幼儿时期,早产婴儿可享受医院免费护理;在青少年时期,中小学生每天可享受一餐免费热午餐,上学可享受种种奖学金及赠款;失业者有职业介绍服务和失业救济金;成年时期有住房、失业、残废补贴和津贴,还有医疗保险;老年时期,政府提供养老金、社会保险、医疗保险等福利服务。
由于社会福利制度的推行,明显提高了国民的收入尤其是中下层居民的收入。收入分配领域中“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制度,对于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改善,保障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缩小贫富差距具有明显作用,体现了收入分配福利化方面的社会主义因素。
为了提高国民的生活质量,减少生活费用的支出,当代资本主义各国还普遍推行了覆盖全民的公共教育。在人均收入较高的国家,用于社会福利开支的比重一般较大,特别是用于公共教育支出的比重较大,公共教育支出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美国1978年为7.
1%;日本1973年为4.3%;联邦德国为4.1%;意大利为5.4%;瑞典70年代以来已超过9%。[4]在德国,教育是作为一种福利向民众提供的。德国的《基本法》规定,国家要对6岁至15岁的青少年实施义务教育,联邦各州对教育事业承担主要责任。
因此,全部教育经费均由政府投入。对全民进行良好的公共教育是瑞典推行“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主义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该国推动收入均等化的重要举措之一。
瑞典的教学大纲规定:瑞典教育的总目标是使每个人不论其社会、经济、种族和所处地的不同,均可享有公平而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中、小学教育全部免费。法国的全民教育坚持“无歧视原则”,不论其血统、种族和宗教的不同,国民都平等地享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的初等教育也都坚持了完全免费制和“无歧视原则”。西方各发达国家推行9年义务教育并对所有学生完全免费,完全免费的初等教育事实上提高了低收入阶层的生活质量,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贫富差距。
三、兼顾劳动者工资收入增长,推出“反贫困计划”
当代资本主义在收入分配方面福利化的特点,在劳动者工资收入增长及各国政府的“反贫困计划”方面得到了印证。
在早期资本主义阶段,工人的工资收入很低,而且没有保障,资本家攫取剩余价值的比率很高。19世纪下半叶,美国的年剩余价值率平均在100%左右,日本在20世纪30—40年代的年剩余价值率平均在230%。二战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
目前,当代资本主义各国的年剩余价值率平均在40%左右。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各国的国民收入中,剩余价值所占的比重在下降,劳动者工资收入的比重在上升。这说明,在剩余价值规律依然占统治地位的同时,当代资本主义各国也开始兼顾劳动者工资收入的增长,并注意保护劳动者的利益。
要想解决收入不公平问题,首先要解决的是贫困问题。为了保证低收入阶层的基本生活需求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战后西方各国纷纷推出了“反贫困计划”,它包括培训计划、社会服务计划、卫生服务计划、住房补助计划、“食品券计划”、公共救济计划等等。
这样能使贫困者生活在某一最低生活水平线上,并能使他们获得改善现状的条件。近些年来,欧共体先后通过并实施了1975—1980年、1985—1989年、1989—1994年的三个反贫困斗争纲领。
最近又提出并启动了第四个反贫困斗争纲领——“前进”纲领。根据欧共体反贫困斗争纲领的精神,西欧、北欧各国都推出了得力措施,对贫困人口实施救济。如通过确定最低工资限额,实行低收入补贴,失业与残障者保险等,以保证贫困者生活水平的最低限度,安慰弱势群体,缓和资本和劳动的对立。
同时各国也纷纷立法,明确规定本国居民有获得一种“有保障的最低收入”的权利。当代资本主义在解决贫困人口问题上是有作为的。
近年来,社会福利的增长已经发展到使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难以承受的地步。但是,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取消社会福利,只是在调整“福利国家”的政策,实行社会福利私营,从单一的福利国家走向由国家、私人机构、社会机构相结合的多元化的社会福利制度,并把福利计划转为就业计划。
这或许是一种更为积极的办法,它使社会福利在制度化方面并没有退步。社会福利制度化的实施,对社会分配不公具有较强的抑制功能,使得各阶级和各阶层之间的冲突与矛盾有所缓和。
时至今日,当代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无产阶级的生活状况、劳动条件,虽然有明显的改善和提高,但是“吃穿好一些,待遇高一些,持有财产多一些,但不会消除奴隶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同样,也不会消除雇佣工人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5]。
因为工人阶级仍然不占有生产资料,仍然要靠出卖劳动力为生。在资本主义社会,财富是世代继承的,财还可以生财,而财富创造财富是产生社会上一切差别的根源。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说,他们是同资本无缘的,即使在当代资本主义亦是如此,因此注定不会发财,只能存在贫困趋势。所以,富裕中的贫困是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无法解决的难题。
四、“福利国家”的社会福利是工人劳动力再生产价值的扭曲表现
尽管资产阶级把资本主义福利说得尽善尽美,但它毕竟是资产阶级在有限范围内对生产关系所作的一种改良和调整。其目的完全在于暂时缓和日益加剧的阶级冲突和难以驾驭的社会问题。资本主义社会福利没有也不可能超出资产阶级的社会属性。
“福利国家”的社会福利没有超出劳动力再生产价值的范畴。“福利国家”的社会福利来源于三个方面:(1)国民收入再分配。由政府拨款,它占社会福利开支的20%~40%不等。(2)资本家交纳的捐款和税收。(3)工人交纳的捐款和所得税。
[6]很明显,第三项是工人工资的直接扣除。有些学者总把前两项说成是资产阶级及其政府的“慈善”,其实不然。资本家上交的部分,通常由资本家计入商品成本,通过出售商品,转嫁到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身上。
政府负担的那部分,来自财政收入,而财政收入来自税收,税收则主要来自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这样就使名义上由资本家和资产阶级负担的主要部分,重新转嫁到工人和劳动人民身上。资本主义国家提高工资和社会福利并不是出自对工人的关心,而是当代资本主义劳动价值内涵有了新的变化。
现代科技的发展和运用,使工人受教育、培训的费用大量增加。特别是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给资本主义国家提出了保证劳动力生存、储备和再生产的要求。这部分费用本来就属于劳动力再生产价值的一部分,然而却以社会福利的形式扭曲地表现出来。
“福利国家”的“高福利”总是伴随着高税收。高税收吞噬了工人相当一部分工资。在资本主义国家,尽管工人与资本家地位截然不同,但他们都把工资和社会福利看成同一种东西。工人把社会福利看成生存繁衍的必要条件,资本家则看成劳动成本的一部分。
总之,资产阶级社会福利制度,只不过暂时满足一部分工人群众最低限度的经济要求,并没有改变工人阶级的经济、政治地位,因而,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越来越趋向频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