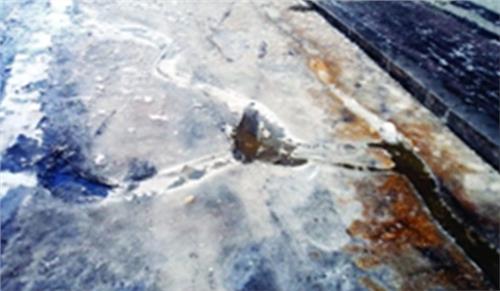梁启超与张君劢 梁启超与他的“研究系”
研究《晨报副刊》,决不能回避它依附的母体——《晨报》,而众所周知,《晨报》是研究系的机关报。研究系是从民国初年的进步党脱胎的一个政治派系,得名于1916年在北京成立的“宪法研究会”,其领袖人物是梁启超、汤化龙,其骨干分子是在1906年的君主立宪运动中曾经跟梁启超合作过的一批官僚士绅。
由于研究系始终想凭借一种固有的旧势力来改良中国,所以曾经在政治上先后依附袁世凯、段祺瑞军阀势力而与国民党相对立,作为研究系言论机构的《晨报》名声不能不因之受损。
不仅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厌恶研究系,而且国民党也将研究系视为“世仇”:1917年9月1日,国民党雇佣刺客在海外枪杀了研究系首脑人物之一的汤化龙;1925年11月,国民党骨干人物朱家骅又带领激进的青年学生愤怒烧毁了位于宣武门外丞相胡同内的《晨报》馆。
但是,历史的本来面貌是非常复杂的。研究系不但缺乏团体的一致行动,而且政治上也反复无常。1927年,梁启超对他的女儿解释说:“我们没有团体的严整组织,朋友们总是自由活动,各行其是,亦没有法子去部勒他们(也从未作此想法)。
别人看见我们的朋友关系,便认为党派关系,把个人行动认为党派行动,既无从辩白,抑亦不欲辩白。”(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篇》,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111页)就政治态度而言,后来组成研究系的那批人物在民初国会中是拥载袁世凯的,因此袁世凯才于1913年推动共和、统一、民主三党合并而为进步党,并为其划拨了经费。
进步党瘫痪后,这笔钱为研究系接受,成为了他们办报(包括《晨报》)的经费来源。
但袁世凯暴露出复辟称帝的狼子野心之后,梁启超又抵制了二十万元的巨额贿赂,坚持发表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跟他的弟子蔡锷鲜明地举起了反袁的大旗。曾支持以段祺瑞为代表的安福系是研究系的一大历史污点,但1918年9月《晨钟报》和《国民公报》这两家研究系报纸跟其它六家报纸一起被查封,却正是因为它们披露了段祺瑞向日本大借款的内幕。
在思想学术方面,《晨报》及其副刊曾大量载文宣扬实用主义、改良主义,极力介绍杜威、罗素的讲演和著作,但也正是在这家报纸上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多次介绍了马克思、列宁等无产阶级领袖的传记,介绍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经济学说,首次纪念了五一国际劳动节,首次全面报道了十月革命后的苏俄。
在五四爱国运动的全过程中,《晨报》一直站在爱国学生的一边而对政府持批评态度。过去论者习惯于将《晨报》曾经产生的积极社会效果归功于李大钊担任过《晨报》的编辑,瞿秋白担任过《晨报》的驻俄记者……这种分析当然有正确有一面,但也有些表现化和简单化。
其实,在五四时期,不仅同一派系的成员之间存在着相对独立性,而且副刊跟报纸之间、报纸跟所属党派之间也有着相对独立性。
梁启超在谈到他对于中国文化运动的向来主张时,强调的是“绝对的无限制尽量输入”。《晨报》对各种新思潮兼容并包地进行介绍,比如陈独秀提倡的“俄国式革命”,周作人向往的“新村主义”,胡适鼓吹的“实验主义”与“好人政府”,蔡元培主张的“美育代宗教”……跟梁启超的上述主张显然是密切相关的。
《晨报》主编陈博生也公开宣称:“我们《晨报》在法律无光、是非不明的社会之中,维持不偏不党底态度……我们决不肯替一党一派说法,也不肯替一国家一阶级帮忙。
”(引自渊泉:《本报四周纪念日》,载1922年12月1日《晨报》)。标榜“不党主义”,这正是研究系及其媒体的一种特色。
1923年,发生了中国近代史的一场大论争——科学与玄学之争。论争双方的主将丁文江与张君劢不仅同属研究系,而且还是两位耳鬓厮磨的最要好的朋友。笔者举出这个例子,并非否认研究系的基本倾向和整体性立场,而只是指出研究系成员有价值判断的一致,也有观点的歧异,只是强调对于色彩纷呈历史原生态不能作单线条或单色调的简单勾勒。
学术界以往对研究系研究的不足,除开表现为对研究系的复杂性缺少具体分析之外,还表现在忽视了它与新文化运动斩不断的关系。众所周知,《晨报副刊》跟《时事新报•学灯》《民国日报•觉悟》《京报副刊》合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四大副刊,而这四大副刊中前两种都有着明显的研究系背景。
除此之外,1919年被安福系军阀查封的《国民公报》也是研究系的言论机关,这也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阵地。
1919年3月1日,《新潮》杂志1卷3号介绍了三种定期刊物,即《新青年》月刊、《每周评论》周刊和《国民公报》月刊,指出三者“虽然主张不尽一致,精神上却有相通的素质;对于中国未来之革新事业,挟一样的希望。
”1919年9月,研究系还创办了一种杂志,叫《解放与改造》,第二年9月改组为《改造》杂志。这份刊物虽然对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有诸多曲解,但也以近十分之一的篇幅刊登了胡适、沈雁冰、耿济之等人的评论和创作。可见以研究系为背景的报刊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有其无法抹杀的历史贡献。
在以往的有关文章和论著中,还习惯于把《晨报副刊》的进步作用划定在孙伏园值编期间。比如文化大革命前出版的《五四时期期刊介绍》就是这样表述的:“《晨报》正张从1923年就已失去其进步作用,但它的副刊到1925年完全被新月派篡夺为止,却一直是当时思想界和文艺界中有广泛影响的刊物。”这也就是说,新月派在1925年10月掌权之后,《晨报副刊》的影响和进步作用也就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