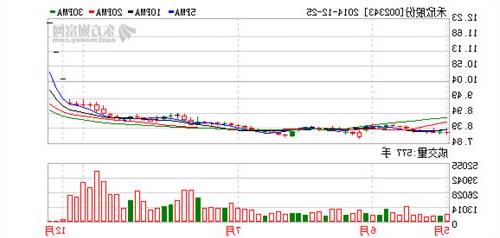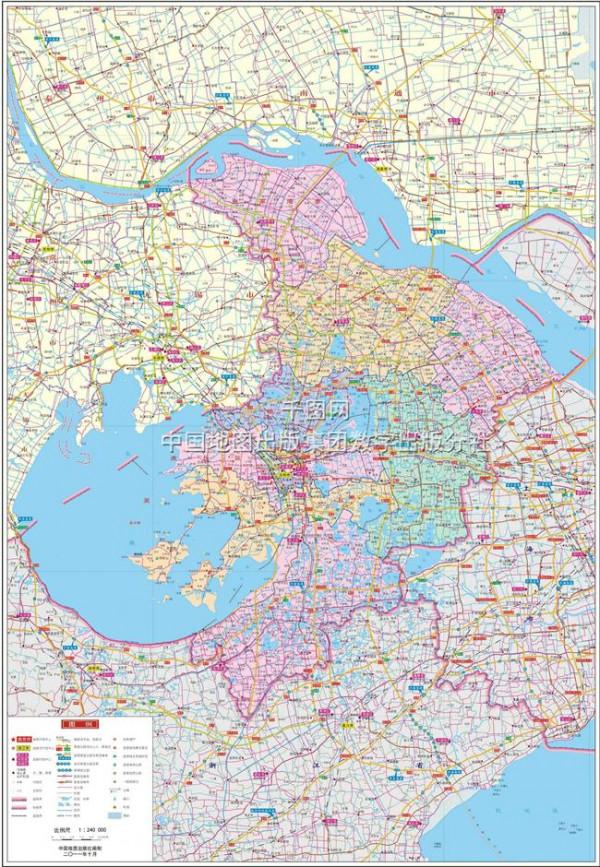姚文元评海瑞罢官 一个普通中学生反对姚文元《评海瑞罢官》后的遭遇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文革”持续十年,给国家的政治经济乃至个人的命运带来巨大影响。马以鑫、姚全兴和林炳义——他们一个中学生、一个大学生、一个中学教师,对姚文元该作提出反驳意见,并“自投罗网”地给《文汇报》、《光明日报》寄稿,此后遭遇接二连三的迫害和打击。在各种版本的“文革”史叙述中,这三个“小人物”的故事属于“外编”。
时隔半世纪后,复旦大学口述研究中心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口述史中心采访了三位当事人。本文为马以鑫口述。他现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口述:马以鑫
采访:金大陆、冯筱才、金光耀
我1948年出生,“文革”发动时在上海敬业中学读高中,平时除了读小说,还喜欢文艺评论,关注报刊动态。关于姚文元这个人,也比较关注。
1965年11月10日,我当天在学校的读报栏看到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读的时候就有两个疑问,第一,海瑞到底是好人坏人?我印象中海瑞名气很大,是个很有影响的清官,老百姓(603883,股吧)一直很爱戴;第二,我们今天看海瑞的戏到底学什么?
记得这天是礼拜三,到了礼拜天,我就到上海图书馆,找了有关的历史剧、吴晗的文章、剧本,从中午到晚上,看了以后觉得姚文元的文章和实际距离太大。两天以后的一个晚上,我用五张活页纸,绿线条的,正反面都写了,一气呵成,写成《也谈〈海瑞罢官〉》。写完以后,因为寄到报社,我猜测不能用真名,担心自己观点错,因为姚文元名气太大了,就用了“马捷”这个名字。拖了几天以后,文章寄给《文汇报》,同时还附了一封信:
编辑同志,我是一名中学生,喜欢文学,爱读你们的报纸,姚文元的文章看了以后有点想法,现在写成一篇文章,也许是不对的,但这是我的想法。
大约就过了四五天,那天中午休息的时候班主任来找我,说你下课以后到《文汇报》去,他们来了电话。她问,你写了什么文章?我说反驳姚文元观点的。她很惊讶,旁边同学越聚越多,一下子班上同学都知道了。
我也不知道《文汇报》为什么找我谈,谈什么情况。我是坐电车去圆明园路《文汇报》社的。
到了总编辑室,进去以后有个头发花白的老人,他和我握手,说姓陈。他先问我怎么会写这个文章,我就把观点怎么形成告诉他,我注意到他手里拿了我的文章,上面划有许多红铅笔的横线。他结束的时候他说“你这篇文章还没有击中要害,观点比较散”。这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下面一句很关键,他说,“文章准备用,你回去改一改,马上给我。”
我有些喜出望外,马上接了一句,“你手上这篇稿子给我。”他说可以啊,就给了我。我路上想了想,这篇文章太尖锐了,锋芒太露。晚上我用不到两个小时,将文章改成一封温和的“读者来信”,而且言明我是中学生,要好好学习,一副谦恭的学生模样。字数也少了一半多。
其实在路上我就有些后悔了。当时第一感觉大概是做了一件傻事,姚文元怎么可能有错?第二从班上的反应、老师的神态上发现不太妙,有点异样。他们好像都有些不屑。
第二天早上8点我再到报社,昨天先接待我的人出来了,他叫闵世英,是陈总编辑的秘书,我把稿子给他了。30日上午第二节课后,别的班有人问我:“马捷”是你吗?你的文章登出来啦!
我奔到三楼阅报栏,《文汇报》通栏大标题:《关于〈海瑞罢官〉问题讨论(1)》。底下,就是我的《也谈〈海瑞罢官〉》,署名“马捷”。我特别奇怪,怎么用了我原来的稿子呢?我更奇怪的是,稿子已经给了我,怎么还能登出来?我马上给报社打电话,找闵世英。
我问:“闵老师,怎么你们用了我原来的文章?”他就说了四个字:“我们需要。”我也没话可说了,愣了愣,然后说“麻烦闵老师寄几份报纸给我”,他说好的。我先到邮局,因为这毕竟是我人生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文章上了报纸。
随着《文汇报》关于《海瑞罢官》问题的讨论一期期地进行,先是翁曙冠校长找我谈话,报纸讨论也越来越倾向于姚文元了。尤其《》的“编者按”旗帜鲜明,明确讲《海瑞罢官》是大毒草,姚文元写的是革命文章。
我周围的环境开始变了,低年级的同学开始当面嘲笑我、奚落我。一天晚上,从来没有接触过的副校长、党支部副书记苏渔溪到我家里来了。他见了我,笑嘻嘻的,事先跟我父母已经谈过了。他说,“马以鑫啊,你要从这件事好好吸取教训,反正事情已经过去了,文章写也写了,自己不要有太大压力。”
后来很长时间里,他都竭力保护我。后来,我逐渐感到压力越来越大,就写了一封信给陈虞孙总编辑,表示我现在觉得很痛苦,很后悔。几天以后,陈虞孙亲笔给我回信,寄到学校的。这封信到现在我都印象很深,是毛笔蘸蓝黑墨水写的。信笺上面是红色的“文汇报社”四个大字,下面一条红线。当时这封信就被班主任拿走了,我到现在还记得,原文是这样的:
以鑫同志,你的来信收到,你现在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是,你属于认识问题。不过,从这件事你如能吸取教训,(下面有个成语我印象很深),改弦易辙,对你未必不是件好事。陈虞孙。
信笺底下有一句话很关键的话,小点的字:
可将此信交予你们校领导一阅。
我看了以后,正好班主任在边上,就交给了她。这封信从此就不见了。当然校长是拿到的,并且对我说“《文汇报》陈总编辑的一封信我们看到了”,但也没说要还给我。这封信极大地保护了我,压力有所减轻。
没想到,6月初“三夏”下乡劳动回到学校,大字报已经铺天盖地。我的有不少,集中的就是“反对姚文元”、“恶毒攻击姚文元”、“反姚急先锋”等。很多是批校领导对我包庇、纵容,也有说我已经出这种事怎么还安排我演群口快板的英雄人物,等等。
1968年夏天,突然有一股紧张气氛,其他班级开始揪反动学生。我非常害怕,去了圆明园路报社,一个群工组接待女同志出来,叫范嘉静,后来跟我关系一直不错。她比我大两岁,以后几乎无话不谈。当时她听了我的叙述和担心,没有说什么,只是要我过几天再去一次。
三天以后,我又去了,范嘉静告诉我:“你的事情我同头头汇报了,他们说,你的文章当时是报社需要,学校有什么问题让他们找报社。”我听了以后,觉得心里一块石头落下来。但是,没有几天,传出要抓我斗我,风声很紧。
我有点怕,就打电话找范嘉静,她不在,我就直接找《文汇报》负责人,电话竟然打通了。我说红卫兵要揪我,他问为了什么事?我说还是当年“海罢”文章的事。他马上说:“你告诉学校的红卫兵,如果他们还是为了《文汇报》这篇文章,让他们直接找我们《文汇报》。你如果遇到什么事情,也可以马上到我们报社来。”
我一听这样的话,当时就有晕眩的感觉,连忙又问尊姓大名。他轻轻说,邵传烈。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上海开作协大会,我才见到他。我怀着感激之情,称他为是我的恩人,表示了深深的感谢。后来想想,如果不是《文汇报》这样的态度,我真的不知道会遭受到什么样的罪!
到了1968年底开始毕业分配时,我知道不会有好果子吃。但我弟弟是67届初中,上海二留一政策,我跟弟弟讲他留在上海,班里去工矿的一半左右,我排不上,最高目标去崇明农场。没想到我弟弟是去了工矿,我连崇明都没轮到。一直拖到毛主席指示出来:“知识青年到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没几天学校开大会,突然宣布首批赴安徽插队落户名单,我赫然在列。我没报过名,一点不知情。过了两天学校逼着我去体检。我无可奈何,但没想到我一两岁时得过胸膜炎,左胸膜上面有个疤痕,体检给我写下:左胸膜病变。带队的学校头头有些不甘心,问医生这会影响插队落户吗?医生回答很干脆:当然不可以去!那个老师咬牙切齿地看着我,还问:“你怎么会得这种毛病?”
过了几天,工宣队和班主任到我家里宣布:“马以鑫,你属待分配,关系转到街道。”然而没有多久,好事坏事一起来,我母亲不知怎么当了街道革委会委员,正好是搞上山下乡工作,当然自己要带头,就劝我到黑龙江去。
当时有兵团和农场两种,我想我这种身份去兵团可能比较麻烦,就去了黑龙江嫩江农场。
我先是到基干民兵连,说起来都是出身好、表现好才能去的,去了没几天又叫我担任文书。再没多久,我是三分场“一打三反”核心组成员。我自己都惊呆了,怎么会“三级跳”?
到了那里没有几天,有个哈尔滨的知青告诉我,“马以鑫,你不得了,你反对过姚文元?”我想他怎么会知道呢?这个哈尔滨知青对我说:“你的档案里有一份检查。”
我在“一打三反”办公室上班,档案都在柜子里面,不上锁的。一天晚上我偷偷溜进去,像特务一样,我就找自己档案,打开一看,果然只有一份表,中间有我自己写的材料。我当时心惊胆战,真想把自己写的东西撕掉,那么,关于批姚的事情不就什么也没有了吗?但是,我终究不敢这么做!
1973年我调到场部宣传队不到一年,开始大学招生。当时读大学是个人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审核。那年还考试。当这些都做得差不多的时候,出了两件事情,一个是体检出我肺部有问题。一个要好的朋友,找卫生院把我的体检表重新做成正常。
但有一天,上海师大来招生的老师突然叫我晚上去他招待所的房间,我一听就觉得有恐怖的事情将会发生。果然,我刚坐下他就问:“听说你1965年写过反对姚文元的文章?”我一听就如同五雷轰顶,只好结结巴巴、原原本本把这件事说了一遍。这位招生老师叫罗宗德,听了我的叙述,他没说一句话。我都不知道怎么走出他的房间的。
没想到发通知那天我还是拿到了(通知书)。我和罗老师没有其他正面接触,却一辈子都在感激他。后来叶永烈的采访文章写了对罗宗德老师的询问,他只说了一句话,很简单:“不要因为17岁的一篇文章而影响他的一辈子。”采访文章出来以后,我去罗老师家里拜访他。他说,还有一句话没对叶永烈表露:“当时我们对张春桥、姚文元其实很看不惯,有人反对不是蛮好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