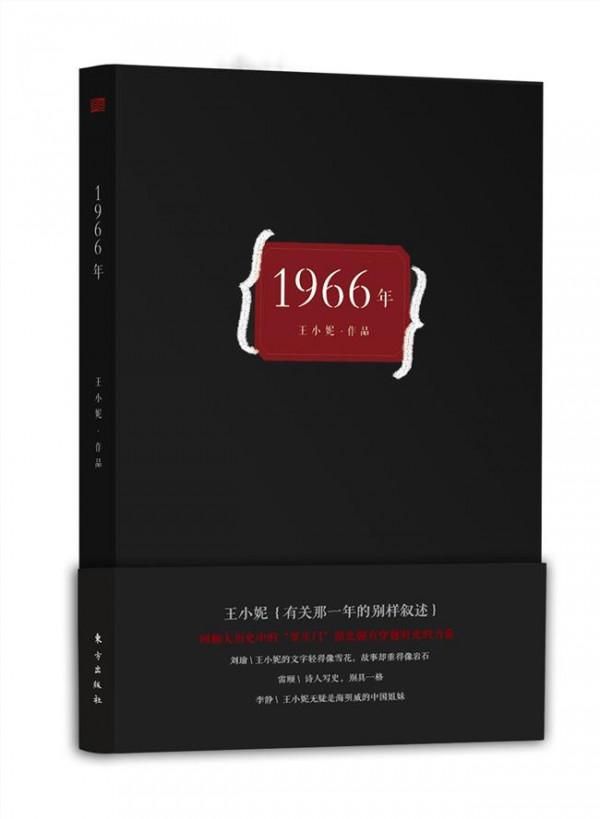野夫1980年代的爱情 为野夫《1980年代的爱情》撰写的序言
土家人野夫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文革”中当过少年樵夫,“文革”后,上过一所野鸡大学和一所名牌大学,当过公务员,当过光荣的人民警察。身为体制内前途一片光明的高级雷子,野夫却在六四时坚决站在民众一边,被捕入狱长达数年。
在狱中,他奇迹般地和某狱卒结为朋友,挖了专制体制的一个小墙角。出狱后,他为谋生而成为著名书商,兢兢业业战斗在出版发行的二渠道,成为“不”共和国或“没”共和国非法出版物的重要工作者,一些易燃、易爆品经他暗中操作流布于世。
作为出版人,野夫同专制体制长期周旋,实施着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的游击战——他把二渠道反讽性地当作了井冈山。但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人有很长一段时间都不知道,野夫还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诗人和作家——也许,这才是他被遮蔽多时的老本行和旧身位。
新世纪以来,野夫写下了一批力透纸背、光彩夺目的文章:《地主之殇》、《组织后的命运》、《坟灯》、《江上的母亲》、《生于末世运偏消》、《别梦依稀咒逝川》、《革命时期的浪漫》……这些文章旨在通过家族中人或友朋的遭际,揭露极权制度如何在摧残宝贵的人性,如何在矢志不渝地蚕食世世代代中国人赖以为生的价值观念。
这是一种惹人深思、让人久久无法释怀的文字,这是一种催人泪下,却只能让读者一个人向隅而泣,并经由暗中的泪水透视惨痛历史的文字。
作为一种“在历史上从未摆脱过政治暴力的重压,倍受意识形态的欺凌,怀旧、撒谎、孤立无援却又美丽无比的”语言(张枣语),汉语的光芒在野夫笔下得到了恢复,得到了张扬,诚实、诚恳,而又无比节制。但让人惊讶的是,即使在述说惨痛之极、压抑之极的故事,野夫的文字竟然无比灵动,毫无凝滞之态,有一种风行水上的感觉,顶多是飘逸、向往自由的风被故事拉拽了一下而已。
沉重和土地有关,飘逸则同天空联在一起。这是汉语当仁不让的两个极点。野夫充分展示了汉语的土地特质与天空特质,他的文字是土地与天空按照某种比例的神奇混合。中国的历史太沉重,土地特质因此始终是汉语的焦点;汉语的天空特质则必须受制于它的土地特质,汉语的天空始终是同尘世相混合的天空、是被土地震慑住的天空。
野夫深谙汉语的两极性,而汉语的两极性则为他的写作对象提供了绝好的对称物和衍生物。听命于语言,但更应该听命于情感,尤其是情感中沉重的历史成分:野夫恢复了汉语内部最正派、最高尚的那部分品质;经由这些品质的指引,野夫拯救了一种被官僚体制糟蹋、蹂躏了多年的语言,拯救了不止一种被国家意识形态凌辱、猥亵了一个甲子的文体。
熟悉野夫传奇生涯的朋友或许都知道,完成于德国科隆的中篇小说《1980年代的爱情》,不过是对一个真实故事有限度的加工、改写和润色。诗人赵野——他和野夫相交甚深——的简略叙述,或许能够充当《1980年代的爱情》的大致纲要:中学时,野夫“喜欢上一个女生,写了情书,却被她交到学校,引起一阵风波。
几年后他大学毕业,分到一个偏远的乡镇,碰到她在那儿的供销社卖酒。此番两人都春心萌动,她深知他终不会为这大山所困,也无怨无悔。
后来他果然远走高飞,一片锦绣前程。89年他逆势而为,落难回乡,她已嫁为人妇。随后他身陷囹圉,囚车离开之日,她还来送行。几年囚徒生活结束,他回乡来接父亲的骨灰盒,老同学为他接风,她也在场。此时的他一无所有,形如枯木,心如死灰。
她留他多住一日,撕了他到武汉的客车票,另为他买了机票。那晚,她把他带到酒店,用一个女人全部的母爱和柔情,温暖他已枯竭的身心。次日,她送他到机场,给他一个封好的信封离去。
飞机上天后,他撤开信封,里面有3000元现金和一封信……”小说与现实的唯一差别是:小说中的主人公丽雯得癌症去世了,留下一个女儿,被“我”抚养成人,现实中的主人公“虽然岁月沧桑,韶华已逝,眉宇间几分英气尚存”(赵野语)。
1980年代的青涩青年如今已到秃顶中年;1980年代的初恋如今早已成为回忆的对象:它是那个年代过来人记忆深处的隐痛。希姆博尔斯卡有一个非常好的诗句,无限沧桑尽在其中:“我为将新欢视为初恋向旧爱致歉。”沧桑感是时间给予有心人的馈赠品。
野夫在德国科隆的不眠之夜,回望遗留在祖国的青春和初恋,仿佛是在回望自己的前世或来生。过来人都愿意承认,1980年代是奇迹,是共和国历史上罕见的清纯时代,是废墟上生长出来的好时光。
那时,野夫年轻,爱情更年轻;那时,野夫纯洁,不敢亵渎神圣的爱情。在1980年代,拉手、在夕阳或月光下散步,是爱情的万能公式;蔑视权贵和金钱,崇尚才华和艺术,则是爱情的最低标准。不像现在,一切都需要货币去定义。因此,前世的爱情构成了野夫心中隐秘的骄傲,但那也是整整一代人的骄傲。他回望80年代,是为了给今天疗伤,是为了讽刺今天,还是为了给自己增添活下去的力量?
很显然,野夫算不上虚构能人,他仅仅是一位非虚构方面的大内高手。幸运的是,他的传奇经历本身就是小说,在贫乏无味、缺少故事的我辈眼中,已经是结结实实的虚构。《1980年代的爱情》之所以感人至深,很有能力挑逗读者的文学味蕾、考验读者的泪腺,仰仗的不是故事情节的复杂(故事情节一点都不复杂),而是野夫对汉语两个极点的巧妙征用:在需要天空特质的时候,他让读者的心绪飘忽起来,沉浸在对初恋的回忆之中,轻柔、感伤和对远方的思念统治了读者;在需要土地特质的时候,他让读者的心情向下沉坠,沉浸在对那段荒诞历史的思考之中,漫无边际的沉重统治了读者。
野夫在小说叙事中,对天空特质和土地特质毫不间断地交错使用,按摩着读者的心绪,让他们从头至尾都处于坐过山车的状态,肾上腺激素居高不下,配合着、应和着速度加快了二分之一的心跳。
对汉语两极性的重新确认和巧妙使用,是野夫迄今为止全部文学写作的最大特色,是他有别于所有其他中国作家的奥秘之所在,也是他以区区数篇文章和少量小说,就彻底征服读者的秘密之所在。放眼中国,或许找不出第二个人会像野夫那样,如此看重和依靠汉语的两极性,甚至是过度开发和使用汉语的两极性。
这让他的文字像书法中的魏碑,古拙,奇崛,方正,守中,从表面上看毫不现代,但无限力道却尽在其间,以至于能够寸劲杀人。《1980年代的爱情》取得的成就溢出了小说的边界,它让读者越过故事,直抵语言的核心部位;它让读者欣赏的是语言本身,而不仅仅是过于简单的故事。
这让人很自然地联想到钱钟书的《围城》。如果没有语言自身的狂欢、撒野和放纵,《围城》恐怕连三流言情小说都算不上;如果没有魏碑式的语言从旁压阵、助拳,作为小说的《1980年代的爱情》该会多么单薄。
和《围城》一样,《1980年代的爱情》也以对语言自身的开采,为自己赢得了应有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