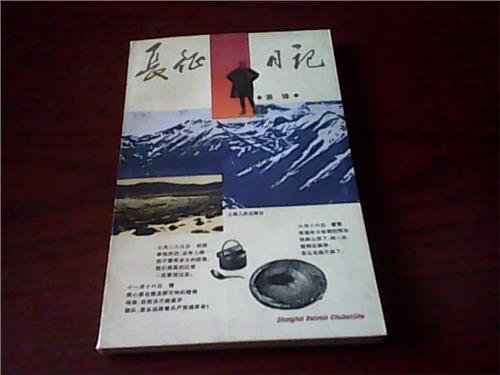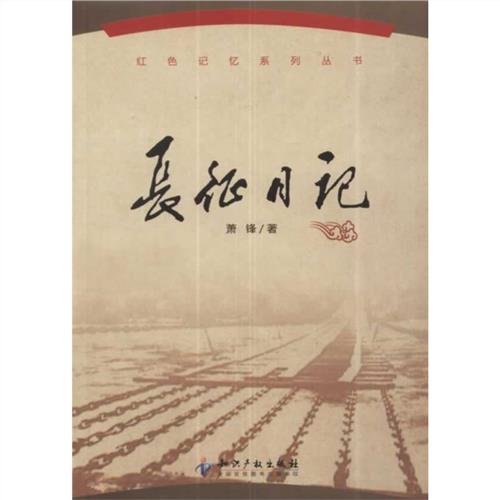萧锋的股事 萧锋少将的长征日记
萧锋少将,1928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图为萧锋在长征途中抵达六盘山西麓兴隆镇。
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就地召开的两河口会议提出了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由于胡宗南重兵控制经松潘北去的交通要道,红军不得不决定取道草地北上。
根据党中央的计划,红一、红四方面军被混编为左、右两路军,穿过松潘大草地。右路军在毛泽东、周恩来、徐向前、叶剑英等率领下,从毛儿盖出发,绕过松潘穿过草地向班佑前进。左路军在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等率领下,由马塘、卓克基出发过草地向阿坝地区开进。
1935年8月,中共中央和红四方面军指挥部率领的右路军自毛儿盖地区出发,正式进入草地。经过7天的艰苦努力,右路军终于到达班佑地区,创造了长征史上的奇迹。
萧锋日记——
1935年8月24日 时雨时雪
早晨起来,肚子饿得咕咕叫,原来准备的青稞麦炒粉,被雨淋得变成了疙瘩,只好烧些开水泡成面糊糊,加上几片肉干充饥。从军团首长到每个战士,都吃一样的饭汤。我们正在吃的时候,忽然下了一阵白雪,落在汤碗里,大家笑着说:“天下白糖,增加营养。”饭虽然简单,汤也不好,可是这么多战友集中在一起,热情交谈,倒也别有风味。
部队沿着荒无人烟的地区前进,右侧是大森林,左侧是一望无边的草原,间隔不远还有一片水汪汪的洼地,景好看,可路不好走。大家都拿根棍子当手杖,吃力地走着。
午后三时,看到神炮手赵章成同志身体不好,由叶青山同志换他下来搞后卫收容,前面掉队的和后面大队混在一起,拼命地赶路。
最讨厌的是草地的烂泥潭,远看像一堆水草,人和骡马走过去,一不小心,掉进去就越陷越深,救都救不出来。
侦察连六班长崔华义同志,江西黎川县人,二十五岁,陷入了泥潭,我们收容队十多个同志千方百计地抢救仍无效。崔班长为革命牺牲,我们在白茫茫的草原上为他开了追悼会。
荒草泥泞,路越来越不好走。向左侧看到电台摇机员也走不动了,我们赶紧组织几十名同志,帮助他们背枪,背干粮袋,减轻他们的负担,保护电台机器安全过去。
司令部和野战医院的十几个炊事员,挑着伙食担子艰难地走着。他们的任务比谁都重,每到宿营地,同志们都休息了,他们还要烧水做饭。当看到有些瘦弱的战友倒下时,他们难受极了。我担任收容队长,看到战友们倒下了,心里更难过。
我跑前跑后,招呼医生和卫生员拼命抢救。没有药品,医务人员只好推拿按摩,进行急救。有的病号按摩无效,很快就停止了呼吸。我们的眼泪像珠子一样滴在战友的遗体上。草地不能久留,只好忍痛告别战友的遗体,扶着那些还有一口气的同志,拉一步走一步,顽强地向前迈进。
草地里,没有地图,没有向导,迷雾满天,有时围着草地推磨子、转圈子,前卫成了后卫,后卫又成了前卫了。晚达达西多奇草地东山原始森林里露营,行程约五十多里。
1935年8月25日 阴雨
这几天不是下雪就是下雨,给行军带来更大困难。
清晨出发,部队刚走到班佑河花滩,发现右侧敌人骑兵一个多团向我冲来。我一师一、二团展开战斗,打了半个小时,分三路向敌人包围过去,打死打伤敌一百五十多人,缴获五十多匹战马。
晚达嘎德纳合东山(海拔3637米)的森林边露营,行程六十里。看到徐向前、陈昌浩骑马前进。今午后还看到张闻天、李德骑马随纵队右侧前进,看样子李德没有病。
粮食和野菜吃光了,饿得没办法。炮兵连炊事员苏清伍同志说,穷人过年过节买不起肉,就捡财主丢掉的猪皮煮汤吃。他一提醒,大家就把牛皮带、枪皮带、旧牛皮鞋用水泡后煮了吃。我的皮包装过盐,煮好后吃起来还挺有味道,有的同志开玩笑说,真像墨鱼炖鸡的味道。许多同志因病、伤、饿,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倒在路上,实在悲痛!
1935年8月26日 阴雨
进入草地第四天了。
清晨出发,到分水岭东南宿营,究竟走多远无法正确计算。好多单位都没有粮食了,菜和肉干也吃光了。军团政治部民运部有位干事,过分水岭不久,就突然倒在草地牺牲了。
草地的水因为长年泡着腐草,又黑又臭又有毒,根本不能吃用。口干得要命,有的喝了几口,肚子马上发胀,甚至胀死。脚上被草根刺破,毒水一泡,就红肿溃烂。
炮连神炮手吴民选班长,江西于都县人,十四岁参加红军。他肚胀、脚肿,两天没吃东西了,走不动,战友们轮流背,背不动,就用木架当滑车拉。这样坚持了两天,实在不行了,快咽气时他拉着我的手流着眼泪说:总支书,你们快走吧,不要管我了,快跟着毛主席打出去。有空时给我家去封信,告诉我妈妈、哥哥、姐姐,叫他们好好活着,工农革命一定会胜利的。
侦察连三排战士张伍才,福建人,二十五岁,刚进草地时,是尖兵班的开路先锋,昨日掉队,饿得头昏眼花,半夜追赶队伍,陷在烂泥潭里,无法出来,光荣牺牲。
工兵连三排副排长,是位非常好的同志。一路上,他为老弱病残的战士背枪,搀扶病号行军,可自己太累了,在路上稍一休息,就中风致命。
警卫连战士卢堂宝,江西兴国县人,十九岁,参加过中央苏区第二、三、四、五次反“围剿”。这次过草地,因吃草蘑菇中毒牺牲。
天黑后,一军团前指在桑白抬合东山(海拔3543米)的森林边露营。军团聂政委找我去汇报军团前梯队四天过草地的情况。我说,根据十四个单位统计,已掉队二百五十人,牺牲一百二十多人。大家心情十分难过。聂政委指示,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注意发挥党支部的堡垒作用。没有粮食,就拔野菜、选野菇、割皮带吃,担子挑不动就丢掉吧。实在不行时,骑的骡马也可以杀掉吃。
许多掉队的战士,连病带饿,有的连拔野菜、选野菇的力气也没有了,看了心里实在难过。四个军团在这草地上,困难实在多。前面的部队把野菜、野菇吃光了,后面的部队就没有什么吃的东西了。有的同志实在饿得没有办法,看到前面部队拉的屎里还有没消化的青稞麦,就一粒一粒拣出来,用水洗干净,再用茶缸煮了充饥。
半夜,通讯连汇报,三个通讯员和一名炊事员吃野蘑菇中毒,有的快要断气了,有的浑身发紫,得赶快抢救,并通知大家注意。
1935年8月27日 阴雨
今天是草地生活第五天了。晨出发,经佑括合进到若隆嘎附近宿营,行程六十里。饿得头昏眼花。听说还要两天才能走出草地,真急人!
午前有两架敌机窜来捣乱,草地无躲藏,让它去。
军团直属队已掉队三百多人,牲口也死了不少,许多重物淤陷在草地。
工兵连二排长丁华齐陷入泥潭里,刚喊救命,转眼就被深泥潭吞没。
一军团前指晚在求吉南哇分水岭(海拔3659米)西山处露营。
晚上,同警卫连连长尹国赤同志等在一棵大树下过夜。尹连长说,七班长高才秦,江西于都县人,过草地挖野菜时被毒蛇咬伤,中毒身亡。他临死时讲,你如能出去,请写封信给我家,我是为保卫苏维埃红旗而死的,请家里人不要难过。
过草地,一直是长征中最艰苦也最神秘的一段。
今天,我们再次走进,回望那段历史。
在沙窝和毛儿盖,我们回想了当年复杂的路线之争。在曲定桥(七星桥),我们追溯了红军出发时的壮怀激烈。在年朵坝草地,我们亲身体会了红军过草地的艰苦卓绝。在巴西乡,我们感受到那支队伍胜利北上的喜悦。
这一切,都让我们明白,红军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都让我们知道,长征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都让我们坚信,怀揣信念,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2016年9月8日 时晴时雨
我们想象得出那支勇敢的部队,壮怀激烈走入草地的样子
在四川省阿坝州松潘县镇坪乡,我们见到了当地唯一健在的老红军尹全学。105岁的他端坐在自家的庭院中,穿着朴素的衣裳,身子骨还算硬朗。
老人家耳朵已听不大清,我们只能凑到他耳边大声喊出我们的问题。尽管如此,他能听到的还是寥寥。只是在我们问到他怎么负伤时,老人家突然抬起头说:“你们要看我的伤口吗?”说话间就要脱下衣服。
我们赶忙摆手示意不用,于是他停了下来,眼睛望向远方,口中喃喃自语:“民国二十四年……”那是1935年,红军过草地的年份。
尹全学的养女告诉我们,父亲很少提起从前,但是只要把剩饭剩菜倒掉,老人家就会发火:“我们在草地里的时候没吃没喝,多少战友就活活饿死了。你们现在就这么浪费?!”
告别了尹全学一家,我们踏上了寻访沙窝会议和毛儿盖会议旧址的路程。正是这两次会议,决定了红军要向大自然闯出一条生路——过草地北上。
四川盆地山峦叠嶂,道路亦依地势起伏延绵。地图上看似挨着挺近的两个点,实际开车却要七弯八绕开上半天。从松潘县城出发,去往两次会议旧址,百余公里的路程,开车需要近6个小时。从高速公路转进坑洼不平的县道、乡道,我们的车也随即切换到了“振动模式”,一路上还时不时有牦牛挡道。虽然当地羌族司机经验丰富,但是糟糕的路况和高原反应,还是让坐在车里的我们吃尽了苦头。
终于到了毛儿盖,我们没怎么费力气就找到了当年毛儿盖会议的旧址。这座喇嘛庙已经恢复了宗教用途,我们去时喇嘛们正聚集在大殿诵经。大殿旁边,有一小块“毛儿盖会议旧址”纪念碑,上面挂着藏族特有的哈达,还摆满了不少鲜花。
接着前往沙窝会议旧址,这仅仅几公里的道路可能是我们经历过最艰难的道路——如果那可以称之为道路的话。好几次,“放弃”都出现在我的脑海中。好在我们坚持了下来,摇摇晃晃间,来到了目的地。这是一座典型的藏式建筑,下部是厚厚的夯土,上部是木质的结构。
走进其中,发现内里格外简陋,顺着木梯爬上三楼,最里面的一间小房间就是会议召开之地。难以想象,如此狭小的空间,党和红军的重要人物竟然齐聚于此,共商大计,实在令人感慨。
返回的路上,我们找到了当年红军出发进入草地的入口——七星桥。多少年过去了,桥下的河水依然湍急,石桥仍旧岿然。站在桥上,我们想象得出那支勇敢的部队,壮怀激烈走入草地的样子。
2016年9月9日 时晴时雨
就如同有一只无形的手,一把抓住了脚,并且拼命地往下拽
今日探访真正的草地。
顺着213国道一路飞驰,很快就深入了当年的松潘大草地。在年朵坝草地,红军三过草地都经过的地方,我们徒步体验了当年的感受。
松潘大草地平均海拔近3500米,高原反应肯定是挥之不去了。来自城市的我们在车上时已经颇感头痛,在草地里走得稍快一些就觉得头晕气喘,大口呼气的样子连自己都觉得好笑。红军当年行军比我们如今的强度高上百倍,不少战士一定也饱受高原反应之苦,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巨大的温差也让我们倍感不适:太阳高挂的时候,觉得酷热难耐,穿着短袖还能被蒸出满头的汗水;如若飘过一片云彩,又一下变得无比阴冷,穿着外套似乎都抵挡不住一个劲往身体里钻的凉意。来回一折腾,若是身子骨弱些,肯定生病。据说红军当年都是单衣薄衫,晚上宿营只能围坐在一起,有时早上醒来,有的战士已经坐着牺牲了。
气候也极其多变,雨水说来就来,毫无征兆。往往前一秒晴空万里,后一秒就天降大雨,有时候还带着冰雹,砸在脸上身上,还真有些疼。即便我们身上穿着轻型羽绒服和冲锋衣,还是觉得顶着风雨前行,是一件容易让人绝望的事。
随着地质地貌的变化和水土流失,加之当地排水疏干和建设公路,如今的松潘大草地已经难觅大面积的沼泽。然而那些仅存的小小泥沼,依然保留着危险的气息,似乎随时准备将不识相的外来者拖入陷阱。在一处泥沼前,我们体会到了这份来自大自然的恶意。
随意扔下一枚石块,立刻沉入其中不见了踪影。我们一人负责保护,另一人试探性地用脚踏入其中,淤泥不由分说地就将鞋子包裹了起来。就如同有一只无形的手,一把抓住了脚,并且拼命地往下拽。当然,我们并没敢继续“作死”,但草地“陷阱”的威力,已经真实地展现在我们眼前。就像影视作品里表现的一样,当年的红军,饥饿、乏力,稍不留神就会陷入这死亡的深渊。
困扰红军的饥饿,我们也感同身受。为了赶在天黑之前完成既定任务回到松潘县城,我们决定不吃午餐。况且进入草地后,笔直的公路两边,除了草地还是草地,并没有任何可以坐下来吃口热乎饭的地方。很快,远超平日在都市里的运动消耗,让我们迅速体会到了饥饿的痛苦,直懊恼没有带足干粮。在草地里灌矿泉水充饥,或许是我们此行中最能体会到红军当年艰苦的时刻。
一路往北,我们来到红军当年草地中看到的第一个村庄——班佑。在班佑的国道边,竖立着一座巨大的纪念碑,上书“胜利曙光”四个大字。据当地工作人员介绍,纪念碑立于2011年,为的是纪念在此处悲壮牺牲的近800名红军战士。80年前,饥寒交迫的他们历尽千辛万苦走出了草地,却最终没能走过班佑河,倒在了这里。就像王平将军所说,他们带走的是伤病和饥饿,留下的却是希望的曙光。
离开班佑,跟随红军的足迹转而向东,我们又到了包座一带。在这里,红军打响了“包座战役”,歼灭了尾随之敌,打通了北上的通道。在当年的战斗遗址,摸着墙上的弹孔,我们不禁想问,这样一支刚刚经历了草地磨难的队伍,怎么能焕发出如此惊人的战斗力?
或许,这就是长征精神,勇敢、坚持的精神。
2016年9月10日 晴
那是一种坚毅而悲壮,同时喜悦与伤感交织的深沉表情
从上海出发之前就被告知长征纪念碑碑园目前正在闭园修整,但是我们仍然决定去一趟:从形式感的角度考量,没有什么地方比这座位于川主寺镇的纪念碑,更适合作为此次寻访之旅的终点了。
川主寺镇距离松潘县城并不算远,仅需大约半小时的车程。一路上路况极佳,让前两日在全程“振动模式”的山路上吃尽了苦头的我们,感受到了久违的畅快。
然而盘山路一个急弯连着一个急弯,对车技着实是不小的考验。司机师傅是当地人,开得很是游刃有余,甚至显得有些漫不经心。然而坐在后排的我们,每一次过弯时还是紧张得不敢说话。
车刚刚行至川主寺镇境内,就已经能看到矗立在远处山顶上的纪念碑碑体上方的铜像:红军战士右手握步枪、左手执花束,高举着的双臂形成一个大大的“V”字。
“Victory!胜利的意思嘛!”司机师傅打着方向盘,嘴里蹦出了个带四川口音的英语单词。
司机师傅告诉我们,松潘县的当地人习惯把纪念碑唤作“红军长征总纪念碑”——突出的是个“总”字:“这纪念碑和别处的不一样,纪念的不是某个会议或者某场战役,而是纪念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这整个历史事件!”
说到此处,司机师傅的脸上难掩自豪与得意。
来到红军长征纪念碑碑园,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抱歉地告诉我们,不仅碑园各处都在进行翻新工程,就连设在碑园内的纪念馆亦在闭馆整理展品。但是他仍建议我们务必去看一看纪念碑,并特意提醒:“一定要一级一级台阶走上去,跟站在山脚下看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长征纪念碑,也就是司机师傅口中的“总碑”,位于元宝山山顶,是整个川主寺镇的制高点。自1989年10月正式落成起,纪念碑就成了川主寺镇最醒目的地标。
走到山脚下,长长的台阶一眼望不到头。虽然纪念碑碑体高达24米,上方的红军战士铜像高达14.8米,但站在台阶处往上看,却只能看到铜像那高举着的双臂。
说实话,我们有点心虚。犹豫了两秒钟,我们决定走上去。因为我们相信,相比远远地眺望,真正站到纪念碑下,一定会有特殊的感受。
在海拔近3000米的地方爬楼梯,断然不是什么愉快和舒适的体验。我们手握运动摄像机,原打算将整个爬梯过程完整地记录下来,然而却不得不一次又一次暂停拍摄,努力调整呼吸之后才能继续。最终,爬梯的主视点视频被切割成了五段。五段视频的时间一段比一段短,不仅画面严重摇晃抖动,录制得最为清晰的声音竟是拍摄者沉重的喘息。
终于,我们成功了。山顶上、石碑下,终于看清了铜像的表情:那是一种坚毅而悲壮,同时喜悦与伤感交织的深沉表情,那是越过雪山、走过草地、渡过赤水河、经历过重重艰难险阻、突破了重重包围封锁的强者们才会有的表情——那是胜利者的表情。
是的,在海拔3000余米的元宝山,我们进行了一次“朝圣”,与无数先烈完成了精神上的会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