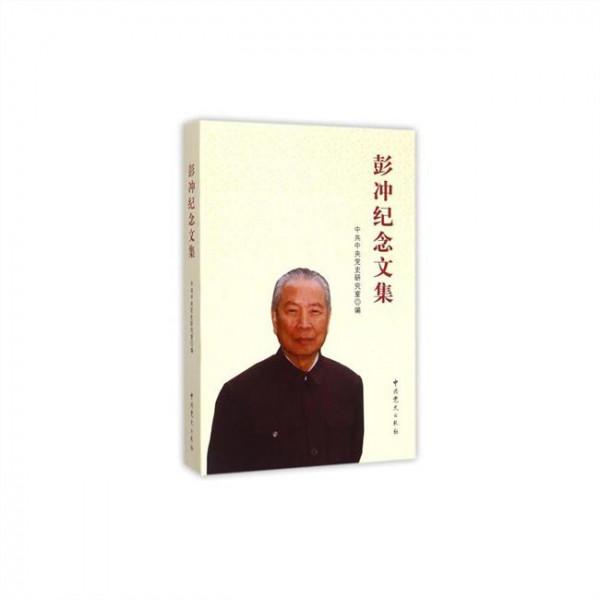蒯大富近况 红卫兵领袖蒯大富近况
蒯大富:“红卫兵领袖”的人生回归从今天的视角看,这样一个经历了“政治过山车”的人,他的身上有摆脱不了的时代印记,他的回归之路则浓缩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和现实。出于对历史的尊重和对人的命运的关切,我们采访了蒯大富。
64岁的蒯大富,身体已经欠安多时。交谈的时候,面部肌肉偶尔会出现抽搐,话说到一半,间或会戛然停止,陷入思索。过去4年,这个身材壮实的老人,三度被中风击倒,每次又都重新爬了起来。最近的一次,看样子还不是太糟糕,语言和行动能力毕竟都没有丧失。
他自己将这种奇怪的恢复归结于180副中药的功效。罗晓波却认为她的丈夫正每况愈下。这个小蒯大富17岁、瘦小黝黑的女人,快人快语得有些出人意料。“你现在来,他还可以和你交流,要是明年来,就困难了……越来越糊涂。
”疾病缠身的蒯大富,目前正在为自己操持也许是此生最后一件大事:补办社会保险。但此事并不顺利,奔忙了半年多,一直没有拿下来。“他们和我谈条文,说我不是调进深圳的,是迁进来的;交养老保险的时间又不够15年。
按条文肯定是不行的,”蒯大富说,“但怎么发生这些事情的?这是特殊历史条件遗留下来的问题。因为我是蒯大富,这是核心问题。”为补办社保他走了不少关系,不免有些心烦意乱。
有一次去见社保局某位领导,领导在12楼办公,发现这一层电梯的按钮是被取消的,没法停靠,他就下到10楼,再步行上楼,结果那一层楼道门口也上了锁。座机、手机均无人接听。在此之前,社保局发生过官员被人锤砍事件。
蒯大富受到“此路不通”的刺激,即给那位领导发去短信,“百姓与您的联系被切断……我有点理解社保局官员为什么被砍。”“出狱这么多年,到哪里都干不成,但是不管怎么样,跌跌撞撞、踉踉跄跄,也走过来了,自己谋生吧,也还可以,”蒯大富说,“有人建议我们成立一个‘蒯大富救助基金会’,我说这种事不能干的,不能让人对政府失去信心了。
”世事无常。30年前,命运之手将蒯大富从人生最高处推落,此后多年,一波三折的变故,促使他由一个“红卫兵领袖”向普通人序列回归。
现在的蒯大富,也许还没有完成这种艰难的回归。这个掉入尘埃的前风云人物,情绪并不低落,性格也不全然像罗晓波提及那样古怪。他的身上,显现出更多平常人的脾性。
谈吐幽默,能一连讲出不少官场笑话。这种状态能够保持至今而不被消蚀,也算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北京蒯大富的一生遭逢,都与北京有关。在这里,他前后呆了29年,至今仍对此地不无怀念和好感。事实上,在15年前,他们就曾尝试过接近北京,结果半路遇挫,又灰溜溜地离开了。
1992年,在罗晓波的推动下,蒯大富离开宁夏青铜峡铝厂,跳进了市场经济的“体制外”漩涡中,到山东一家企业工作。一年时间不到,“想干点事儿”的蒯大富就又跳槽了。
他准备重返北京。当时,北京一家街道办企业计划在北太平庄兴办通讯器材一条街,有意引进蒯大富来打理,并将此举称为改革开放新举措,给出的条件是:到北京后,蒯大富必须合法经营、不干政治。
尽管有朋友规劝他们不要进京,以免引来麻烦,但想着大展拳脚一番的蒯大富,还是让人风风光光地用专车接进了北京。此后,一个多月时间不到,形势突然发生了变化。他们的公司怎么也注册不下来,据传还有指示要客客气气地将蒯大富请出北京。
蒯大富当时表示,可以不当董事长、总经理,自己就在北京支起牌子擦个车、修个鞋、开个小茶馆儿,但没被允许。“走的时候就比较惨,没来得及跟我们商量,老总和他太太又拿车把我们送回山东。
10几个小伙子,开着个装肉的冷餐车,把我们的东西往纸箱里一塞,把门一锁就走了,像逃难一样。”为了让孩子能上一个完整的幼儿园,去而复返,罗晓波独自带着女儿又回到了北京。在此前后她自己已经找了一份工作。
但不久就被迫辞职了,因为她当时接受了一个采访,公开抛头露面,谈论自己与蒯大富的生活。“怎么可能让你那么猖狂?有些东西,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我带着孩子在北京,就感觉到处有人和你为难,但真不知道那是谁。
”在北京没能干出一番事业的蒯大富,回到山东感到没脸继续呆下去,又折到江苏去,结果那边也对他关门谢客。这样四处碰壁,蒯大富却并不感到已经陷入绝境,总觉得终究会有一条出路。这种心态,在沦为阶下囚的时候也没有打断过。
尽管他自己也承认,这样一段日子,有时候是很心酸的,但当时又比较容易找回心态平衡。1970年代,“有人一拍桌子,说把蒯大富‘拉出去’。当时要是把我‘拉出去’,也就‘拉出去’了。所以那时候我就想,活一天就是赚了,能活着就很不错,不要说活成什么样子了。
”商旅“三十年河东,斗私批修,灵魂深处闹革命,革命尚未成功;三十年河西,成家立业,身体力行搞经营,经营初见成效。”2005年,蒯大富60岁。在深圳,他大宴宾客,高调庆生,座中有吴桂贤、韩爱晶等人物。
这一幅横批为“六十大富”的对联,当时就张贴在宴会厅的门楣上,像是在公开宣告着什么。当能走的路都被切断之后,经商就成为蒯大富融入社会的一个途径。而当年造就的名气,为蒯大富的日后行商铺就了一条捷径。
第一次尝试,是在宁夏青铜峡铝厂,有段时间铝不好卖,厂里请他出马。他带着老婆、孩子在外面一逛3个月,卖了605吨铝,拿回去605万元。生意做得这么顺利,是因为知道他的人太多,“厂长、处长一般都是我这个年龄段的,下面报告说,蒯大富来卖铝了,那是很愿意见的。
我立刻就可以见到他们的最高领导。买个面子吧,你得用铝,我们价钱也还行,你买我100吨,那好商量了。
”1994年,数度辗转来到深圳,蒯大富和他的清华同学联手经营一家音响设备工程公司。第一单,接的就是从前一位老部下的业务,这是一家国营单位,他为他们装了一层楼的音响系统,老部下则替他报了黑价,1000元成本造价被报到了1.
4万元,当场提成给蒯大富1.5万元。当时的中国,万元户还寥寥无几,拿到这么一笔巨款,蒯大富感到“非常恐怖”。当年的深圳,老清华毕业生据说就不下5000人,差不多都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
蒯大富名声在外,上门拜访,人人买面子,和他同学合作4年半,总业务量做到了9000多万。按约定,他应该从中提成90万,但那同学掏钱如同割肉一般,最后只给了22万外加一套房子,总计40来万。蒯大富后来选择了单飞。
但是病来如山倒,之后没有人能替代他的角色出去跑业务,他的公司接着也垮了。“人要发财,有四个条件,缺一不可,”这些经历,让蒯大富悟出不少道理,“第一要勤奋,有单就去跑,有机会就抓住;第二是聪明,要知道怎么谈生意;第三靠运气,再勤奋聪明,运气不好也不行;第四就是德行要好,待人要宽厚。
差一条,肯定发不了财。”商海漂浮15年,他已经是个腰缠万贯、事业有成的商人,高调得仿佛得到了新生一般。这从他那一大摞与各界名流会面的影像中可以看出来。
“商业上,我也没有什么造诣,但养家糊口可能没问题,”蒯大富说,“毕竟我是清华大学毕业的,我学嘛,也不是什么高深得不得了的事。”但终究名气太大,有关方面也要关照一下,有事没事会约他出去喝个茶吃个饭K个歌什么的。
15年来,就这样相安无事地生活着。蒯大富也明白自己的处境。当年一到深圳,为了躲避那些蜂拥而来的港澳及境外记者,他另给自己起了一个名字叫“戴明”,以便缩小被干扰的目标。
波折太多,一家人尽量避免任何是非,他们住的小区,业主委员会发起维权,叫了他们好几次,他们都坚决回避,不愿介入这种群体事件。但那个历史上的包袱,始终若隐若现,并没有完全摘脱。1990年代末,办理户口调动,就遇到了不少麻烦。
根据地方的规定,只有当地户口,孩子才可以上当地的一些好学校,他们的女儿没有当地户口,申请报告交上去每次都石沉大海。最后在旁人提醒下,蒯大富和罗晓波协议离婚。申请表上没有蒯大富的名字,不出几个月户口问题就落实了。
蒯大富将此看作是晚节不保,是一种被迫投降。“他是不食人间烟火,我让他稍微屈服一下,他说什么户口?怎么可能?很倔的那种人。”但在多方劝解下,实在没招了,也只得低头。
直到现在,他们也没有复婚。他们的女儿,曾经要求罗晓波立一个书面保证,在蒯大富有生之年,绝不会改嫁他人。她拒绝了。“我从南京嫁到宁夏的时候,他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劳改犯。有什么需要保证呢?我是深圳义工,别的孤寡老人我都管,何况是我孩子的父亲,肯定是要为他养老送终了。
”晚境早早被历史巨浪送上了岸边,那样一段经历,却成为蒯大富和清华一班同学日后聚在一起的永恒话题,而且谈的每每都是细节,这让罗晓波有些搞不懂。
故事听得多了,曾经是“红小兵”出身的罗,就认为她丈夫充其量只是一个政治爱好者,并没有什么政治智慧。而他之后的身败名裂,在她眼里,也只是一个由于某种阴差阳错被卷入不同派系争斗的“打手”“爱凑热闹、好出风头”的性格缺陷使然。
“当年毛主席向清华派驻‘工宣队’,表明红卫兵都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嘛,他们还和人家打起来。什么3个人逃出来发电报,‘清华井岗山(兵团)正在血泊之中,向毛主席呼救’,你说他有什么政治智慧啊?反正我听着就跟听个笑话似的。
”1970年至1987年,由北京而宁夏,蒯大富过了17年牢狱生活。外人以为这段经历很悲惨,当事人却不以为然。当年在狱中,他还为狱警即将考大学的儿子补习课文,全然没有一点坐牢的样子。
他说,“我这个人一贯就是这样,40多年,一直坦然地活着,从来不认为自己悲惨。最悲惨的时候也不这样认为。”老来怀旧。2008年至今,蒯大富先后两次带着妻女去宁夏,专程造访当年关押自己的劳改农场。
那个地方早已经被废弃,长满了杂草。故地重游,颇有一番感慨。“有人问我,你坐了17年牢,冤不冤?一种意义上讲,跟着党干革命,最后坐的还是党的牢,很冤;另一个角度想,比起当年那些被我们整的干部,可能他们更冤。
我们犯了比较严重的错误,但他们没什么错误,有些还被整死了。相比之下,我们受的这些冤,也算不了什么。”在青铜峡,他感受到了底层人民的纯朴和友善,没有因为他的身份和遭遇而将他视作异类。
出狱之后,青铜峡铝厂不仅重新接收了他,还给他分了一套房子,这是很多年轻职工都没有享受到的待遇。在那段时间里,他们生活得十分开心。就这样过了20多年,每次回去,他们依然会受到热烈欢迎。那里有一批最铁的朋友。
蒯大富的电脑和相册里,保存了他过去和现在的记忆。书桌上,堆着各种各样已发或未发的书刊与稿件,其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别人给他的历史所做的记叙和整理。晚年,他有更为充裕的时间反思当年的一些事情。除了错整了一些干部之外,他认为与此同时发生的流血冲突,自己也负有责任。
这是让他多少年都后悔的事情。“当时我是我们学校的一把手,影响力是很大的。我们清华最后大规模打起来是1968年4月23日,如果当时我主张不打,那场武斗(百日武斗)肯定打不起来。
当时认识上发生了偏差,”蒯说,“有些是可以制止的,或者是应该制止的,但是没有觉察,导致死了十几个同学,都是很好的同学。看着他们死掉,是非常心痛的。”“我被推到那种位置上,有一种偶然性。
‘文革’,清华肯定是要出学生运动的,假如没有蒯大富,也会有张大富、李大富,具体落到我身上,就有很大的偶然性……我被树起来了,后来就身不由己了,被推上去,想退都退不下来。”这样一段复杂和纠结的历史,很难用一个简单的是非对错一言以蔽之。
近水楼台,他们的女儿,曾经嚷嚷着要拉罗晓波一道去研究那段历史,但罗晓波坚决不干,她怕碰触到人性的残酷和阴暗一面,况且要研究的这些人,又都是他们相识相交的。
每天,除了在家里为自己熬熬中药,大病初愈的蒯大富,现在还在一家同样是经营音响设备的公司担当顾问,主要的工作,就是利用自己的关系网络跑跑单,接洽一些业务。此外,3次病发,动摇了他那种“生命在于静止,千年的乌龟、万年的王八”的反潮流主张,经常也会跟着公司的年轻同事和下属出门远足。
在罗晓波的提醒下,蒯大富还坚持定期去做瑜伽,而且每天晚饭后要下楼散步。对于时事政治,他依然保有兴趣,但只限于旁观,也可以说是学习。
每天大致要挤出两个多小时翻阅各类报刊,了解各种动态。9年前,蒯大富去探望一位曾被他整得够呛的老师,他们都是从那个暴风眼里挣扎过来的人。他安慰老师,一定要把身体养好,不能弄潮,可以观潮;不能演戏,可以看戏。“这也是我目前的状态,”蒯大富说,“我们这些人,不想关心政治是不可能的,某些政策的变化,某些领导的变化,可能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