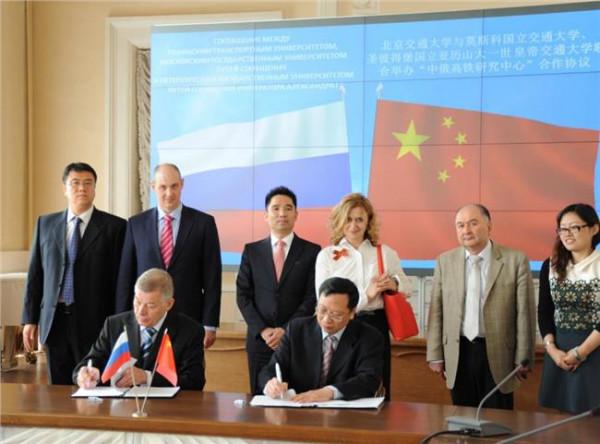专访张继刚:中国书画艺术是一束奇葩
2007年7月,张继刚接受台北国立艺术学院学述委员会主任著名学者画家《艺苑》主编赵妍教授专访。
赵:张教授你好!此次你应台湾大学、台北国力艺术学院之邀进行一周的学术访问,我注意到你时间安排很紧凑,就连朋友拜会也都是在晚间,没有时间观光。
张:是的,台北我来过多次了,每次过程都是这样,在学校及博物馆中度过,甚为愉快。
赵:我知到你在国外多所大学讲学展览,无一时不在推动汉学及中国书画艺术在国际艺苑中的发展,让更多的域外人士了解我们的历史、文明及艺术,使得中国书画艺术走向世界,您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你认为中国书画在国际艺苑中未来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占有什么样的地位?
张:中国书画艺术是人类艺苑中最具有魅力的一束奇葩,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智慧的结晶,随着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汉学在不断地被世界各国人士所接受,我想不久的将来汉语必定会成为世界各民族人民的通用语言,而中国书画艺术也随之必然被各国人民所喜爱,进入国际艺苑之中占有主流地位。
中华民族具有光辉灿烂的历史,与日月同辉的文明,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基石,艺术是民族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书画艺术更具有博大深的内涵,它完全能体现出民族之魂,真善之美!因此,我们必须要很好的继承和弘扬并且有责任来完成这一历史使命。
赵:你认为当代花鸟画如何发展,什么样的作品才是好的,还有哪些不足?
张:花鸟画从徐熙、黄筌创格至今,千余年来随着时代演变,风格也不断出新,但无论如何演变,花鸟画创作是秉承民族文脉及审美情趣的延续,这是让我感到十分悦愉与自豪的,也可以说是民族的文化动人之处。
花鸟画是怡情愉心的,是国人追求生活品质的再现,是人们对锦上添花的追求,花鸟画的创作不在于敷色的艳丽,而在于画家内心的营造和修养的境界,故此我认为当代花鸟画家书读的不够,对民族文化深层次的研究不够,没有体会到花鸟花画之灵魂及其内函的精神,花鸟画绝不是俗艳的而应该是如明月般的皎洁,雅姿逸态,这便是花鸟画的妙谛。
花鸟画的不足在于轻浮,这不是纸笔黑色的问题,而是画家心境修养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是无法进步的,也不会流芳艺苑,画格必从读书中来,才能得以雅正,这是规律也是百代画家的心得。
赵:你是一位有影响的学者、艺术家,请你谈谈你的学述思想与绘画实践中的追求。
张:我的学述思想是在二十年前初步形成,我认为从事文艺创作的艺术家,首先要有自己的思想体系,而这种思想体系的形成与完善,是离不开民族文化的熏陶,是在人生漫长岁月中不断的学习积累最终的实现。二十余年来我的感受是很真切的,严谨的治学细心的求证,是我治学的一贯思想。
我是从治美术史及古书画鉴定开始的,在学习过程中得到我的恩师杨仁恺、启元白、王利器、钱钟联、刘海粟等诸老的精心指导,在治美术史书画鉴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探求《说文》及古贤经典,对文字声韵学有所了解,亦对诗词创作算是通了门径。诸子之学是要从《说文》开始的,通了训诂治学的门径也就通了,中国画家是集诸学之大成而后才能完成自已的作品,要求是极高的。
我的绘画是从传统中来的,是在鉴定过程学到的笔墨技法,我的工笔花鸟画是从北宋时期作品开始入学的,体会到宋人严谨的法度和敷色的妙处,气象纯正和意境的深邃。写意画从近代画家学起,既知远古意亦追寻先贤,从宋元明清诸家中吸取营养又参苦铁、虚谷、齐黄之法进行裁解学习,虚谷作品是好的,格高于吴昌硕,吴氏熟艳,到了晚年还没有去火气,如果他不以金石书法及书卷气养画笔,作品是不能观的。
齐白石是好的,他虽没养成士人之气,但童趣愈老弥真,是十分难得的,是大聪大慧之人,从民间体悟到国人追求的真谛,行笔缓慢,得中庸之妙,有吉祥瑞象又能参似与不似之间,故不入俗格。
我的追求是带着许多问题进行思考的,参悟学习落到笔墨实处,体会古人心境与造化嬗变的过程,是实践笔墨技法与个人修养的完美结合,表现出气韵生动万物之象及自家风骨,追求理想中的境界和绘画品格中精气神,这是我在绘画学习过程中对自己的要求,也是这样做的。
赵:你对徐渭八大山人的作品是如何的理解,我认为目前学术界对两位古代大师的研究还不够深入,你认为是这样吗?谈谈看法。
张:是的,徐渭是明朝中晚期的一位著名文人,是中国美术史开宗创派的一代大师,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创造奇迹,为艺苑增添奇葩,是后人永远学习崇敬的。徐文长生不逢时,人生凄苦,作品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他内心的凄凉世界,笔墨纵横,秋霜泪雨,是徐渭一生的写照。
从徐氏流传的书画作品及诗词文赋中,可以感受到这位天赋才情的大艺术家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弥足珍贵的艺术作品,是值得我认真研究学习的。但目前学术界及画家在学习实践过程中的研究,我认为还不够深入,处于表面现象。徐谓不同于画史中的其他画家,他气韵高华,天趣胜于技法,逸态狂姿,若不是以大文人之气息蕴藉笔墨其画必流于疏野,终不能成正果,这一点是应该看到的。
八大山人与徐文长有别,笔墨之外而心境殊异,文长是生活中的凄凉,八大山人是国破家亡的痛苦,将生命中的痛恨融入水墨画卷之中,表现出墨水不多泪水多的凄凉景色,八大山人对儒释道有着深刻的慧悟,无论是笔墨还是花卉鸟虫的造型及构图都能反映出禅悟临济、曹洞两宗的最高境界。八大山人是中国美术史中的一座高山,须要有识之士坚韧不跋的攀登,最终才能感受到山的内涵和眼前无限风光。
研究八大绝不是疏浅于一花一木,一草一石之间的探讨,是要从深层次中探寻山人的哲思和晚年复归平静的心境,这是山人对人生了悟的终极。新中国成立以来,学述界对八大山人研究不多,倒是或外华人学者们先做了这方的工作,如:方文、王芳宇、饶选堂、王已千等诸先生的辛勤耕耘为后来学者打下了基础,这是八大的幸事,也是中国美术史的幸事,更是当代画家的幸事。
赵:我去年访问巴黎大学蒋梅村先生、耶鲁大学的张君范先生,两位国学大师都谈到你,并建议我访问你,在两位先生书斋读到你为二老及当代十位国学大师文集作的序言,令我惊叹不已!
张:说起序言之事,甚为惭愧,疏陋之学岂敢品评,浅思拙言刊于篇首,是令我至今不安的。在二十余年前我与恩师杨仁恺先过访沪上,拜识学界泰斗王蘧常先生,先生授我治学之道,言“想画好境界高须从读书中来”,我牢记老人之言请教诸师,下了一点画外功夫,对训诂考据学科有了兴趣,明确了自己的治学方向,治学之道是一生的事,须要锲而不舍终生努力,才或许有一点建树。











![[名家论坛]著名导演张继刚:我的艺术人生](https://pic.bilezu.com/upload/6/72/67297c2b7fdd3124704f89d6ff21b674_thumb.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