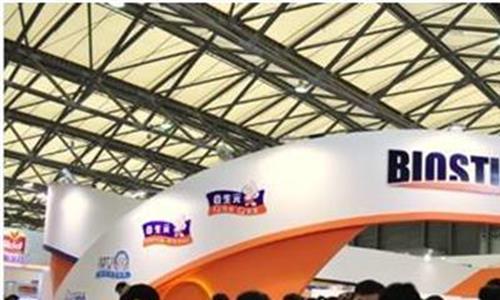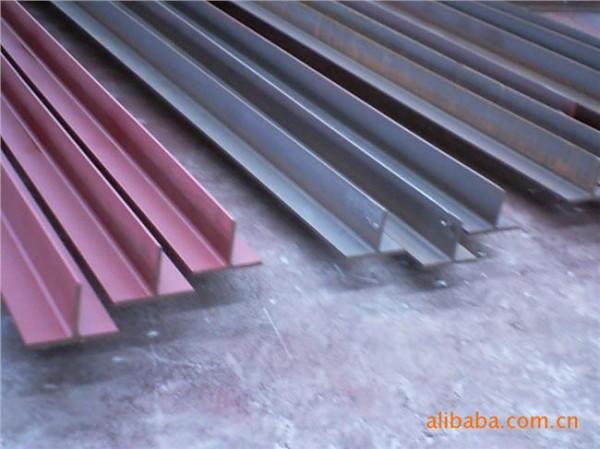马少华判处刑 马少华:比批评和建设更优先的是判断
近日,正在进行时评大评奖的搜狐网上,网友们对时评的评价标准——乃至时评的“灵魂与生命”进行了一番热烈的争论。
先是鄢烈山先生贴出《时评:建设性是嘛玩意》长篇文章,对几家“主流媒体”联合举办今年新闻评论最佳作品的评选启事中的所提倡的“理性和建设性”、“主流、建设性、影响力”,都进行了批判。接着孙振军先生贴出题为《批评是时评的灵魂与生命》的旧文以示支持,他这篇文章所批评的对象,恰是中青报青年话题版编辑冯雪梅的文章《时评的理性与建设性——兼论“青年话题”的编辑思想》。
这些论争是有意义的。在我看来,都在比较高的层面上进行。但是,比较高的层面,并不意味着优先地位,因为,无是批评还是“建设”,单就时评本身来说,一个最基本的功能是必须具备的,那就是判断:事物(这里是新闻事件)究竟是什么、怎么回事?它怎么来的?受什么影响?与什么发生关系?将向什么方向发展?这些,都需要对事物本身严肃的研究态度和认识态度,而不仅是批判的热情、愤慨或者“建设性”的功利心。
说不出这些,就既谈不上什么有价值的批评,更谈不到理性、建设性和影响力。
实际上,就时评的读者而言,往往首先需要的,不是你批评什么现象,或者建议如何解决问题,而是你如何判断这个大家感到困惑的现象和问题。时评的批判和“建设”,作为人的认识过程,都有着一步一步递进的规律。判断就是在前边的重要一步。
没有清晰的判断,没有被清晰地表达的判断,批评和建设都没有基础。一些时评版的编辑所不赞成的“一上来就批评”,我想就是因为作者没有“一上来就判断”,因此批评就可能无根。这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认识规律问题,在这里,是时评写作的规范问题。
在我看来,作为一个认识的过程,判断是难事,因为认识是难事。相较而言,我们一般说的表达,就是比较容易的事。我提出“时评是公民普遍表达的工具”,是在时评应该起到的一个最基本的功能的意义上谈论的。但表达什么内容,确实是有层次高低的:喜怒哀乐都是表达,它们更接近于感性自然的层面;而表达对事物的判断,则接近理性的层面。
事物越复杂,越难于判断,所需要的理性层次越高。判断的时候,没有愤怒,没有热情,只有一颗认识的心。
但是,判断的结果,当你通过艰苦的认识过程,通过扎实的分析和论证最终一语说破事物的本质的时候——如果这个事物是丑恶的话——那么,这一语就“严于斧钺”,就胜过无数愤怒的千言万言。对于事物来说,判断既成,批评自见。
我国最期最著名的新闻评论家邵飘萍1911年在时评中写道:“清帝退位而后祸中国者,必袁世凯其人矣。”“帝王思想误尽袁世凯一生”。可谓一语成谶。于时,辛亥革命刚刚爆发,南北军队正在和谈,离1916年袁世凯称帝还有5年呢!这不是批评,而是判断。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后,“一部分舆论颇有以将演西班牙内战惨剧为忧的”。恽逸群几天内连续发表评论《中国决不会作西班牙》等篇:“我们从各方面的情形来观察,可以负责任对国人说:中国决不会变成西班牙第二。”,这也需要一番审时度势的功夫。
2003年拉克战争期间,中国国内许多观察家对战争形势和各方力量的消长进行各种预测,我们搜狐的评论人黎明通过细密的观察和推理写出一篇《人民不会死战》——被网友推为最精采准确的一篇战评。
2003年某保险公司推出“酒后驾车险”,引起了轩然大波,大多数人都在这个险种的利弊及其合法性上争议。杨支柱撰文《“酒后驾车险”是一个骗局》,这样一个惊人的判断是基于他对保险制度的了解和细密分析。
美国研究媒体与民主问题的威斯敏斯特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基恩在《变动中的民主》第十三章《费城模式》写道: “判断,作为在充满复杂性的公共情境中选择行动路线的一种可以公开学习的能力,是最卓越的民主艺术。它依据的既不是演绎和归纳法则,也不是诱人上当的假想。
它避免想象力的驰骋,也摆脱实用理性的约束。”台湾《联合报》的主笔王民写的《新闻评论写作》认为“最重要的一课――判断”。他说:“在大多数情况之下,新闻评论所讨论的问题,不外是真或伪的问题,是或非的问题,善或恶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实际上就是一个判断问题。”
就表达而言,人人都会表达,只是表达的内容、效率不同;就批评而言,人人都会批评,只要对象看得一清二楚。但不是人人都有能力判断,因为现象往往是复杂的,它在最初呈现的时候性质未明、原因未明、关系未明、发展方向未明。
如果只讲表达、只讲批评,那么这意味着时评必然放弃许多读者关心的现象和问题。刘洪波先生曾作文《分析的失语》,其中说到,由于长期以来简单的思维模式,使中国评论界对于美国西海岸港口工人罢工几乎说不出什么话来。
因此这条新闻就几乎没有人评论。在我看来,这与其说是“分析的失语”,不如说是“判断的失语”。这种现象和话题,所在多见。对于普遍表达的目标而言,我们中国人的确还缺乏表达的能力和渠道。但对于活跃的时评家而言,不是表达能力不足,而是判断能力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