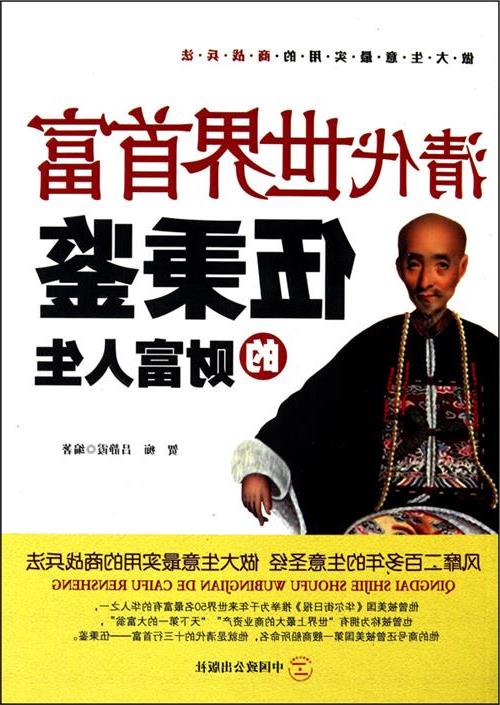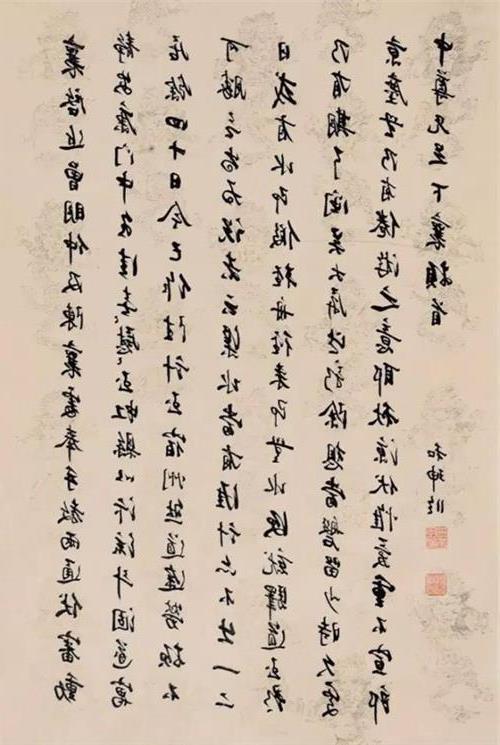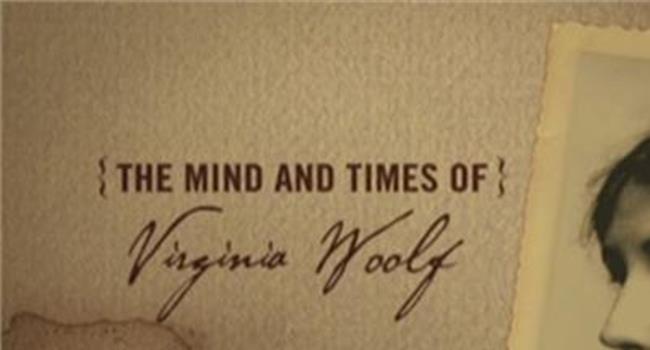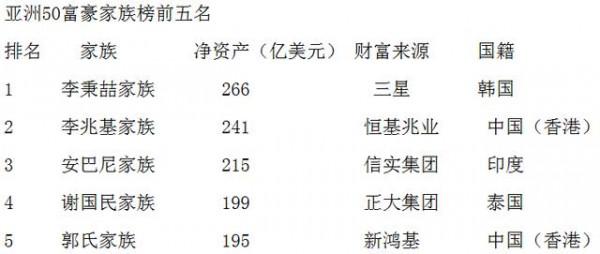伍秉鉴家族 曲路浚:从和珅伍秉鉴的财富积累说到国家安危问题
本文将清代前中期的和珅(1750—1799年)与伍秉鉴(1769—1843年)的财富积累同国家安危问题对接起来“说事”。也许有人会觉得这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一般的理解,财富积累不外乎原始积累、复利增值及财富力量三个基本途径。
但若没有“极有利于财富积累”的宏观大环境,和珅与伍秉鉴能够积累起如同天文数字般的富可敌国的财富是根本不可能的。自秦以后的二千余年来的政治架构,是以国家(皇权)为中心的政府——经济——社会三位一体化运行体制的“为民当家作主” 的传统国家——在国家与社会混沌的“一” 以及国家所有始终统治民间所有的公有制基础上的以国家(皇权)为中心的政府——经济——社会三位一体化运行体制。
这套政治架构的目的是明确的,就是为着:万岁!
万岁!万万岁!矛盾的是,数千年来,就国家能力而言,中国的国家又是一个大一統的强大而又弱小的矛盾自我同一体!?这背后肯定有一个隐秘的“经济基础”在支撑着。本文的目的是顺着和珅与伍秉鉴财富积累的“足迹”,试图找到这个“经济基础”。
另外,国家安危问题始终是历朝历代帝王将相的“雄心”,而将和珅与伍秉鉴的财富积累提升到国家安危问题进而提升到国家安全和国家的战略的高度来认识,对当代中国就具有高度的警示意义。
因为,当代中国的未来将通过贸易和金融实现全球战略,在地缘政治和国家军事安全的基础上又加进了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因素,这既需要消亡历史上的那个至今仍发挥潜在作用的隐秘的“经济基础”从而提升国家安全和国家战略能力,又需要终结中国商人在历史上有过的历史命运从而满怀实业报国的壮志引领企业走向世界!
2001年,《亚洲华尔街日报》做过一个统计评选:在过去一千年来,全球最富有的50人。其中目前仍然在世的,包括身家过360亿美元的汶莱苏丹陛下哈志哈山纳柏嘉,以及比尔-盖茨。 在入选的50人中,有6名是中国人,出现时间前后横跨800年,他们分别为成吉思汗、忽必烈、和绅、太监刘瑾、清商人伍秉鉴、宋子文。该报纸是这样描述这六位中国富豪内容如下:
成吉思汗职业:征服者;财富来源:战利品;资产:五百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入选原因:如果财富用占领的土地来衡量的话,成吉思汗将被列为从未有过的世界最富有的人,他的职业生涯于联合不和的蒙古部落,然后开始占领了将近五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包括现在的中国、伊朗、伊拉克、缅甸、越南和大部分的朝鲜、俄罗斯。
忽必烈职业:征服者和后嗣;财富来源:继承;资产:黄金和珠宝;入选原因:成吉思汗的孙子,他建立了中国的元朝,而且在国都建造了奢华的镀金宫廷。马可波罗对忽必烈避暑宫殿中散发的珠宝光辉啧啧称奇。
刘瑾职业:朝廷宦官;财富来源:贪污;资产:黄金和白银;入选原因:一个在明朝时传说最富有的宫廷宦官,他因为叛逆被处以极刑的时候,被发现有一千二百万盎司的黄金和二亿五千九百万盎司的白银。而当时明朝国库中只有三千万到七千万盎司的白银,(明武宗年间太监刘瑾被处死后,人们从他家中搜出黄金3360公斤、白银725万公斤。明末国库仅得200万公斤白银)。然而,刘瑾的财富报告可能被过分渲染,因为吏官想用这个故事来警示:当一个宦官掌权时能发生什么。
和珅职业:皇帝身边得力的人;财富来源:贪污、回扣;资产:黄金、白银、裘毛;入选原因:英俊、富于机智,有自信和令人难以置信的腐败。1772年和珅进入了乾隆的宫廷,当上了一个侍卫。但他很快变成了老皇帝的知己。他劝说日益年老的皇帝延长一次血腥的军事行动,当士兵正在挨饿的时候,他却把数量巨大本因分配给军队的军饷装入囊内。清朝的和绅被查出贪污白银达2.2亿两。
伍秉鉴职业:贸易人;财富来源:进口、出口、钱庄;资产:千万银元;入选原因:伍秉鉴的父亲是允许与外国人交易丝和瓷器的少数中国商人之一。1789年,伍秉鉴接管了他父亲的生意。他也是公认的慈善家。
宋子文职业:金融家、政府官员;财富来源:银行业、欺诈行为;资产:蓝筹股、现金;入选原因:宋子文被认为是上世纪40年代世界上最富有的男人。在1923年,他创立了中央银行,后来在1924年他被任命为财政大臣后成为国库。1942年,他被任命为外交部大臣,使用他在中国财政部的权利,把他大部分的个人财产投资外国的股票,包括持有世界通用汽车和多特公司的股票。
我们先不管上面的统计是否具有实际意义,就财富的主要来源而言,除去战争征服者的战利品的途径以外,官员与商人都可以通过原始积累、复利增值及财富力量这三个基本途径堆积起庞大的财富。这可能是中国历代以来的特色。本文中所指的和珅与伍秉鉴就分别代表着官员与商人。下面先说和珅财富积累途径。
和珅被抄家后的财产全部合计约十一亿六百万两,相当于清朝鼎兴时15年到20年的财政收入。一般认为,和珅有价可估的财产有2亿3000万两,未能估价者更数不胜数。按当时朝廷岁入7000万两计,和珅的财富到底有多少实在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天文数字。
对于和珅在前面的系列文章中已有不少笔墨,概括起来说,他的财富积累途径的第一个环节是使原始积累合法化,第二个环节是使原始积累通过地租、高利贷、商业资本三位一体化的“完美”的形式实现商品货币经济化。
按照大清的法律规定,在旗的满洲人是不允许涉及各种商业活动的。从法理上讲,和珅的财富积累活动都属于非法的以权谋私,但他通过“议罪银”等等财政制度同乾隆一起,建立了税上加税的由平民百姓支付账单的关系网,每一级官员都从下一级榨取自己所需要的的金钱,再向上一级“进贡”,这个关系网同官场的上下级关系网十分匹配,从而达到了原始积累包括“人情财”、职权贪污等合法化的目的。
和珅更大的财富来源应该是利用合法化的原始积累通过地租、高利贷、商业资本三位一体化的“完美”的形式实现商品货币经济化。
据记载和珅能够收取地租的土地有126600亩;他在北京城内开了12座当铺,其中有不少是行业中的佼佼者;他还开办了各种各样的商店,如石灰窑、酒店、杠房、柜箱铺、鞍毡铺、粮食店、瓷器铺、药铺、古玩铺、弓箭铺、印铺、帐局等等;此外他还从事物流产业,添置80辆大马车做长途返运;甚至刚刚起步的煤矿业,由于成本高,风险大,一般人根本不敢尝试,而他却投入巨资在门头沟和香山开办两处煤矿;即使是不动产,他也不会让其闲置,北京有房屋35处用于出租。
总之,和珅的投资,涵盖了商业、医药、物流、采矿、房地产、金融等绝大多数当时的行业,可以说,只要能够挣钱的地方,就能看到和珅的身影。
再来看伍秉鉴的财富积累途径。
伍秉鉴的财产有2000多万两的银子,这是什么概念?是清朝财政收入的30%左右。作为一个观照,当时美国最富有的人也只有700万两。在美国历史上,曾有一位留下八位数遗产的“千万富翁”,他就是1848年去世的当年美国首富约翰·雅各布·阿斯特。他死的时候,遗产估计有2000-3000万美元。而阿斯特混成美国首富,靠的就是和当时的大清朝做买卖。他其中的一个重要贸易伙伴,就是当时富可敌国的伍秉鉴。同和珅非法的以权谋私但却披着合法化外衣完成的原始积累不同,伍秉鉴靠“继承”完成“原始积累”。这里,先要讲清伍秉鉴“继承”了一份什么样的“原始积累”。
1686(康熙二十五年)年春节后,广东巡抚李士祯在广州颁布了一项公告,宣布凡是“身家殷实”之人,只要每年交些钱,就可作为“官商”包揽对外贸易。于是,广东地方政府于1686年招募了13家较有实力的行商,指定他们与洋船上的外商做生意并代海关征缴关税。
从此,近代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广州十三行”诞生了。后来,所谓的“十三行”,实际只是一个统称,并非是13家,多时可达几十家,少时则只有4家。但由于它享有垄断清朝海上对外贸易的特权,凡是外商购买茶叶、丝绸等国货,或销售洋货进入内地,都必须经过这一特殊的组织,故“广东十三行”逐渐成为与两淮的盐商、山西的晋商并立的行商集团。
可以说,“十三行”是清王朝的“外贸特区”。
到1757 年,乾隆下令、“一口通商”,四大海关仅留广东一处,“十三行”更是达到鼎盛时期,对中国后来的经济发展甚至世界贸易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几乎所有亚洲、欧洲、美洲的主要国家和地区都与“十三行”发生过直接的贸易关系,大量的茶叶、丝绸、陶瓷等商品从广州运往世界各地。
此后的100年间,广东“十三行”向清朝政府提供了40%的关税收入。相对来说,伍秉鉴的父亲伍国莹只能算是“十三行”的后来居上者。据考证,1738年以前,“家贫好义”的福建人潘振承来到广东,先在一家洋行中打工,后创立同文行。
从这个家族的第一位行商潘振承(名启,字逊贤,号文岩)开设同文行开始,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潘家都在广州的对外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潘氏家族的主要人物在广州一口通商80余年的时间里担任洋行首领达39年之久,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其行号能绵延不绝,是“十三行”中绝无仅有的。 潘家到底富到什么程度呢?咸丰十年(1860年),一位叫亨特的美国人在一本叫《旧中国杂志》的书中写道:我最近参观了广州一位叫潘启的中国商人的房产,他每年在这处房产上花费达300万法郎……这一处房产比一个国王的领地还大,据说他拥有的财富超过1亿法郎,这已经比当时欧洲很多国家的国王还要富有……他有50个妻子和80个童仆,还不算30多名花匠和杂役等……从这位外国人的记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潘家的极奢程度。
直到1783年伍秉鉴的父亲伍国莹创立元顺行(后更名怡和行)以前,一直是潘家的账房先生(转引自历史网,《平安商人之伍国莹》,12年9月26日)。
怡和行为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伍国莹开设之洋行。伍国莹之祖先为泉州安海人,在武夷山种茶为业。十世朝凤由闽入粤,籍隶南海。
国莹死于嘉庆五年(1800年),其子秉鉴继承父业,因其乳名为亚浩,故以“浩官”为商名。嘉庆十二年(1807年)怡和行跃居行商第二位,十八年(1813年)清政府在行商中设立总商,伍秉鉴居总商之首。
在前文中笔者已讲到,在1600-1813年的200多年里,东印度公司享有印度贸易的垄断权。这个权力在1813年被取消后,东印度公司仍然继续拥有印度和中国之间贸易垄断权,直到1834年被取消。因此,东印度公司和广州行商之间的贸易,其实就是两个垄断集团之间的贸易。
“十三行”就是官商合作的代名词。经商和做生意有着一定的区别。做生意怎样精明,十三档算盘,盘进盘出,丝毫不漏,也许算不得什么!但如果生意人凭借自己机灵的头脑、长远的眼光、多样的手段,把生意盘活、做大了,就上升到经商者的行列了。
经商是一门智能性很强的活动,商道在其中起着尤其重要的作用。伍国莹并没有仅仅将自己定位在账房先生的职位上,满足于简单的算算账,而是广泛涉猎。
那时商户的账房先生要比现在的公司会计的权力大很多,不局限于记账、算账,还可以参与资产的管理(与现在的管理会计差不多),还可以进行贸易投资。更准确地说,伍秉鉴的父亲伍国莹,在“十三行”——官商合作这个“极有利于财富积累”的宏观大环境中完成了“原始积累”。 伍秉鉴“继承”这一份“原始积累”后,继续行走在“十三行”——官商合作这条道路上。
当年“十三行”的繁荣可用“金山珠海,堆满银钱”来形容,据记载,1822 年十三行处所发生的一场大火,大火中熔化的洋银满街流淌,竟流出了一二里地,一场大火就烧毁了商馆价值4000 万两白银的财物,可以想象十三行当年的华贵景象。
伍家经营的“怡和行”与英商和美商每年贸易额达数百万两白银。伍秉鉴不仅在国内拥有巨额的资产,还是东印度公司的“银行家”和最大债权人,而且在美国投资铁路、证券交易和保险业务等,他可谓是19 世纪的世界首富了。
“怡和行”在中外商界都是个响亮的名号,1832 年英国人威廉. 渣甸和詹姆士. 马地臣借用伍家“怡和行”老字号,创办了“怡和洋行”,鸦片战争后“怡和洋行”总部迁至香港,成为远东最大财阀,对香港早期的发展举足轻重,有“未有香港,先有怡和”之称,至今怡和洋行在香港仍然维持相当的业务,包括:置地、牛奶公司、文华东方酒店 、香港空运货站、 香港货柜码头、 惠康 超市、 7-11 、 宜家家居 、 Pizza Hut 等等,员工总数超过十万。
“十三行”的大部分生意是与另一垄断者做的,即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它是英帝国的全权贸易代表,双方以垄断对垄断倒也“门当户对”。但在1834年,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垄断权被取消,中国“一口通商”的方式无法满足日渐增长的贸易活动,与英国自由商人的贸易摩擦日渐升级,“十三行”逐渐变为19世纪中西关系危机的焦点,鸦片战争一触即发,“十三行”也在战火中走向消亡。
1856 年,繁盛一时的“十三行”处所在英法联军的炮火中付之一炬,英国商人也将经营中心转至香港,“十三行”从此退出历史舞台。咸丰帝六年(1856),十三行毁于广州西关大火(转引自新浪博客,韦博,《清末首富伍秉鉴的考究》,11年10月19日)。因这篇文章的主题,伍秉鉴的商道用不着多说了。
在本文中“关注” 和珅与伍秉鉴,并不是因为一个是天下第一贪,一个是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成功的商人,也不是他们都是在过去一千年来全球最富有的50人之一,而是因为他们两人都从不同的途径积累起如同天文数字般的富可敌国的财富。
在2014年世界500强排行榜上,排在前三位的公司依次为:沃尔玛、壳牌石油、中石化。零售巨头沃尔玛以4763亿美元的收入力压群雄,而壳牌石油收入为4596亿美元,来自中国的中石化以4572亿美元的收入,首次打入前三甲阵营。
利润,沃尔玛和壳牌石油都超过160亿美元,而中石化为89亿美元。从绝对的数量规模看,当代的沃尔玛、壳牌石油、中石化同和珅与伍秉鉴的关系是“牛”与“毛”的比较。2013年财政收入为129143亿元,比上年增加11889亿元,增长10.
1%(人民网-财经频道,2014年01月23日)。从财富积累占国家财政收入的相对的数量规模看,不要说和珅(被抄家后的财产全部合计约十一亿六百万两,相当于清朝鼎兴时15年到20年的财政收入),光说伍秉鉴的财产占清朝财政收入的30%左右就是一个庞大的如同天文数字般的富可敌国的财富。
当代的沃尔玛、壳牌石油、中石化同和珅与伍秉鉴的关系又成了倒过来的“牛”与“毛”的比较。我们能从这两个绝对与相对的“牛”与“毛”的比较的“存在”引出什么样的现实性的“存在”的“潜在”呢?
这里,需要引入一点哲学上的话题。我们认为从潜在到存在的逻辑,不是神秘的从无到有,或无中生有,而是从可能性的存在到现实性的存在。或者说存在是现实性的潜在,潜在是可能性的存在。更进一步地说,存在是一个有组织的存在,是矛盾的自我同一,是无限与有限以及绝对与相对的矛盾的自我同一;潜在是存在的种子,是世界上万事物存在的本源,是“宇宙村落”的奠基石。
显然,存在不是哲学的出发点,有必要从潜在——存在——表现的完整的逻辑中反思“存在决定意识”问题。
因为,存在至多只是有限的确定性,潜在才是无限的非确定性。如果将含有巨大潜能的空间、时间这一存在的基本形式,以及信息以存在和能量为载体并且是存在和能量的时空序(有序和无序)也整合进来,那么,存在就是一个全息元(一滴水的信息包含着大海的信息,一个枝条包含一根大树的信息),其显态和潜在信息之和是相等的,且具有同源、同构、同质性。
由于存在的空间、时间、运动、信息、信息等等形式的多样性,使世界上的存在就具有同质异量与异质异量的矛盾自我同一性。回过头来,存在又成为潜在的本质,潜在的意义却在价值。
沿着上面的哲学思维方式,只有先找到和珅与伍秉鉴所处的时代这个存在的潜在——东方中国历史的潜在,才能找到他们的含有巨大潜能的空间、时间这一财富积累——存在的基本形式。那么,东方中国历史的潜在究竟是什么呢?回答问题之前先说明寻找东方中国历史的潜在的必要性和现实性。
在1980年代前期,有一个流行的说法是,在近代以前,中国社会的几千年历史是在自然经济和人的依赖关系(群体社会)中周期循环,并没有发生质的飞跃,没有发生大的社会转型,没有从自然经济转变为商品经济,没有从人的依赖关系过渡到物的依赖关系(物化社会)(刘佑成,《社会发展三形态》,第111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2月第一版)。
那时的人们大多从从马列本本上那个“时空差”中,企求“理论联系中国的实际”而得出结论,还少有人从同国际接轨的“现代化” 的“时空差”中,企求同西方学者对接对话的 “理论联系中国的实际”而得出结论。
因此,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曰》中的法国农民“马铃薯社会”论影响了那时的学人。
在马克思生前所看到的19世纪的法国农民,仍然像“一个口袋里马铃薯”—— 每个社区都是一个社会整体,所有社区属于同一类别,但每个社区又都有自己的独特性。通俗地说,“马铃薯社会” 由一个个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社会经济单位组成。
中世纪欧洲的庄园组织是典型的“马铃薯社会”。 这种庄园组织,支配着居民的全部生活,社会惯例具有无上的权威,它决定着每个人的权利和义务。在这样的社会中,商品经济不发达,缺乏市场机制,整个社会是许多相同的“马铃薯” 组成的群体。
今天看来,用“马铃薯社会”套用传统中国有点风马牛不相及。真实的中国的“农户经济社会” 与西方“马铃薯社会”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如,直到18世纪工业革命前,中国的“农户经济社会” 的商品经济有着悠久的传统且比西方“马铃薯社会” 发达,是一个农商并举而非重农抑商的“传统”。
个体经济(农户经济)是几千年农业社会的传统中国的自组织与选择的结果。是几千年农业社会的传统中国发达的自组织基础。
过去,老是说“小农经济”“ 汪洋大海” 是近代中国落后根源之一,因而也就看不到具有发达的自组织基础所蕴藏的自组织的创新意义。在前近代的传统中国二千余年的以国家(皇权)为中心的政府——经济——社会三位一体化——专制一尊中央集权制运行体制就是以发达的个体经济(农户经济)自组织为基础的。
人们似乎忘记早先在西欧以反庄园封建为目的,那时的个人主义的理想就是以个人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在农村也不过是东方中国式的“农户经济社会”!?
1980年代,大家谈的都是“人”, 关键词是“个人”。 大家直接把改革开放看成个人抬头、人性复归的契机。“在那里,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笫1卷,第273页),这一话语被反反复复引用着。
1990年代,主题词变为“市场”、 “ 阶层”、“ 市民社会” 、“公民社会”、“民间”等。这时的人们已大多不再从马列本本上那个“时空差”中,企求“理论联系中国的实际”而得出结论,而从同国际接轨的“现代化” 的“时空差”中,企求同西方学者对接对话的 “理论联系中国的实际”而得出结论了。
人们谈论的话题转换为“社会” 既不是一个“鲁宾逊们”( 鲁宾逊是笛福写的《鲁滨逊漂流记》的主人公)的总和,也不是一个“市民社会”(黑格尔将市民社会看作是私人利益的体系,认为个人是市民活动的基础,也重视在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的作用,认为市民社会依附于国家。
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的思想,把市民社会看做是市场经济中人与人的物质交往关系和由这种交往关系所构成的社会生活领域),而是一个“利维坦” (英国政治家、思想家、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1588-1679,代表作品之一就是《利维坦》)。
新世纪最近十年,又转移到“国家”这一话题上。最后的结果是,将1980年代集权与放权这一晓晓板转换为国家与市场这一晓晓板。避开左中右,形成了国家中心论、市场(社会)中心论以及介乎两者之间的市场(社会)中的国家论三大流派。
评价每一流派并不是本文的主题,需要指出的是,每一流派中涉及到的这主义那主义都是引进西方的主义,用一种西方的主义“理论联系中国的实际”而得出结论反对另一方而针对“中国的实际”能堵塞真实中国的漏洞吗!?只有立足东方中国历史可能性的存在——潜在这一历史基础,才能进入东方中国现实性的潜在——存在的历史大门。因此,寻找东方中国历史的潜在也就有了必要性和现实性。
关于东方中国历史的潜在问题在笔者前面的系列文章中多多少少已论及,在这里只能简要地概述之。笔者曾反反复复说着以下话语:自秦以后的二千余年来的政治架构,是以国家(皇权)为中心的政府——经济——社会三位一体化运行体制的“为民当家作主” 的传统国家——在国家与社会混沌的“一” 以及国家所有始终统治民间所有的公有制基础上的以国家(皇权)为中心的政府——经济——社会三位一体化运行体制;传统中国二千余年的以国家(皇权)为中心的政府——经济——社会三位一体化——专制一尊中央集权制运行体制就是以发达的个体经济(农户经济)自组织为基础的;数千年来,就国家能力而言,中国的国家又是一个大一統的强大而又弱小的矛盾自我同一体!
?借用前面的哲学术语,一个活着人的当代与逝去的历史关系既具有同源、同构、同质性,又具有同质异量与异质异量的矛盾自我同一性。和珅与伍秉鉴他们的含有巨大潜能的空间、时间这一财富积累——存在的基本形式,是一个历史上的实实在在:一个活着的个人既可以通过国家权力场域也可以通过市场积累起如同天文数字般的富可敌国的财富。
如果再对和珅与伍秉鉴的前后作点延伸(春秋末期的陶朱、战国时期的吕不韦、秦朝初期的寡妇清、西汉文帝宠臣邓通、西汉哀帝宠臣董贤、西晋著名富翁石崇、北魏时河间人王元琛、元末明初江南巨富沈万三、清末红顶商人胡雪岩),同样可以证明这个历史上的实实在在。
就最深层的“经济基础” 而言,除去国家财政以外的财富在国家权力场域与市场双向流动,且国家权力场域之手与市场之手从来都在比手腕之力——权力本身成了货币,国家权力场域之手大于市场之手成了历史常规。
正因为如此,在一个农商并举的传统中国重农抑商与官商合作都是响当当的两面鼓。
也正因为如此,三千多年来,中国商 人的命运起起伏伏既有司马迁《货殖列传》里的洋洋大观,也有近代商人被抄家杀头的悲惨命运(中国商人,发迹于三千年多前的商朝,兴盛于西汉初期,鼎盛于两宋。
自春秋,齐相管仲盐铁专营,士农工商四民分业。两千多年来,商鞅变法,商人为国之五害之一;汉武帝桑弘羊变法,强收商人之利, “垄断天下之利源, 以便其治” ;朱元璋在位,尽徙江南商户,杀明首富沈万三以立威。
两千年来,商人作为四 民之末,上为统治者日夜提防,下为世人所不耻。每每在重大历史关头, 商人总是屈从强权,不做应有的反抗。从汉景帝七王之乱,到蒋介石南京上台,商人一次又一次的错失改变自己 命运的时机,一次又一次被当权者玩弄于股掌之上君不见, “莫作商人妇,金钗当卜钱”“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 ,商人在世人眼里,尽是这般模样)。
更进一步说,中国商品货币经济以货币的价值属性、价格属性通过权力赋予为“经济基础”。也就是说“经济基础”始终只靠以国家(皇权)为中心的皇权本位,而始终没有搞“金本位”或“银本位”。所以商人只有一条路:工商食官,与权力结合。不然的话,所有的货币都是不安全的。
按照刘刚,李冬君的《中国近代的财与兵》(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10月)一书的观点,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出现过本币制,虽有金银,却始终不搞本币,所以每当经济发展到一个阶段,反而会出现种种危机,越繁荣,距大崩溃越近。宋朝铜钱遍天下,那时宋钱有点像今天的美元,在北非一带就发掘出了宋钱。宋代有很多货币理论,非常先进,比如沈括,比如永嘉学派的叶适,可南宋还是崩溃了。明朝也一样,明朝时中国号称是一个“白银世界”,世界各地的白银都流到中国来了。可银子越来越多时,出现了金融危机,而且就在你经济发展最高峰时,国家开始衰落,最后还是没有闯过险滩。财富越多政权越危险,是他们两人的观点。笔者在这里补充一点,就是,当一个活着的人通过国家权力场域或通过工商食官与权力结合的市场积累起如同天文数字般的富可敌国的财富时,这个王朝离灭顶之灾也就为期不远了!?
笔者在前面的系列文章中不止一次地写道,18世纪后期相对富足的几十年间所孕育的1790年代乾隆传给嘉庆的不是一个“盛世”,而是一个危机四伏的坏得不能再坏的清王朝。但从1790年代到1820年代,中国一直是全球“龙头老大” 、“全球第一”。几千年来,具有私人契约关系的土地与劳动力交换的活动,在中国农村一直十分活跃,农民也亨有流动性的选择职业(七匠八匠)的自由;平静的简简单单的乡村也蕴藏着“生机”—— 地租、高利贷、商业资本这些“现代” 要素;但从乾隆时期开始,地租、高利贷、商业资本三位一体化地剥夺农民取得了“完美”的形式。由地方政府内部操纵的税收借贷生意,由18世纪后期相对富足的几十年间在农村表层之下积聚起来,到了19世纪初却成了暴露无遗的社会罪恶。和珅活着的时期正吻合着清朝从强大走向弱小的转折时区。而伍秉鉴的生意似乎并没有受到大清国由盛转衰趋势的影响,而是与大清国的这种衰退之势恰恰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