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批遇罗克 周恩来两次挨批真相
1973年是周恩来命运多舛的一年。1月13日,因膀胱癌恶化,排出大量鲜红的血尿。3月10日,他住进玉泉山施行第一次电灼术治疗。令人欣慰的是肿瘤甚小,术后几天尿色就清澈透明了。总理很高兴,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设“烤鸭宴”答谢医生护士,他以为自己已经康复了。
不料,7月和11月,两次“批周”,使周的病情急剧恶化。第一次“批周”后,再次发现全程血尿,膀胱癌复发,大夫的意见是立即住院。但接踵而至的第二次“批周”会,使大夫们只能望病兴叹。二次“批周”后,肿瘤迅速增长,每天的出血量由几十毫升到了二百多毫升,周恩来终于告别了西花厅,住进305医院,直到去世。
两次“批周”,章含之都是近距离的亲历者。别说是大红门内的历史,就是在共和国的历史画卷上,这两次“批周”都可算得上是浓重的一笔。我们多么希望在章的书中能看到这段历史的真相,遗憾的是,惊心动魄的政治风云被凄美、哀艳的浪漫故事掩映得面目全非。
第一次“批周”源于外交部《新情况》上的一篇文章。周恩来第一时间看到了该文,十分赞赏。可当有人把文章拿给毛泽东看时,毛却勃然大怒。7月4日,周去玉泉山治疗,毛召见王洪文和张春桥,说:“你们两位是负责(十大)政治报告和党章的,今天我请你们来谈几件事。”于是海阔天空地讲了一席话。其要点是——
都说此文不错,我一看呢,也许我是错的,你们贵部是正确的吧!不过与中央历来的,至少几年来的意见不相联系。
你们年纪还不大,最好学点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爷们的当,受他们的骗,以至于上他们的贼船。(原话是“上乔老爷、姬老爷的贼船”。)
我这几年名声不好,世界上唯一的马克思一盏明灯是在欧洲,那个地方放个屁也是香的……“明灯”是用我的名义写的,我就没看。凡是这类屁文件我照例不看。总理的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
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当晚,张春桥通知周恩来,要求召开政治局会议,传达毛的讲话。周遵命主持会议,传达了对自己的批判。其实,早在7月2日夜,王海容已经把谈话内容通知了周恩来。而章含之知道此事比周恩来又早一天。那是7月1日下午,章在政协礼堂开完章士钊治丧会后:
一辆汽车疾驶过来,我当时的那位“通天”朋友从车上下来,急匆匆找到我,说来给我“打招呼”。她说在我离开北京的一周内(章要去香港迎父亲骨灰)外交部可能要出大事。右倾错误是肯定的,乔冠华也肯定要涉及,要受批判。他说要我有思想准备,究竟是站在革命路线一边,还是死心塌地跟乔老爷走。(《十年风雨情》)
和周恩来不同,王海容是把章当“自己人”来打招呼的。她希望章站在毛的一边,和周、乔他们划清界限。但那时,章和乔已然打得火热,用章对乔的话说:“如果你是贼船,我早已上了这只船,下不来了。”因此,在那次“批周”的过程中,“冠华的处境一直十分困难,而我却必须周旋于两种势力之间”(同上)。
“周旋”一词用得十分巧妙,仿佛章是在批与被批之间。而行文中,章更巧妙地把自己划进了被批的一方。事情果真如此?非也。章提到“批周”时上边传下来的话,说“外交部是独立王国”,“外交部要掺沙子”。自称“是毛主席亲自点名调进部里的”章含之,是否也是掺进来的沙子?此事怕是路人皆知。只是不晓得,这一次是沙子被带上了贼船,还是贼船靠沙子上了岸。章虽不便明说,细心人仍不难看出端倪。
“批周”后周恩来没有参加十大政治报告的起草,而“冠华被指定参与起草十大报告的外交政策部分”,那一部分恰恰是“批周”的主要内容,即“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世界形势。“开完十大,冠华当选为中央委员”,按章含之的说法,这场斗争“莫名其妙地逐渐消失了”(同上)。
然而,“批周”却并未消失。第二次“批周”,源于周恩来与基辛格的会谈。11月17日,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及外交部有关人士谈话,对周恩来在会谈中的“右倾错误”严加申斥:“有人要借我们一把伞,我们就是不要这把伞,这是一把核保护伞。
”“当着你们的面讲,政治局开会,你们可以来,在后面摆一排椅子,谁要搞修正主义,那就要批呢!”毛亲自拟定列席政治局会议的名单,即四老:姬鹏飞、乔冠华、黄镇、仲曦东;四小:王海容、唐闻生、章含之、罗旭。章由此成了“批周”会上的“小人物”之一。
从11月21日到12月5日,政治局天天开会“批周”。会议是怎样的惊天动地,只有参加者才会知道。但章含之却说:“作为当时参加会议者之一,我自然明白会议的全过程。但是我宁愿把这段历史留给局外人去分析研究,让后人得出符合历史真实的结论。
”(《昨日旧事残梦》)被与会高层人士慨叹为“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的会议记录,据说已经付之一炬了,而参加会议的人却宁肯让局外人去研究,后人又怎能“得出符合历史真实的结论”呢!
作为局外人,我们只能从相关人员的回忆中,感受到会议的紧张、激烈。
一次,警卫战士张树迎进会场送药,见“总理单独坐在大厅的一个角上,前面搁个茶几,一人孤零零地坐在一张单人沙发中。其他人围成一个圈,完全是一个批斗的架势”(《我的伯父周恩来》)。一位服务员进去送水,目睹现场,“她惊呆了,把几杯水倒翻在地,哭着跑了出来”(《周恩来卫士回忆录》)。
每天散会后,“(伯伯)总是面色灰白,紧抿双唇,眼神悲凉,步履踉跄,有好多次都是张树迎和高振普迎过去,赶紧用双手插进他的腋下,几用尽全力架着他挪步上电梯”(《我的伯父周恩来》)。
“往日谁见了周恩来都会主动热情地打招呼,现在……即使迎面相遇也要表现冷淡,大概为了表示划清界限吧!”(《周恩来的最后十年》)
在会场外,周的警卫、保健大夫也备受冷落,“多数领导人的随员,见到我们或低头而过,或扭头避免彼此目光接触……即使擦肩而过,也不理睬我们”(同上)。
随员们甚至做好了蹲大狱的准备:“我们的直感是……像要动手杀牛了。” (《周恩来卫士回忆录》)
别看是政治局会议,左右形势的还是“小人物”。就是调门最高的江青,也免不了不得要领。如她说周是霍查,主张两个拳头打人,显然是把上次“明灯”的谈话挪了过来,急得一位小人物悄悄拉了她一把,说“把问题弄反了,搞颠倒了”。
小人物比政治局委员还明白,盖是身份使然,王海容、唐闻生是毛泽东的联络员,口衔天条,自然了得。张颖听一位与会者说,周恩来癌症在身,右手发颤,想让一位小人物帮忙记一下。那位小姐杏眼圆睁,怒斥道:“是批你还是批我?自己记!”(《外交风云亲历记》)
忝列“小人物”的章含之,自然比不上联络员风光,充其量不过是“偏师借重黄公略”罢了。但章和乔的批判,恐怕也可圈可点。章曾这样剖析:“我为了自己的生存与‘前程’,随着那汹涌而至的浊浪,说了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伤害过好人。
尤其在周总理蒙受屈辱时,我们并未能为他做一点事减轻他的压力。”此话倒有几分当真。章和乔确实是为了前程而批周的,但当时究竟是真心还是违心,现在已无从查考了。至于做一点减轻压力的事,那原本不难,譬如叶帅,散会后会找到张佐良(总理保健医生)用力握一下手;纪登奎则会悄悄地问张一句:“怎么样?还好吧?”一握手,一句话,暖遍了周家人的心。章和乔,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乔冠华是总理从1940年代一手提携起来的干部,二人关系情同父子。到关键时刻,也是真刀真枪啊!倒是江青的护士小赵,总理不过是解了她一次难,“批周”时她竟在大会堂对着张佐良说:“张大夫,你还不知道呢,他们白天睡觉,晚上来开会整总理,……他们到底在搞什么名堂!”张要她轻点声,她说:“张大夫,你不用害怕,我说话,我负责,我说的全是真话,我不怕坐牢!”相形之下,乔的表现未免令人寒心。
据章说,1975年一次会见外宾后,乔曾向总理痛切剖析1973年自己的懦弱,并得到了总理的谅解。但就在那次会见后,工作人员要求与总理合影,章、乔均在合影人群中,照完相,总理忽然大声说:“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在我脸上打叉。”有学者认为,这是在点乔。我也想,周大概不会去说那些工作人员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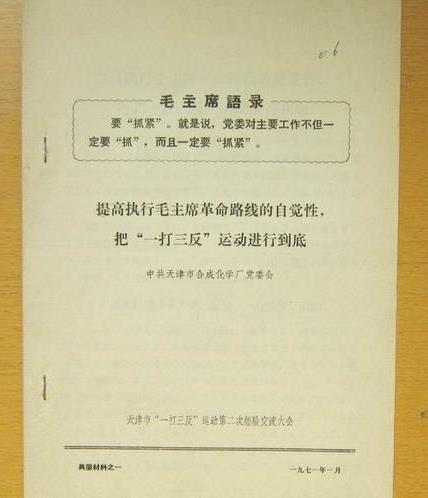


![>[转载]戳穿张志新 林昭 遇罗克们的谎言](https://pic.bilezu.com/upload/2/11/211fca2c58b022061c719dc2f45a7ad3_thumb.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