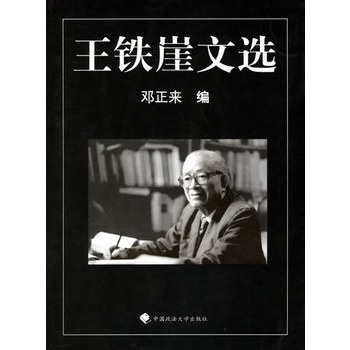王铁崖的学生 邓正来:中国与世界的王铁崖先生
然而,未料想,那一次见面竟成了我与先生的诀别(本书彩插所刊我与王铁崖先生和王彩师母的合影便是那日下午在先生家中拍下的最后一张合影),而先生的那些教诲也竟成了先生对我的遗言,因为先生于2003年元月12日因病无治而撒手人寰,离开了我们。
先生是中国学术界的泰斗级人物,公共性的悼念活动自然甚重甚隆。然而,我与先生的深厚友情却基本上是私性的和学术的,所以我决定还是按照先生生前喜欢与我交往的那种私性的学术方式来哀悼和纪念先生。
我相信,我悼念先生的最适当的方式便是将《王铁崖文选》重新编辑后再行出版,因为这是先生在生前对我的遗嘱中反复提及的一件事情──只是我为先生未能亲眼见到这部新版《王铁崖文选》而深感遗憾。为此,我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一方面认真校正了初版《王铁崖文选》印刷工作中留下的各种错误,另一方面又重新编辑了《王铁崖文选》第七部分有关1943年中英中美新约的研究文字并且收录其间──这部分文字因当时的种种原因而未能刊出。
这次编辑先生的文稿,实际上使我又一次聆听到了先生的学术教诲,并又一次与先生进行了倾心交谈。
铁崖先生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先生不仅是中国国际法学会的会长和中国法学会的顾问,而且也在国际上取得了崇高的荣誉。先生是国际法大师劳特派特的高足、被美国著名海洋法学术刊物《海洋发展与国际法》聘为编辑委员会委员、被荷兰《亚洲国际法年刊》聘为顾问委员会委员。
1981年,先生在法国迪戎召开的国际法研究院会议上被选为副院士,并于1987年当选为院士。国际法研究院是1873年创建的国际上最重要且最具影响的国际法学术团体,院士和副院士的总数限于132名,而先生则是第一位当选院士的中国国际法学者──后来经先生的推荐,陈体强、李浩培和倪征懊先生也相继当选为院士。
同年,先生又被加拿大著名国际法学者麦克唐纳教授推荐为加拿大国际法理事会咨询理事。
1988年,先生被在美国洛杉矶的“建立国际刑事法庭基金会”授予“著名国际法学者”名誉奖状。1989年,作为著名国际法学者,先生被选入含括国际上著名的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和文艺家的世界著名的科学院的院士,他也是中国大陆学者中的惟一院士。
先生在国际法研究方面的贡献蜚声于国内外,而其间在先生80寿辰之时由先生以前的学生撰写论文并以《和平、正义与法》为题的纪念论文集的出版便是这方面的明证,而由加拿大著名国际法学家麦克唐纳教授任主编、由26个国家和地区的著名学者撰文56篇的《王铁崖纪念文集》〖WTBX〗(Essays in Honour of Wang Tieya)〖WTBZ〗的出版更是最佳的明证,因为在我看来,这乃是当代中国学者中惟一一位学者在国际上获得的由学术界同行给出的如此之高的真正的学术承认。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隐含于上述国内国际荣誉背后的却是先生贯穿于其学术研究之中并在某种意义上构成其学术贡献之基础的“追究”精神,这种精神便是先生反复与我谈到的他所坚定信奉的治学原则:“学无止境”;更为重要的乃是我所认为的先生在建构中国国际法学的过程中所凸显出来的他对国际秩序的深邃洞见,而其间处于支配地位的便是他立基于中国立场和世界立场的国际法观。
我以为,先生的国际法观基本上可以从这部《王铁崖文选》中反映出来。
尽管《王铁崖文选》这部学术文集由七个章节构成,但是先生的国际法观却主要是由下述三个部分构成的:第一是有关国际法与中国的研究;先生的这部分文字主要展现了他立基于废除不平等条约和捍卫主权的中国立场的中国国际法学观。
第二是有关国际法研究的文字;先生的这部分文字主要反映了他在国际法研究中的世界关怀,而其间最为重要的则是他对国际秩序的深刻洞见,以及他立基于此种洞见而对当代世界格局中不平等的国际实践的严肃批判。
第三是有关中国国际法学建构的讨论;在先生的这组文字中,主要呈现的是他经由对如何进行国际法研究这个问题的思考而建构中国国际法学术传统的努力。当然,先生这三个部分的讨论或研究题域并不是互不关联的,而毋宁是先生整体的国际法观中的不同侧重部分;此处需要再加以强调的乃是前述所论的使这些不同部分勾连成一个整体并贯穿于其间的王先生关于国际法的中国观和世界观。
近代国际法在发生学上的结构性基础,乃是主权性的民族国家及其互动间所必然发生的各种关系。然而国际法一旦生成,它便在某种意义上与其自身的结构性基础处于一种辩证的张力之中,最为重要的一面便是它对国际秩序的规范,套用先生的话说,“目前以及可预见的国际关系的现实是国家在国际关系中处于主要地位,并同时需要遵守一些法律原则、规则和制度。
因此,国际法之所以为国际法,其效力根据在法律上在于国家的意志的合致,而在社会上在于国家在国际社会中交往的必要”。
正是在这种视角下,国际法亦就在理论上和实践中成了透过主要调整国家间行动而型构某种国际秩序的一套国家行为的判准。然而,国际法并不是应着主权性的民族国家的出现而自然生成的,而是参与国际关系的行动者(此处主要指主权国家)依据其采取行动的知识体系或世界图景而建构的,并在国际关系的活动中予以实践的。
当然,国际法在国际关系的实践中,实际上也在一定程度上转换成了各主权国家采取行动赖以为基础的知识体系或世界图景的一部分。
正是此一分析逻辑的展开,我们可以说国际法及其调整进而型构的国际秩序亦就会因不同的知识体系或世界图景在国际关系格局中所处的不同位置而表现为不同的形态和具有不同的性质;换言之,亦是依据这种我所谓的“秩序-行动-知识”的分析框架,我们可以说,国际法既是世界的,也是各主权国家的,进而当然是中国的。
作为国际关系中的主权国家,中国当然是调整进而型构其置身于其间的国际关系的国际法的建构者之一,而不是被动的无所作为的受调整者。然而欲做出建构者的努力,就至少要求对其行动所赖以为基础的知识体系或世界图景(包括内化入其间的国际法知识)进行探究。
与此同时,一如上述,国际秩序乃是在不同主权国家的互动中形成的,所以这还要求国际法的建构者对不同国家的互动行动所赖以为基础的不同知识体系或不同世界图景加以研究。仅就此一向度而言,这是中国国际法学的使命,从而也是中国国际法学研究者的使命;用先生的话说,“就建立中国自己的国际法学说本身来讲,更需要的还是中国国际法学者自身的深入研究和思考”(王铁崖《国际法引论》“自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在我看来,先生长达72年的国际法研究生涯,正是中国国际法学研究者所应承担的上述使命的展现,因为先生的国际法研究不仅伴随着中国国际法实践和中国国际法学的发展而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先生的国际法研究及其相关的活动还在其间推动甚至引导着中国国际法学的发展。
正如王先生的老学生、原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端木正教授在其为《王铁崖文选》所做序文中指出的,王铁崖先生“在我国国际法学界的巨大影响和崇高威望不是偶然的,而是实至名归,当之无愧的”。
从1933年在《清华周刊》发表“最惠国条款的解释”一文起,直到1948年解放前夕,先生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有关条约理论中的诸问题上。先生在解放前出版的两本学术专著都是有关条约法的专著:一本是《新约研究》(1943年版),另一本是《战争与条约》(1944年版)。
显而易见,先生这一阶段研究重点的选择,并不是他个人的偏好所致,而是他对当时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性质的深刻认识的反映。众所周知,中国自五四运动以降的30年间,中国国际法学的发展在此一阶段就是以研究条约为重点的,这是因为中国在这一期间的对外关系中,最重要的国际法问题就是废除不平等条约以及因此而牵涉到的有关法律问题。
先生在这个方面所做的相关研究不仅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研究方向,更是凸显了隐含于这种选择背后的他关于国际法研究的中国立场和世界立场。
先生立基于国际法的中国立场,对不平等的条约以及由这种不平等条约型构成的不平等的国际关系进行了严肃而犀利的批判,并通过这种批判而揭示出了他对平等和正义的国际秩序的强烈关照。当然,先生关于国际法研究的中国立场和世界立场,在他于1978年以后的中国国际法学的建构过程中得到了更为明确的表现。
先生一以贯之地认为,虽然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法学的任务很艰巨,但是必须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法学。《王铁崖文选》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先生在这个方面的贡献,而其间最为重要的贡献,在我看来,主要是先生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国际政治、经济和科技等方面的发展所做的精彩分析,并立基于此一分析而对中国在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中的定位所展开的讨论,进而在这样一种先生所谓的国际法学的“法律现实主义”的前提下,为确立符合中国利益的“法律现实主义”的国际法学奠定了理论基础。
一如先生在总结他自己的国际法学时所明确指出的,“《国际法引论》在理论上是以现实为依据的。作者不妨自称为现实主义者。但是,这种现实主义,不是像有些西方学者以‘权力政治’为内容的现实主义或者以‘政策定向’为主导的现实主义,因为我所谓的现实主义的现实乃是国际关系的现实,是为法律所制约的现实。
……从这个角度来看,这种现实主义可以说是法律现实主义”(王铁崖《国际法引论》“自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当然,先生的“法律现实主义”的国际法学非常繁复,实在不是我在这里可以阐明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