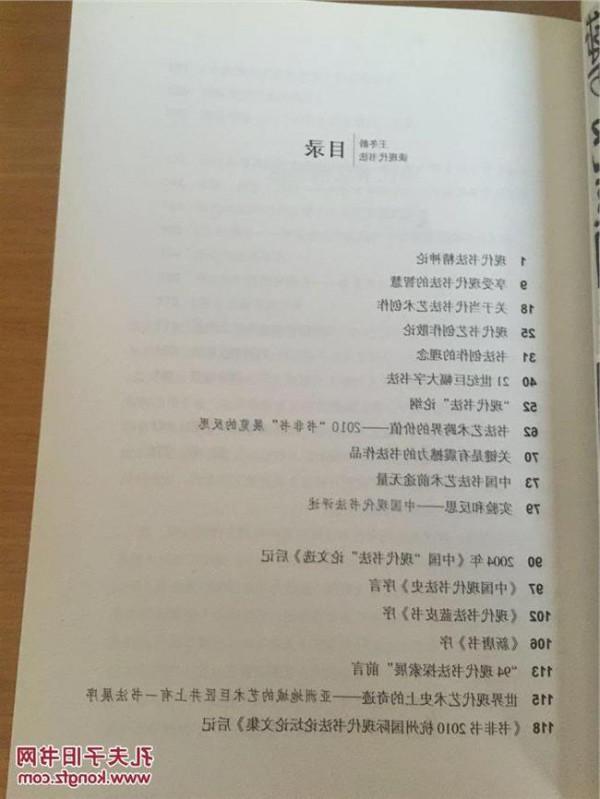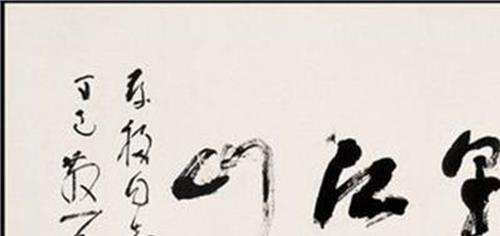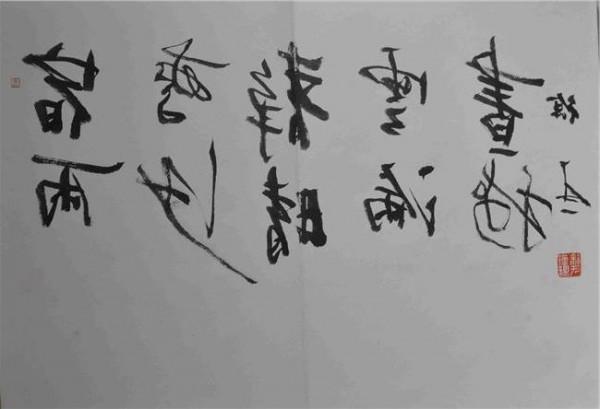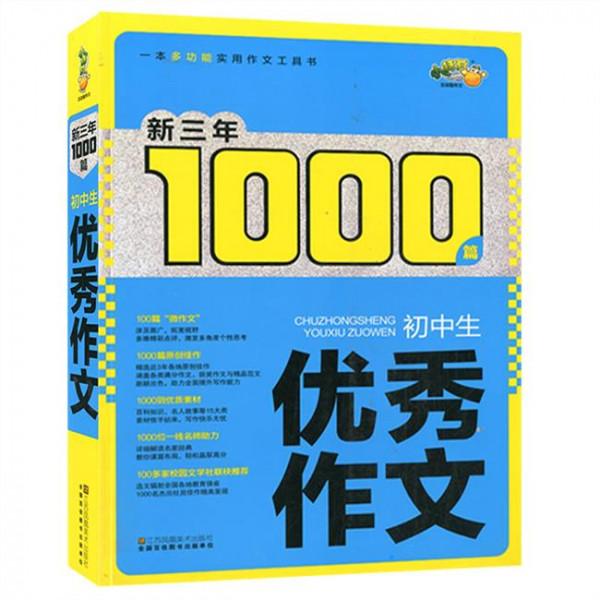王冬龄谈名作名家(修订版)/王冬龄
关于王献之《洛神赋》中国书法发展至魏晋时代,各种书体的演进几近完备,正楷行草均臻成熟,书法已成为独立自觉的艺术。其间,东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更将书法艺术推向新的高峰,被后人奉为圭臬,称之为“南派”书风及“帖学”的开山鼻祖。
从某种意义上说,“王字”整整统治了书坛一千多年,直到清代“碑学”的狂飙突起,才改变了“王字”及“帖学”一统天下的局面。当然“二王”在书法史上的特殊地位和巨大贡献是必须充分肯定的,我们既不可一味崇拜,认为“王字之外无书法”,也不可将其一笔抹煞,贬为“羲之俗书趁姿媚”,而应该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
遗憾的是,现在存世的“二王”作品,除王献之的《鸭头丸帖》为真迹外,其余均为摹本、刻帖。
尽管这些复制品真赝混杂,与真迹尚有距离,但只要善于鉴别,仍不失为研究“二王”的可贵资料。本文拟就王献之小楷《洛神赋》谈几点看法。一王献之(344—386)字子敬,小字官奴,官至中书令,因称王大令。
献之所写曹植《洛神赋》,在唐宋时存世尚不止一本。而唐代欧、虞、柳诸家皆有临摹,“唐人经生小楷,硬黄临本,往往托之羲献以传”(《清河书画舫》)。故宋代董逌云:“今世所传《洛神赋》,余见已四本矣。
”(《广川书跋》)蔡襄则认为:“世多传十三行而已。”(《汪氏珊瑚网》)宋《宣和书谱》记载内府所藏王献之的法书中,《洛神赋》有正、草书两种,正书本后注“不完”二字,此“不完”本应是“十三行”本。献之《洛神赋十三行》真迹,至元代由陈灏手转入赵孟頫处。
赵氏对此迹的原委十分清楚,他说:“晋王献之所书《洛神赋十三行》,二百五十字,人间止有此本,是晋时麻笺,字画神逸,墨采飞动。绍兴间,思陵极力搜访,仅获九行,一百七十六字,所以米友仁跋作九行,定为真迹。
宋末贾似道执国柄,不知何许,复得四行七十四字,则与九行之跋,自相乖忤。故以绍兴所得装于前,仍依绍兴以小玺款之,却以续得四行装于后,以悦生葫芦印及长字印款之耳。
”(《松雪斋集》)赵氏跋此后不久去世,此真迹本亦不知所向。明代祝允明外祖徐有贞跋《赵孟頫书洛神赋》云:“《十三行》真迹,不可复见,一刻本翩翩逸气,犹能动人。”董其昌也说:“大令《洛神赋》真迹,元时犹在赵子昂家,今虽宋拓,不复见矣。
”(《画禅室随笔》)可见元以后,只见刻本,不见真迹了。既然献之《洛神赋十三行》真迹不存,只有赖刻帖以传。而元明以来翻刻甚多,究竟哪种是据真迹刻帖,并能更多地保留献之楷书面貌的版本呢?孙退谷(承泽)谓昔人评《兰亭》如“聚讼”,《洛神赋》虽没有《兰亭序》那样错综复杂,也颇费口舌。
真是“世人惟重十三行,真赝难分争牴牾”,好在我们可以利用现代印刷技术发达的便利,将不同珍本一起对照参阅,以印证前贤的论断。
王献之《洛神赋》版本,从大的方面来划分,可分为“玉版十三行”与“柳跋十三行”两大类。在玉版中向有碧玉版、白玉版之说。所谓白玉版,龚定庵《学海谈龙》云:“雍正八年庚戌,渔人得于西湖葛岭园,亦有篙痕,不及碧玉本之肥古,而以神采胜。
童氏得之归制府,李卫进于朝,在童氏才十日,李五日,人间拓本皆此十五日中幸而流出者。其石至嘉庆三年乾清灾,毁于火。”碧玉版于万历年间,在西湖葛岭贾似道半闲堂旧址出土,后归于陆梦鹤,康熙年间为岭南学政翁嵩年以三百金获得。
杨宾考定为贾似道摹勒于阗玉版者,认为“字之秀劲圆润,行世小楷无出其右”(《铁函斋书跋》)。后翁氏将此版贡入内府。此版现藏首都博物馆。
关于碧玉与白玉之由来,一说白玉为宣和内府所制,碧玉为贾似道所制。或指其发现地点,一为葛岭,一为西湖。杨龙石云:“自明迄于昭代,翻本如林矣,若白玉则前人未有知者,近时如秀水张叔未(廷济)亦未知之而不深信,其他无论也。
”张廷济精于碑帖考证,岂有不知之理?他所题识碧玉本两件,仅题“玉版真本”,其意即舍此种版本而外非真本,否定白玉版之说,可见白玉版定非宣和内府所制。而前人又仅是从瘦本、肥本,或“弃”字竖画连与不连的细节上区分,未深究其理。
且宣和与贾氏相隔一百余年,又是两石,何以玉版上十一处大的泐痕(也有说是篙痕),两个本子有如此一致之理。两相对照,白玉本点画略有僵硬,无碧玉本笔意秀颖,若玉树临风之态。
所以说,白玉本当是后人据碧玉本翻刻而成。第二类为“柳跋洛神赋”。所谓柳跋本,赋的内容自“嬉”至“飞”,共十三行,与玉版本相同,不过前无“晋中书令王献之书”,后无“宣和”印,而是多柳公权跋语两行:“子敬好写《洛神赋》,人间合有数本,此其一焉。
宝历元年正月廿四日起居郎柳公权记。”或者还再附两跋,即:“天祐元年五月六日,堂侄孙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户部璨续题王子敬《洛神帖》后”;“献之《洛神赋》迹遗头尾外得十三行,都二百五十字,重加整背。
祥符八年八月十日周越记”。此柳跋本北宋周越作跋刻石,为十三行帖最早版本。其实《柳跋十三行》墨迹与献之《十三行》真迹,都曾在赵孟頫处,赵氏辨之甚详:“又有一本是《宣和书谱》中所收,七玺完然,是唐人硬黄纸所书,纸略高一分半,亦同《十三行》,二百五十字,笔画沉着,大乏韵胜。
余屡尝细观,当是唐人所临,后却有柳公权跋两行,三十二字,云:‘子敬好写《洛神赋》,人间合有数本,此其一焉。
宝历元年正月廿四日起居郎柳公权记。’所以吾不敢以为真迹者,盖晋唐纸异,亦不可不知也。”(《松雪斋集》)按此说法,赵氏此本即为《宣和书谱》中正书《洛神赋》不完本,亦是周越本。赵孟頫不认为其为真迹,首先指出晋麻笺与唐硬黄纸质不同。
赵氏为一代大家,两本又同在其手,“屡尝细观”,其鉴识当然可信。所谓柳跋本中,种类繁多,不胜枚举。笔者曾见柳公权临《十三行》墨迹照片,其行款与柳跋本刻帖,惟柳跋最后一字不同,刻帖诸本为“记”,墨迹照片为“临”,另附元人袁桷、乔篑成及明董其昌跋。
董云:“右柳公权临《十三行》真迹,与颍上县井中所得刻石颇相似,想为柳公权临摹上石者。其用笔清劲,回腕藏锋,翩翩有冲霄之度,实为自餐霞服气中来,非临池工夫所能庶几也。
此卷向藏御府,有宣和、政和小玺,后为元时周公瑾所得,传流有据,今从馆师韩宗伯家借观。焚香展玩,敬为题识。”观此本虽不可据,然明言柳临本,却可玩味。
因为柳跋本之“记”字,也可理解为临写之意。这当然还要靠版本说话,所谓目鉴,而不是耳鉴。张廷济说:“唐人临摹晋帖悉皆自运笔意,无规规形似之见,此《十三行》即柳跋本也,世以贾相‘玉版’晚出,因目此为《十三行》正本,愚谓玉刻冲和,不见运法之迹,自从大令真迹摹勒,此则谨严肃括,法胜于意,全是唐人结构,味诚悬题记,虽不明言摹勒,已露端倪。
”(《清仪阁题跋》)杨守敬《学书迩言》亦说:“世传唐荆川所藏本,有柳诚悬跋者为真迹,余以为不似晋人之笔,或即是诚悬临本。
”张、杨二家之论,颇有见地。另外,张氏在《跋元晏斋本》时说:“管驷卿为勒石名手,此刻经年乃就……传闻管刻至柳跋二行,罄心研索,必欲追取赋与跋用笔所以异处,喉间致闻血腥,良工心苦,谅哉。
”这一点也为我们提供了柳跋本为唐人摹本的佐证。袁晏斋本在柳跋本中久负盛名,管氏既是名手,只要照祖本摹刻,做到不差毫发即可,又何以至柳跋处要追取用笔异处,这反而说明了祖本献之写的赋与柳跋用笔一致,管氏察觉到这里的破绽,正是他高明之处,可谓作伪心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