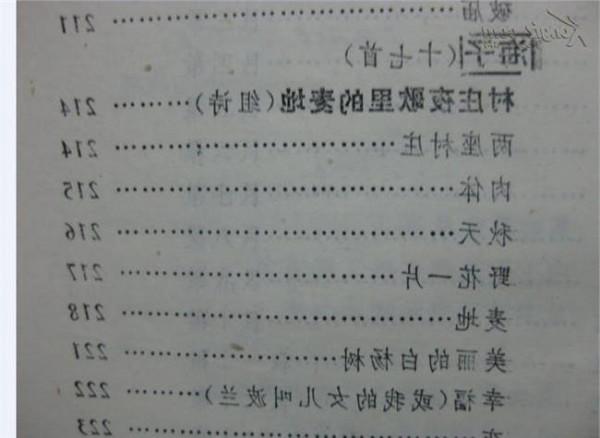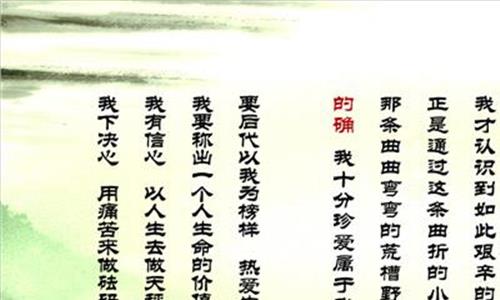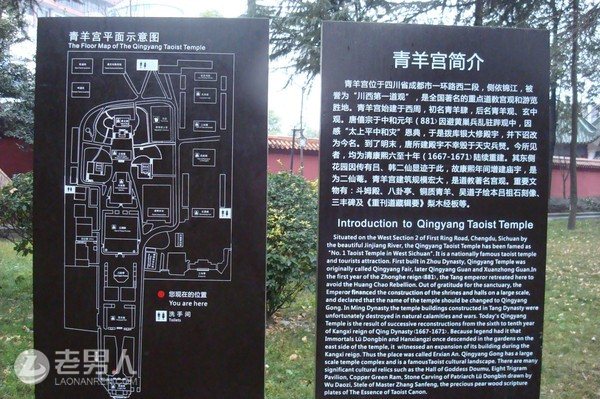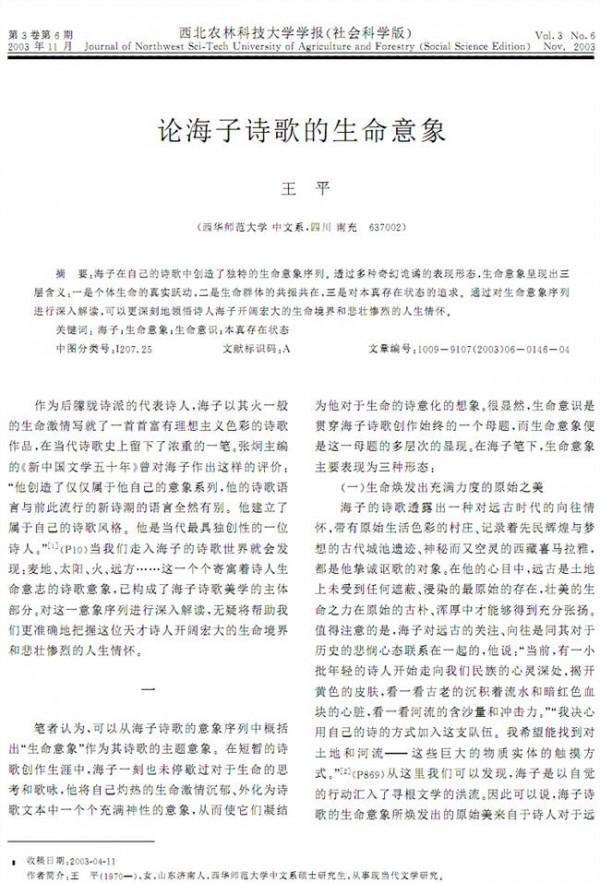戈麦海子 生命的故事 | 西川忆海子戈麦骆一禾张风华
怎样才能卸下心灵的重负?即使不能完全摆脱,怎样才能稍微从容一些地走路,而不必紧张地、时不时地回头张望跟随在身后的幽灵?我已为逝者写下不少诗篇和文章,但依然无法凭借文字完全清除他们留给我的阴影。保存一份记忆,是良心所在、道义所在,但也不能否认,死亡像一股凉气进人我的大脑,进入我的脊椎,它像恐怖的天启进入我的噩梦。
我曾经梦见我孤身一人步行在山谷中一条落叶纷飞的小道上,径直走进一座无人居住的房屋。这房屋内的一切都是蓝色的:蓝色的墙壁、蓝色的地板、蓝色的桌椅和茶杯,一种冰冷的感觉,忽然蓝色的窗帘自动拉开!这不是那种大喊大叫的鬼魂在做怪,这是寂静,是空无,是死亡的真实面容。
美国女诗人希尔维亚•普拉斯生前说过:"死亡是一门艺术。"对于一个像普拉斯那样的自杀者,死亡可能的确是一门艺术,可对于生者,对于不得不面对死亡的人来说,死亡,作为一个事实,太残酷了,这其中不包含任何人们想象的诗意,甚至哲学也派不上用场;任何人的安慰都无用,任何你对死亡的猜测都失效。
措手不及。哑口无言。头发倒竖。为时已晚。你只能接受一切,体验一切,并且回溯死者的一生,从中收获悲哀、痛苦、焦虑、愤怒、无奈、荒诞,以及真理。
1989年3月26日诗人海子的死把我带向此一精神境地。骆一禾在山海关料理完海子的后事,回来后向我描述了孩子最后的情形:戴着眼镜,右额角有擦伤,嘴张开,身子断为两节……同年5月,骆一禾在北京天坛医院作为植物人躺了18天,于5月31日去世。
一禾的父亲因此双目失明,一禾的母亲在火化室门口瘫倒在地……然后是1991年9月24日诗人戈麦自沉于北京西郊万泉河。送别戈麦的那一天,我硬着头皮第一个走进告别室,但戈麦已经无法看到我,因为他的脸上敷着石膏……然后是1992年秋天我的大学同学、我最早的诗友之一张凤华在深圳跳楼自杀。从那只黑色的电话里得到张凤华的死亡时,我的脑袋轰地就木了。
毁灭与生俱来:母亲们悲叹
儿女生不逢辰,却争着投胎。
横冲直撞地奔向人间,
却落得头破血流多惨。
这是英国17世纪玄学派诗人约翰•堂恩《尘世剖析》中的几行诗歌,表现了他对人类世界的悲观绝望。尽管他也写过《死神莫骄妄》那样的诗歌:“凡人了却浮生,但精神永生,超脱死的魔掌,灭绝死神!”但看来《尘世剖析》说出了更多生命的真相。
我也曾经积极地看待死亡,我也曾经接受过肤浅的人生观教育,但这一切都说服不了死亡本身。不能阻止他人走向生命的绝境使我无限愧疚,而目睹他人死亡使我犹如犯罪。可是上帝看来还嫌我看到的死亡不够多,还要让我看到更多文学的尸体、哲学的尸体、道德的尸体、宗法的尸体、政治的尸体……也是在1992年秋天,在西安,我亲眼目睹了一个农民从鼓楼南大街上一座商业大厦高高的雨棚上一跃而下,“嗵”的一声把死亡固定为一个不可磨灭的场面。
这场面把所有的死亡吸收过来,以无比暴烈的形式诉说生命的哀痛。我好像一下子被死亡击出天外,等我回落到地上,尽管还活着,但已经是另一个我。这时我越过种种谎言、虚饰、小布什乔亚的多愁善感与儿女情长,看到了约翰•堂恩所看到的生命的真相、世界的真相,看到了一向处于遮蔽状态的负面的事物,于是我抱持了很久的世界观、道德观、艺术观、生命观訇然崩塌。
只有体验过这一切的人才清楚这一切的力量。
刺眼的死亡强迫我思考死亡究竟想对生命说些什么?对于生命,死亡的意义何在?人能否站在生命的立场上谈论死亡?人应当怎样生活?不同的人应当依据什么划出边界?何谓理解?何谓抱负?理解和抱负何以能够既引导我们前行,又不至令我们走到生活的反面?拔高的道德要求肯定是有害的,那么道德的平均律是否同样有害,因为它鼓励庸人?我们以培养真空人才为目标的高尚的教育体系是否从根本上就是反人道的?那么何谓善?善与欲望的关系何如?何谓真?真与假的界限是否如常识所告诉我们的那样分明?事物的负面价值,也即世界的阴影部分是否被我们忽略了?怎样才能既使用事物的负面价值又不至身陷邪恶的泥塘?我们是否应以生命包容邪恶?我们的生命中是否已然包含着邪恶?承认这一点是否意味着我们理解了人道主义?人道主义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人道主义我们应当首先给予他人还是应当首先给予自己?何谓人道的艺术?人道的艺术是否就是伟大的艺术?……要回答这些问题或许需要我们一生的时间,或许一生的时间根本不够。
瑞士精神分析大师荣格曾经写过一篇作品,名为《向死者的七次布道》。荣格视现代人为死者,而布道者却是公元2世纪叙利亚诺斯替教的领袖巴西里德斯。通过这篇布道辞,荣格表明,人们应当把精神的门户打开,让那些幽灵进来教训我们。
在过去,在传统中,多数精神导师都曾访问过死者,如俄耳浦斯、埃涅阿斯、耶稣,以及我们中国的黄道士等。所以,荣格的意思,不是生者向死者布道,为他们指路,提醒他们要迈过多少道冥府的门槛,转过多少个无人的街角,而是死者向生者布道,告诉我们生命的航行需要张挂多少张帆,在恶劣风浪中怎样稳住船舵。
很明显,在这里,荣格是要我们将精神的门户主动打开,这一点肯定不易做到,这要求我们放弃身为生者的满足与矫情、安全与无聊,去寻觅,去倾听。
不过不管我们是否愿意主动打开精神的门户,幽灵都会闯进来。不是人人都能成为俄耳浦斯、埃涅阿斯、耶稣、黄道士,对于我们背向死亡的心态,死亡命令我们转身,接纳。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生者,死亡是一种教育。
这不同于有人倡导的"死亡教育",教育我们去了解死亡,正视死亡;不,我的意思正相反,死亡是要以它的残酷、它的黑暗、它全部的时间过去给我们以训导、撼动和摧毁。这样的教育是我们大多数人所不愿意接受的,但我们又必须接受。我们被迫改变我们自己,好让死亡满意。
圣保罗说过:"我每天死亡一千次。"我懂他的意思:他把死亡视作一种生命状态,每一个人每一天都会有无数个瞬间进入死亡。但是在经历了海子、骆一禾、戈麦、张风华,以及那些大街上的死亡之后,我不再愿意承认这一点。
不用一千次,几次强行刺人我们眼帘的死亡已经让我们不得不承认生命的脆弱与无常、世界的愚蠢和暴力。他们死时都那么年轻,他们一个个都那么才华横溢,他们去了哪里?或许我可以安慰自己:当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就能够与他们相会,他们已经用死亡把来世变得不那么可怕,但是这解决不了生的问题。
我多想学会心平气和地面对死亡。我多想忘却这一切,让文字和纸张来承受记忆之苦,以便能如诗人梯姆•柳本在加拿大圣彼得修道院外的小树林里劝慰我的那样:放下心灵的重负,脱胎换骨,开始新的生活。我或许还会一千次重返记忆,但不是重返死亡、黑暗、暴力和血腥,而是重返活的记忆:绿草、清泉、醉汉的丑态、女邻居的芳心。
今天早晨阳光明媚。窗外那棵已有两百年树龄的老榆树上,一只喜鹊"嘎嘎"奏鸣。这应该也是海子的早晨、骆一禾的早晨、戈麦的早晨、张风华的早晨。
张风华是我最早的诗友之一。大学生活一开始,他、我以及另外三名同学(一男两女)便组成了一个小小的文学团体。我们五人经常结伴去圆明园散步,聊天,并且还油印了一份小小的诗刊《五色石》。
张风华是个小个子,皮肤黑,走路时一颠一颠,为人极聪明,但可能也有些自卑。他是1981年天津市高考外语科状元,据说上初三时他参加天津市高中生知识竞赛就得了第三名。他的英语非常好,法语也不错,同时他还自修德语、日语,甚至拉丁文。这样一个天才是他那个家庭的奇迹。他的父亲是一位澡堂工人。从张风华身上可以看出他们朴实、厚道的家风。
一旦他不再谈论诗歌,他就转而谈论佛法和气功。有一年寒假他从天津回到北京。天已晚了,他没能赶上回北京大学的公共汽车,便到我家找我(那时我家距火车站不远。但是他又不忍心打扰我们一家人的睡眠,便在我家院外胡同里一辆大卡车的车斗里打坐、发功呆了一夜。这件事深深感动了我的母亲:她把张风华看做天下最好的人。
大概是为了改善家庭的经济状况,多挣钱赡养父母,也加上那么一点儿虚荣心,大学毕业时他报名去内地设在香港的华润公司,可行李箱里却只带了一本《华严经》、一本《老子》、一本《庄子》和几件衣服。第一次回内地探亲,他带给我一本英国诗人D.J恩赖特编的《牛津版战后诗选1945-1980》,要不是我坚决反对,他会带给我一台电脑全自动洗衣机。那时内地电器市场还不像今天这样繁荣。
他写信告诉我,刚到香港那个花花世界时他总觉得有件什么事该于而未干,想来想去,是没见识过色情。于是在一个星期天,为了避免让同事撞上,他走很远的路去看了一场色情电影,从此心也就踏实下来。这真是佛教徒特有的幽默。
香港虽号称"东方之珠",但在我看来它可能不适于张风华的聪明才智与巨大的精神关照。大概他在香港的生活极其乏味。他来信说他要去美国万佛城落发为僧。我去信劝他,若要出家,在五台山更好,这样我们还可以离得近一些。但最终他既没有去万佛城,也没有去五台山。
戈麦原名褚福军,黑龙江萝北县人。1985年我大学毕业,戈麦正好考入北大中文系。毕业以后他到外文局《中国文学》杂志社当编辑。1990年初夏的某一天,他到我当时工作的单位找我,我们谈了很久,就这样成了朋友。
戈麦的诗歌使我惊讶。他一拿起笔来就是个成熟而且优秀的诗人。他的诗歌广阔而深远,展现出对于本体、精神、时间、现象的关怀;他的语言丰富而肯定,将世界和生命转化成棱角锋利的语象。戈麦生命中惟一的问题是,未能以成熟的诗歌换来成熟的心智。他年轻且敏感,无力面对生活的压力,并因此怀疑自己的价值。
有一回,北京大学作家班的人请吃饭,戈麦也去了。他坐在我身边,小声对我说:"在座的不是名人就是教授、博士,只有我什么也不是!"戈麦想过一种诗人的生活,但自觉此路走不通;他又想过一种普通人的生活,但为他所爱恋的女孩所拒绝。我是后来才知道这些事的。
在戈麦1991年5月以第三人称写的《一个复杂的灵魂》(后被戈麦好友、诗人西渡将题目改为《戈麦自述》,放在他编的戈麦诗集《彗星》的卷首)一文中,他说:“戈麦喜欢一切不可能的事,他相信一位年岁稍长于他的诗人的一句话:‘让不可能的成为可能’。”这句话是我说的,在短诗《李白》中。
有一段时间我住在北京火车站附近的一个大杂院里。我们住得较近的十几户人家轮流负责收水电费。有一次--那是在戈麦去世以后--为了收水电费我敲开了一户人家,这家里忽然冒出来一个我以前没太注意过的女孩。她问我:"你是西川?"我感到诧异,没想到在我的邻居中还有人知道我的笔名。那女孩接着问:"你认识戈麦吧?"这使我越发诧异。"那么你是谁?"她说你别问了,以后再说。可以后我再也没见过这个女孩。
戈麦从未见过海子,他曾引此为憾事。但是尽管互不相识,他们依然是精神上的兄弟,他们都是早慧的天才。我听说,还是在海子两岁时,村子里每开批斗大会,总要先由海子家人把他抱上台去朗诵一段毛主席语录,这无疑使每一次批斗大会多了点儿喜庆色彩。
海子15岁进入北京大学法律系。但他学习法律纯属偶然:考大学时他可能还不大清楚法律为何物。他报考的第一志愿本是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但没有被取录;他的第二志愿是北京大学中文系,但也没有被录取。大概是北大法律系负责招生的老师看到了他的材料,便与他家人联系,问他是否愿读法律,他这才成了法律系的学生。
我现在想,如果当年他上了复旦大学中文系,他不可能是后来的海子,如果当年他上了北京大学中文系,他也不可能是后来的他。作为一名法律系的学生,他曾写过一篇论述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的沦文,据说这篇论文曾经得到过著名学者金观涛的称赞。他还向我推荐过印度的《摩奴法典》,说这是法律与诗歌结合的典范。
由于海子没有受过严格的文学训练,因而在某种程度上他保持了对文学的"大众式"的热爱。他广读武侠小说。大概那时已出版的金庸、古龙、梁羽生的书他都读过,并且买下来。他说将来他打算用这些书帮他在乡下做裁缝的父亲开个租书铺。
由于海子没有受过严格的文学训练,他的身上始终洋溢着一种自由的写作精神。这首先表现在写作的抱负方面,其次表现在对语言的霸占方面,再其次表现在对想象力的挥霍方面。有一年他旅行去了四川。在成都他见到一些诗人。吃饭时大伙比赛想象力:天堂是什么样?天堂里有什么?后来海子跟一禾和我吹牛:他的想象力最棒,他把别人全"灭"了。
在海子身上蕴藏着自然之力,因此他的写作无需仰赖书本、理论。他把自然之力转化为直觉判断力,一眼就看出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其实就是一部《旧约》:像大卫王一样,布恩迪亚上校也领兵打仗,也写诗,也睡女人,也搞小发明。
由于有了《旧约》的背景,《百年孤独》得以放肆地展开,同时不失其精神的一致性。他瞧不起《百年孤独》的追随者们;他瞧不起他们鸡零狗碎的文学。他认同韩波那样的少年天才。他在一份写作提纲上写道:"要和韩波赛一赛。"
海子去世以后,骆一禾和我做了分工:他与海子家人、政法大学校方一起去山海关料理海子后事,我则留在北京为海子家人募捐。一禾从山海关回采,未回自己家,先来我家。他一脸疲倦,头发上、黑色的风衣上落满尘土。从某种意义上说,一禾与海子是两类不同的诗人。
他们走到一起是由于他们有相似的诗歌抱负以及同等强度却不同质地的才华。骆一禾文雅、渊博、深刻、正直、爱朋友,对于世界文明负有使命感。他的写作和做人被"修远"这两个字表达出来。戈麦曾经把他的《修远》一诗复印下来,贴在床头,反复诵读。
一禾生前常常说到"义人"和"义人之路",想必是由于深受其父母的熏陶。一禾的父亲骆耕漠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我在陈敏之为《顾准文集》所写的序言中读到,一禾的父母与顾准是肝胆相照的朋友。1974年,由于坚持思想而历尽坎坷与折磨的顾准病危住进了医院,这时在病榻边悉心照料顾准的人中就有一禾的父母。
一禾在写作之初,曾经受益于老作家王愿坚,他们之间有书信来往。我和一禾相识的时候他已有一些作品发表、那时他穿着,一件褪了色的蓝色卡叽布中山装,一天到晚为文学忙碌。北京入学五四文学社印行过一本《大学生文学作品选》,刊中推出一辑诗歌,贯以"第三代"之名。这看来是"第三代"作为一个诗歌批评术语第一次被使用,这是一禾的功劳。
他后来成为北京出版社《十月》杂志编辑部的编辑。本来他可以有更多方便发表作品,但他严格要求自己不与其他杂志的编辑互换作品来发表,他也因此得罪了不少他称之为"文学肉虫子"的人。为了在《十月》发表作品,恭维他的人大有人在。有一次,一个人往他家里打电话,在电话里想象他家窗外一定是一座花园,一禾回敬道:"我家窗外是一条臭水沟!"
被一禾视做朋友的人,一定是他从内心深处敬佩和珍重的人,这其中有诗人昌耀、小说家张承志、小说家黄尧、传记作家林贤治等。我本人能够成为一禾的朋友是我的荣幸。他帮助我在《十月》上发表了我22岁时写的长诗《雨季》,并且为《雨季》专门写下一段引言,我把这引言视做他卓绝的心声:
我们祈愿从沉思和体验开始,获致原生的冲涌,一切言词和变动根源的现代意识。它将决定诗人在人心中留下的影像。为此这诗歌成为一种动作:它把经历、感触、印象、幻想、梦境和语词经沉思渴想凝聚,获得诗境与世界观的汇通,并通过这凝聚把启示说得洗练:某种震撼人心的情绪骤然变为能听似见的,从而体验令人的生命。
这诗歌不是心智一角孤单的发声,而是整个精神活动的通明与诗化,它剥凿着现代意识,直到那火红而不见天日的固体呈现于眼前,新鲜而痛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