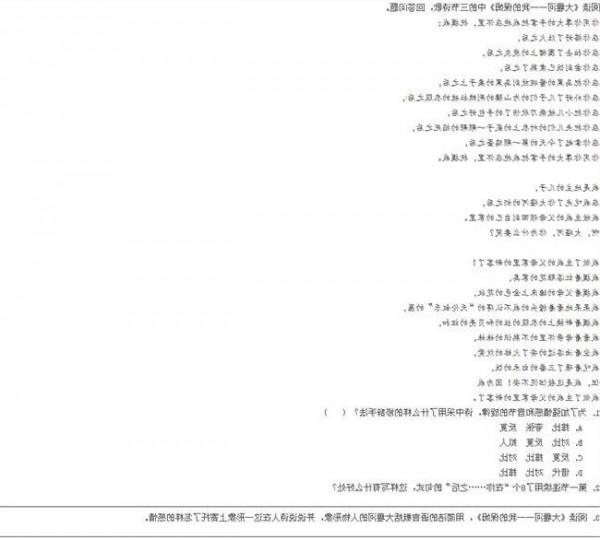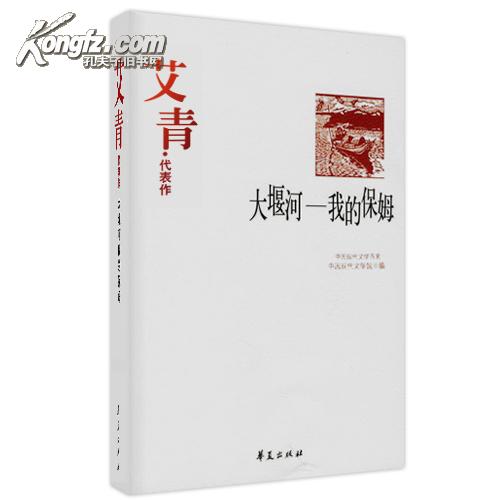胡适我的母亲 比起《大堰河——我的保姆》 胡适的《母亲》更有血肉(下)
长江商报消息 教育先进的国家甚至没有教科书,只有广泛的阅读
锐读:在出版这套“语文书”之前,你做过相当多的语文课本分析、研究工作,还出过《对抗语文》。你想“对抗”的是什么?此次凭一己之力编教材,是在延续着这种“对抗”?
叶开:我对抗着的是一种长期弥漫在我们语文教材、语文教学上的令人窒息的“非人性”和语文的物化——我曾写文章说这是把个性差异的孩子打磨成面目模糊的螺丝钉,是落后蛮横的共性化教育,而非尊重爱护的差异化教育。这种语文教育的“非人性以及相随而至的封闭性和惰性”,造成了今日中国语文教育的沉默无趣,破坏了中国新一代孩子的独立思考能力、写作能力和表达能力——而这种能力,是今后他们无论从事什么职业都需要的基础竞争力。
锐读:很多教师、家长、学者、作家都参与了对语文及其教学的批判,但惟独你在批判之后还拿出了这么一套书。你怎么自评这种行动?
叶开:对语文教育进行批判有不同层面,不同深度。有些作家在记者采访时临时临急说几句不痛不痒的闲话,并不是真正有价值的批判;而深入地研究现行各种版本的语文教材,与中小学校的语文教师和学生广泛地交流,从而有的放矢地进行深入批判和反思,又是另外一种。而在深入广泛地批判之后,拿出自己实际的建设性方案来,并自己切实编写“语文书”,又是另外一种。我推崇切实地做有益的小事,而不是做空头批评家。
锐读:这套书的读者面是怎样的?更适合学生在课堂上读还是作为课外阅读?
叶开:我编写这套《语文书》适合不同层面的中小学生阅读,也适合文学爱好者,实际上是适合所有华文地区读者阅读。它适合课外阅读,也合适在课堂上学习。已经有些熟悉的教师在课堂上进行试验了,说学生很喜欢,兴致很高。
我在确定编写思想和具体框架时,有意地跟现行教科书编写模式区分开,不以各年级分册模式编写。其实很多教育先进国家并没有严格区分的教科书,甚至没有教科书,更多的是广泛的阅读。我国传统也没有这种细分到荒谬程度的语文教科书。
现在因一些学者和媒体推崇而流行开来的传统蒙学读本,一般只具备基本的识字和阅读功能,然后进阶阅读“四书五经”以及更广泛的其他经典。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对胡适之先生等推崇的新派教科书就不太赞同。
锐读:但现在的青少年课余似乎更青睐读郭敬明、安东尼、杨红樱以及一些漫画杂志、轻阅读类作品。对于他们选择非经典性的流行文学的阅读倾向,你持什么态度?
叶开:我不反对青少年课外阅读这些流行作品。我更希望在正常的教育内,能给学生进行有成效的经典阅读培养,这样他们才能鉴别出什么只是消遣娱乐的消费作品,什么才是培育心智的经典名著。差别在于:消费作品在人生中如一阵小小的风沙,不断落下;经典名著是一眼温润深泉,清澈甘甜的活水持续涌现。
我们的教科书受制于糟糕的文学史观
锐读:你在选胡适的散文《母亲》时是怎么想的?我想起有三位浙江教师在2009年写了一份考察报告,总结说小学语文课本中的母亲形象不外两张脸孔——要么苦大仇深,要么道德完美如同圣女,很少见到有血有肉的真实的生活中的母亲。
叶开:写母亲的好作品很多,但选入现行语文教材里的作品不知道为何都在歪曲一位真实的母亲的形象。作家余华在为莫言的中篇小说《欢乐》写的一篇评论文章《谁是我们共同的母亲》里,精妙地揭示了国家意识形态对母亲形象的改造和升华。
在这种改造中,母亲不再有血肉,而成为国家、土地、文化、政府、党派的象征。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在这些意识形态化的母亲身上,你看不到她们真正的喜怒哀乐,真正的人性。而我选胡适先生的散文《母亲》,就是想让学生看一看一位真实母亲的样子。
锐读:我能理解你在书中会多选择1980年代以后创作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作为老牌文学杂志的编辑,你是不是一直对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在中小学生中的接受度偏低而倍感遗憾?
叶开:我对此不仅是遗憾,而且是悲伤。我们的语文教科书受制于一些糟糕的文学史观念和逻辑,似乎只有去世很久的人才更伟大。也似乎只有被选定的那几位“鲁郭茅巴老曹”才是正宗祖师爷。但这种座次排定完全是意识形态的把戏,是水浒梁山的排位置分交椅,很搞笑。
1980年代后,随着思想的开放,人们开始知道了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等作家的作品。我个人精读中国当代文学创作,深知这30年的文学创作遭到了极大的贬抑和蔑视,而实际上,这30年的文学创作已经达到了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最高水平。华文作家在短短12年内两次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殊荣,与日本并列亚洲第一,是一个可以作为衡量的鲜明标志。
锐读:前不久,王安忆称莫言的小说《大风》最应该进教科书。而你不仅选了这篇,还认为莫言很多散文和短篇小说都可以选入。你希望借莫言的作品,以及格非、马原等被称为“先锋作家”的作品向学生传递什么?
叶开:2012年8月莫言来上海参加书展,我就在边吃饭边神侃时,和他签订了《大风》的授权书。他很高兴地签名,并告诉我等他回到北京后修改一次,再发给我。他说非常支持我对语文教育的批判,1990年代末他也写过《虚伪的教育》等文章来反思过现行教育。
王安忆也很支持我对语文教育的批判,我们在交流时常常谈到语文教科书的一些可笑而可恨的问题,例如她的散文《我们家里的男子汉》遭到严重窜改,例如选文大多数很糟糕等。马原等作家的作品一直遭受现行教科书的排斥,其中一种保守的观点是,学生读不懂。
我一直认为,读不懂的是教科书编写者,是一些顽固保守的老师,而不是学生。你只要给他们读,他们就懂了。我的目的是让学生知道,文学里有各种各样不同的作品,不同的作品是作家们不同个性、不同思想的具体体现。阅读和学习更多丰富的作品,对学生的思想和表达,都有直接的好处。
进入小学以后,孩子们的灵感都枯竭了
锐读:你透露自己作为一名考试界前辈,高考、硕士生考、博士生考,专业课和写作课都是以第一名的最优成绩过关。这除了与阅读量大有关,还因为什么别的?
叶开:这个是我为了壮胆而在中学里吹牛的。我一直认为,考试能力只是一种次一等的能力。有个著名的说法:考试成功只能证明你在学校成功,不能证明你在社会上也成功。但我很讨厌“成功”这个词。建立在母语基础上的语文是门特殊学科,有其不同于数学等科目的特殊性。
语文学习没有捷径可走,有大量的、切实有效的阅读作为基础,只需稍加妥协,你就能考出高分。我在乡村长大,在乡村中学读书,除了高考那次,其余的考试常常不及格,很惨。但我努力了一下,就考好了。无他秘方,相对同龄人更多的有效阅读,然后稍稍适应一下考试的技巧。
锐读:你近十年来都在陪女儿一起读书,同时自己也在“成长”。你从女儿这代人身上学到了什么?这反映到这套书的编写中,具体有哪些表现?
叶开:我一直认为孩子才是我们的老师,是我们这些被毁坏了心灵的大人重新返回到更为本质、自然的世界去的向导。看到孩子,我深深地明白了自己被毁坏得有多么厉害。过去,当我们小时候,也是这样的天真无邪、自由自在的。
可是,一旦进入社会,就被逐步、有计划、有步骤地毁坏了。我和太太说,孩子进入小学之前,我们都一起疯玩,不教她识字,只随她自己的兴趣胡乱画画,涂鸦。但进入到小学之后,热爱画画的孩子们灵感都枯竭了,被学校的各种可怕的恐吓吓坏了。每次我被孩子五六岁时那些充满了神思的涂鸦所感动时,就对现行的毁坏式教育模式充满憎恶。这不仅仅是语文一门学科的问题,而是整个教育制度的问题。
在陪小孩读书时,我发现自己的相关阅读近乎空白,所以也是一直在补课,不断地阅读。有趣的作品,我们会一起讨论,相互推荐。例如“综合分册”的《一则绕口令的故事》等,就是她喜欢的作品。《小说分册》里须一瓜的短篇小说《彩虹总在风雨后》,在确定编入时,我也请她读了一遍,她很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