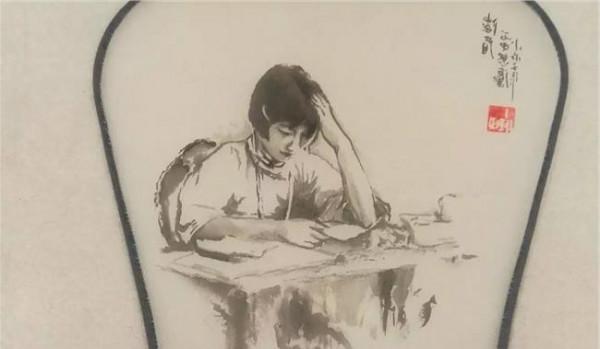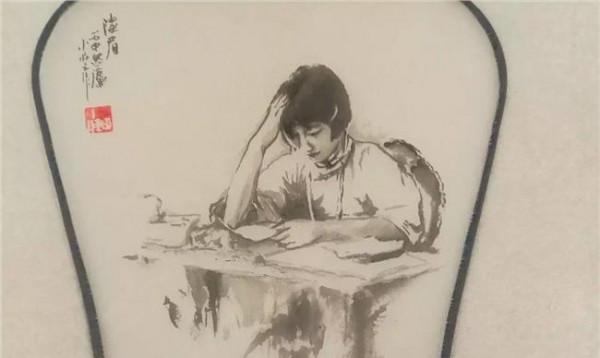凌叔华酒后赏析 凌叔华《酒后》的爱情心理意义
凌淑华的短篇小说《酒后》,塑造了一位敢于寻找自我主体价值的新女性,小说的情节十分简单,写的是一位在家庭生活中不幸的男子,因醉酒鼾睡在朋友家,朋友的妻子采苕同情他的境遇,钦佩其才华和为人,于是便向自己的丈夫提出想吻一吻他的要求。
我们首先不管采苕的这种想法是否经得起道德的检验,但多少说明了这一类女性开始微露那种大胆的对自我主体价值注目的端倪,因为在中国的传统社会,男性权威长期严酷地禁闭着女性的心灵世界,使她们对自身灵魂的表达受到来自外在世界的羁绊和束缚,承受着男权社会对她们“严重的审查”,只有女性自我独立意识真正觉醒后,女性才能展开对自我本真的生命追求与探寻。
作者在拨开小说叙述的遮掩和枝蔓中,诠释出真正的女性运动不仅追求客观上的平等,更是强调女性自我意识的独立和勇于探寻女性主体价值,从这一意义上来说,绮霞已经基本具备这一要求。凌叔华描写了一个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新女性绮霞,从女性自我意识发展的角度看,可以看到作家把对女性自我价值的探寻看得高于幸福爱情生活之上,将女主人公置于尖锐冲突的生存境遇中, 使绮霞较其他女性走得更远,当别的女性还在为争取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努力奋斗的时候,她已经触及到了更深一层的问题:女性自我价值在更高层次上的实现。
在她身上,最大程度地体现了“五四”以来现代女性追寻人格独立、自我价值实现的强烈愿望和自觉行为。并把这种自觉行为上升到女性是人格独立、具有主体性的人的高度,并在痛苦的思索之中决然地实现自身质的一次蜕变,这使女性生存的底色中透射出新的时代曙光。
在中国的传统文学中,酒往往是与愁绪联系在一起的。李太白举杯邀明月,勾起的是壮志难酬的感慨;易安居士东篱把酒,难消对丈夫的思念。但在“中国的曼殊菲尔”笔下,酒后的少妇却多了一份平常难以展露的美,这种美是对世俗的反叛,是桀骜不驯的美,是追求自由的美。
这种追求个性解放的美已经在许多文学评论家的笔下得以绽放,他们将这种美看成是女权主义思想的流露和对男权的反抗。而我所关注的并不仅仅是这种美的内容,还有这种美激发的过程。女主人公那泛着涟漪的心海在一次偶然的机会被激起波澜复又归于平静,上演了一场精彩的心灵挣扎戏,也巧妙地诠释了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
一个平日里温柔贤淑的少妇,竟然请求自己的丈夫允许她亲吻一下他喝醉酒的朋友子仪。这种行为注定是经不起道德考验的,这种场景也注定只能发生在小说里。但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来看,这无疑是采苕“本我”的流露,是“本我”冲破伦理道德的藩篱所展现出来的真性情。
但在凌淑华女士的笔下,采苕“本我”的流露不是突兀的,而是自然而然的。当一个作家笔下的环境可以将读者都灌醉时,她笔下的人物又怎能不陶醉于其中呢?文章的开头十分简单,只有短短的五个字“夜深客散了”,但只这五个字就为故事的进一步发展创设了静谧的环境,也为女主人公难以外道的思想的激发排除了他人的干扰。
除此以外,作者还为采苕“本我”的激发安排了一个合理的情境,那就是酒后。俗话说,酒后吐真言,虽说此话未必千真万确,但也表明酒后是人摘去伪善的面具的时候,也就是“自我”和“超我”意识削弱之时,这样“本我”在被激发时所受的阻力便大大减少。
再加上空气中弥漫的温馨甜美的香味,更是加重了这种沉醉的程度,不禁有“酒不醉人人自醉”的效果。
这样,在这个静谧、甜蜜、温暖的氛围中,女主人公的“本我”意识便一步步得以流露。在作者笔下,女性所特有的细腻得到了完美的诠释。在这篇小说中,女主人公的心理活动经历了六个复杂的过程。
原本就爱好文墨且十分钦佩子仪的采苕,那晚的酒宴中子仪的言语风采更是使她心醉,使她那种一直压抑在心底想要亲近子仪的潜意识得到了触动。但在文章的开头,采苕的还处于情绪的压抑期,她想要关心子仪,想要亲自为他盖毛毡,但在丈夫面前,她仍有所顾虑。
因此,只好指挥丈夫去办,可见此时的她还是严守道德界线的。接下来作者不厌其烦地写了永璋对妻子的赞美,但采苕却那么心不在焉,不断敷衍。她两次从与丈夫的对话中牵涉到子仪身上,两次委婉地想要打断丈夫的话,三次写她回头看子仪。
可见采苕一直沉醉于对子仪的关注中,这可看做是采苕“本我”的发展期。这种“本我”意识一步步激发,最终在丈夫问她想要什么新年礼物时得到了总爆发,她向丈夫提出了可不可以闻一闻子仪的脸的要求。
不出我们所料,永璋自然是拒绝了采苕不合常理的要求。在被拒绝之后,采苕的心理进入了挣扎期,她向丈夫详细解释了自己这种要求产生的原因,与其说是她在说服自己的丈夫,不如说是在说服她自己,得到丈夫的允许不过是为了坚定自己的“本我”意识。
最终永璋同意了采苕的要求,但采苕自己却陷入了“本我”的畏缩期,犹豫不决。最终,采苕的反叛行为并没有成行,她的“本我”意识还是被压抑了回去。这就是采苕的“本我”意识所经历的孕育、发展、爆发、挣扎、畏缩和消失的六个阶段。
在赏析这篇小说时,似乎所有的人都将目光集中在了采苕的身上,却忽略了作者另一个精心刻画的人物形象永璋。如果说采苕在小说中流露了“本我”意识,永璋又何尝没有流露“本我”呢?从他与妻子的对话中,我们不难看出他是一个十分马虎的人。
他觉察不到妻子对他的敷衍,没有理会妻子平时对子仪的倾心,甚至没有注意到妻子眉的美。这样一个马虎的人,相必在平时也不会对妻子说很多甜言蜜语的话,但酒后的他吐露了自己的心声,真切地表达了自己对妻子的爱,这也可以看做是永璋“本我”意识的流露。
平时稍显木讷,不善言辞的他在酒后展现了他的另一面。除此以外,在本文中,永璋的形象还有两个作用。一方面,永璋充当了采苕“本我”意识觉醒的推动者。
他笨拙且滥俗的赞美,不仅没有使妻子开心,反而更让妻子感到子仪思想的深邃和言谈的不凡。另一方面,在永璋阻拦妻子想要亲吻子仪的行为时,永璋所充当的其实已不再是丈夫的角色,而是采苕另一个人格结构的组成部分“自我”。
通过弗洛伊德的理论,我们知道“自我”的作用是控制和指导“本我”,“自我”处于欲望和满足之间。凌淑华在描写采苕心中“本我”和“自我”的挣扎时,没有介入人物的心理直接描写其心理活动,而是巧妙的让丈夫充当了“自我”的角色,阻拦“本我”的冲动。
面对采苕的不合理要求,永璋,也就是“自我”进行了四次阻拦,其中最耐人寻味的一次阻拦便是永璋说道:“亲爱的,你真的喝醉了。夫妻的爱和朋友的爱是不同的呀!
可是,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我很喜欢你同我一样爱我的朋友,却不能允许你去和他亲吻。”原本永璋前面说夫妻的爱和朋友的爱不同,可后面又说不明白为什么不允许采苕和子仪接吻。这个“不明白”表明永璋的思维并不清醒,他真的喝醉了,也就是采苕的“自我”意识不清醒,没能很好地控制“本我”产生的冲动。
除此以外,文中还有两个引人深思的问题。一个就是作者对采苕的褒贬问题。永璋的赞美可以让我们了解到采苕是一个勤于持家,美丽且厨艺很好的主妇,从文中“采苕今晚似乎不像平常那样,把永璋的话,一个个字都饮下心坎中去”一句也可看出采苕还是爱永璋的,但她却产生了如此不合情理的想法,永璋的那句“我相信一个人外表真美的,心灵也一定会美”,似乎是对采苕的讽刺。
虽然作者并没有在文中很直白的表露自己的态度,但作者并不认为采苕的行为时轻浮的。
作者通过采苕自己的口为采苕的行为进行辩护,她说:“我向来不敢对人提过这话,恐怕俗人误会。”可见,采苕对子仪的钦佩是纯洁的,不容玷污的,作者对采苕的褒贬也不言而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采苕对子仪的态度。当她终于说服了自己的丈夫同意自己的要求时,她自己却退缩了。这固然有采苕的“自我”战胜“本我”的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酒后的子仪,不过是酒后的采苕在钦佩与同情的作用下虚构出来的理想形象。当她一步步走向子仪,子仪的面庞越来越清晰时,她也意识到,先前子仪的形象不过是自己虚构的,并不是真实的。
在凌淑华女士细腻的语言中,巧妙地构思下,采苕的心理活动得到了真实的展现,“自我”与“本我”的挣扎也得以体现。但最终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凌淑华适可而止的描写了旧家庭中婉顺女性间有的出轨之作,但也是因为偶受了文酒之风的吹拂,最终也回复了她的故道。小说的情节,不过是女性生活的一个小插曲,一场小小的心灵挣扎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