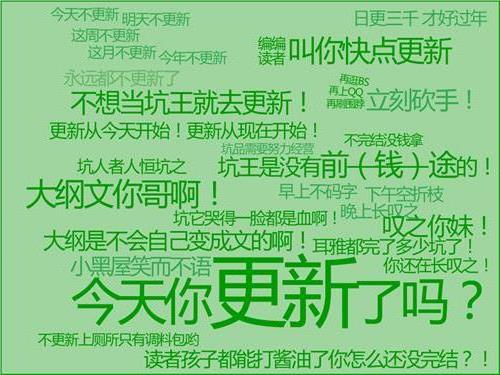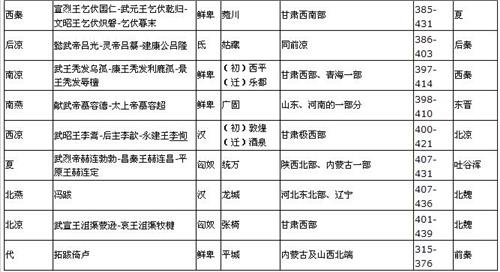凤皇 by 楼上黄昏(苻坚×慕容冲)
他知道,苻坚的援军已然到来。 而自己此刻,是退,还是进? 偷袭贵在神速,而这次百姓的骚乱已然害他错过了深入长安腹地的最佳时机。他此次所带的将士不过万人而已,骚乱之下,许是已折损大半。若这般同驻扎在长安的秦军硬碰硬对战,无异于以卵击石。
可是……可是自己在这长安周遭盘桓一载有余,从没有如此刻一般地逼近那九重宫阙。若今日退去,整个长安的防御工事必定自此加强。日后,此等天赐良机,可还会有第二次? 纵是有,上天又可还会赐给我慕容冲? 不……他不能甘心就这样退去!
念及此,慕容冲忽地打马回身,根本未曾看清面前奔驰而来的敌军,便拔出刀剑,大喝道:“不要在此多做纠缠,且随我杀入宫中去!” 众将士闻言,立即听令。
能脱身的便策马跟上,不能的,便只能被淹没于潮水一般的百姓之中。 慕容冲一马当先,飞驰着充入对方军中。手中佩剑左右挥舞,寒光凛冽之下,不断有人倒下。
而他身后的将士也紧紧地跟随着,同对方碰撞在一处,激烈地厮杀起来。 刀剑交错,铁马轰鸣。喊杀震天,龙血玄黄。 人海之中,慕容冲一眼便寻到了这支秦军的主将。 太子苻宏。 他冷笑一声,劈倒两旁纠缠的秦军,立即打马朝那处奔去。 苻宏原本处在对方将士的包围之中,此刻见慕容冲杀了过来,却也并不躲闪。飞快地拔了剑,挡住迎头的一击。 “太子殿下,好久不见了。
”慕容冲横剑在前,嘴角慢慢挑起一丝阴毒的笑容。 苻宏一提马缰,后退了几步。火光之中,他定定地看了看慕容冲那苍白却又遍布杀气的面容,却亦是慢慢笑道:“慕容冲,常言皆道‘一日夫妻百日恩’。
过去父王对你可是宠冠后宫,你如何却要对父王刀剑相向?” 然而话音刚落,慕容冲连人带剑已然逼近过来。寒光一闪直逼苻宏喉头,似有千钧之意。 苻宏原本不过随口挑衅,却未料对方反应至此。
仓皇避开这一剑,让周遭秦军立刻蜂拥上来,自己则急急退身在后。而待他打马立定之后,再看慕容冲,才发现对方的神色,比他手中的剑光更加冰冷。 一身白衣立在月色之下,即便身后是跳动的火光,周身仍是散发着冷冽的寒意。而那目光之中骤然凝聚起的怨毒,更是足以令人战栗。 苻宏迟疑之下,不由得再度退后几步,然而片刻之后,却是对左右忽然喝道:“杀!” 部下得令,齐齐涌向慕容冲。
而燕军见状,亦是簇拥过来,两军前锋再度死死纠缠成一处。而慕容冲却只是盯着暗中后退的苻宏,撇开众人,仍是独自打马跟上。 苻宏打马回身,眼见着慕容冲如利刃一般,将自己的护卫一层一层地刺穿,分明是生死不顾的决绝。
他定定地看了片刻,神色不由得沉了下去。 然后他转过身,忽地夺下了身边一名偏将的弓箭。 “太子,这……”那偏将见他不动声色地上箭,面露迟疑,“陛下可是千叮万嘱过……务必要生擒……” “无妨。
”苻宏却是淡淡打断。将箭头对准不远处左右厮杀的人,夜色之中那一袭白衣纵是沾染上了血红,仍是分外显眼。 苻坚的心思,他不是不明白。然而此刻心知,慕容冲已然无异于亡命之徒,纵是活捉了,日后许是也无法留住。 况且这你死我亡的时刻,他自由自己的考量。
脑中平静地思量着,而手中的箭看准了一个时间,猛然脱手而出! 这一箭力道极大,然而指向的目标却是异常精准。只闻“嗖”的一声,夜色掩映之下,那高坐在马匹上的白色影子,几乎是在一瞬间,便立即坠入马下。
彼处顿时一片骚乱,秦军燕军一齐簇拥上去,不辨你我。苻宏远远地看着,嘴角露出笑意,慢慢地将弓箭递回偏将手中。心知那一箭纵是未曾要了慕容冲的命,他滚下马之后,也逃不脱自己将士的乱剑了。
“把慕容冲带回来,”他偏过头,淡淡地吩咐一旁的偏将道,“无论生死。” 然而话音落下之后,他再一抬眼,却怔在原处。 慕容冲被数十名燕军护卫在身后,正翻身上了马,一扬手,已将手中的箭刺入了一名秦军的喉头。 然后他抬起眼,朝自己这边看了看,道:“太子殿下,这一箭,我慕容冲记住了。” 苻宏看着他,一时间,四肢竟是无法动弹。
难道他……竟未曾中箭?! 苻宏一时怔住,方才那一箭,他分明是有十成的把握。杀不了,也足够伤了慕容冲。然而对方此刻却仍是挥着剑,不断地抵挡着周遭的秦军,看不出任何负伤的迹象。
而正在此时,身后却响起一阵蹄音。 苻宏诧异地回头,双眼不禁霎然瞪大。然后他垂下眼,对对方一拱手,道:“父王不是坐镇宫中,如何亲自前来了?” 苻坚一身铠甲,带着一骑人马从夜色中走来。
他并未回答苻宏的话,顿住马蹄,只是抬眼朝远处看了看,道:“战况如何?”顿了顿,“慕容冲……何在?”然而话音落下之后,他的目光在火光的映照之下,显露出几分明显的异样。 苻宏心知他看到的是什么,只得顺着他的目光望去。而方一回头,却正好对上慕容冲望向自己这边的目光。 而他心知,慕容冲此刻目光落向的,必是自己身后。
“陛下,是苻坚!”与此同时,慕容身边的一名偏将也发现了苻坚的到来,“如何,可要趁势杀过去?” 然而慕容冲盯着那处许久,却在燕军的掩护下朝城门退出几步。然后回过头,对他低低道:“今日……先撤。” “撤?”那偏将闻言有些诧异,他以为如此良机,以慕容冲之性,是断然不会放过的。
抬眼看了看苻坚身后,又道,“苻坚今日只带了数人,若奋力一搏,兴许……” “撤,立即撤!”而慕容冲却忽然打断他,低低地吼道。 那偏将猛然呆住,随即只得点头道:“是!” 很快,一支号火划破天际,燕军见状,纷纷掉头朝城门奔去。苻坚见状一怔,忽然一扬马鞭,人已然追了出去。
“追!不能让他走了!” 苻宏见状只得速速传令下去追击,自己也已然跟了上去。 慕容冲在人群中飞快地奔驰着,没有丝毫停滞。留在城门内的那些燕军,大都已死在了长安百姓的啃咬之下,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他低头看了看,然而面色却始终冷峻如霜 “陛下,秦军快追上来了。”有人近身在旁道。 慕容冲略一迟疑,忽然驻马,一把夺过那人手中火把,道:“你带人先撤出!” “陛下,你……” “快!”慕容冲沉着脸,只是盯着远处。
待到人马退去大半之后,在扑闪跳动的火光之中,他看见了策马而来的苻坚。 然而他没有动,单骑立在城门口望着苻坚。二人之间隔得距离太远,看不清对方的面容,却分明知晓自己在同对方对视。 忽然慕容冲面上露出了几分笑意。他举起手中的火把,搭在弓弦上,然后拉弓如月,指向苻坚。
苻坚身侧的秦军立刻护卫过来,然而他本人却亦是立在原处一动不动。 然而片刻之后,慕容冲手中指向苻坚的火把却忽然改变了方向,竟是朝着一侧的茅屋突然射了过去。 屋顶的茅草上很快燃起了火光,连带着相连的房屋一并燃烧起来。只在片刻功夫,街上便化作一片火海。 “苻坚,你给孤一箭,孤还你一箭。如何?”抛下这句话,慕容冲在火光冲天之下转身打马而去。
白色的身影一闪而过,未作片刻停留。 周遭的秦军乱作一团救火,而苻坚却只是定定地立在远处。 他身后是无数的秦军,是冲天的火光,是十里的长安。可他却好似一个人立于空旷的长街一般。 许久之后,垂下头自嘲地笑了一声。 “终究,还是晚了一步么。” ***** 慕容冲一路一言不发,带着残余的燕军,马不停蹄地奔回阿房城中。 此时天已破晓。韩延听闻了消息,急急出来迎接。
心知此战不利,便安抚般笑道:“冲儿无事回来便好。” 慕容冲并不作理会,吩咐下去清点人数后,便径自下了马,朝自己的房中走去。 “冲儿……”韩延立在远处,低低地唤了一声,没有得到回应。
他只能一叹息,转身意欲离去。 慕容冲快步回了自己房中,然而在门边却低低地唤道:“韩延,进来。”韩延愣了愣,却也立刻跟着他进了门。
“冲儿,”他看着慕容冲慢慢地掩上了门,终是试探道,“……何事?” 而慕容冲面无表情地转过身子,抬头看了他一眼,忽然按住侧腰重重地靠向门后,然后整个人力不能支地滑了下去。
韩延大惊,赶紧冲过去扶着他靠坐在门后。拿开捂在腰间的手,掀开长袍的一角,发现腰间一侧,一片伤口已是血肉模糊。 仍有血顺着伤口流出,流过之前已然干涸痕迹流过,染上新的殷红。
半边腰腹已几乎是浸染在血中,在血迹斑斑衣衫的遮掩之下并不易看出,而此时一看却分外怵目惊心。 “冲儿,”韩延心头一紧,不由抬起头颤声道,“你这是……” “替我……替我请个大夫……”慕容冲面色惨白,连唇边也褪了色泽。
微闭着双眼,话语在断续喘息之中显得含混不清,“不可声张……此事……万不可……不可让人知晓……” 然而话音刚落,他紧紧攥着衣角的五指便忽然松开,整个人重重地栽倒在韩延怀里。
第三十二章 箭在弦上
苻宏射出的那一箭并未落空,实则伤在了慕容冲右侧腰腹。大力之下,几乎将彼处洞穿。然而慕容冲翻滚下马之后,却是借着夜色的遮掩,悄然将箭簇生生拔了出来。 然后他抬起头,便远远地看见苻坚立于月色之中,正目不转睛地看着自己。
于是他知道,无论伤口如何疼痛,血如何流,自己都不能露出半分痕迹。 毕竟他是燕军的统帅,他若倒下,必伤全军士气。然而这却并非全部的原因,更重要的是,他慕容冲绝能不容许自己在苻坚面前,显露出哪怕一丝一毫的孱弱之态。
过去在宫中的那两年里,自己在他的各种凌虐和折辱下尽失了高傲和自尊,在他的胯-下颤抖过,哭号过,哀求过,求他放过自己,甚至求他杀了自己……而那只是过去了,此时此刻的自己决然不复当年。
他要做的是高高在上地将对方踩踏于足下,又怎能容忍自己在他面前显现出半分不支来? 更何况,他心知只要自己露出分毫受伤的破绽,苻坚便定然不会放过这次机会。正如同他无论如何,也不甘愿在杀入长安城之后,那般生生地撤退出去。
可是腰腹流出的血液,无时无刻不将他周身的力道一丝丝抽走。他深知,自己无法支持太久,哪怕是多留一刻,自己便有可能生生昏倒在这里。 不,这是他决然无法容忍的。所以纵是有千万种不甘,他还是下了撤退的命令。 然后用尽最后一丝气力,一把火点燃了长安南面的长街,阻住了秦军追击的脚步。
再如何遗憾,今日也只能至此地步了。 ***** 韩延请来了大夫给慕容冲包扎好伤口,那大夫看过之后,只道伤口十分深重,虽无性命之虞,却着实需要好生静养一番。
慕容冲靠在床边,面色里仍是没有什么血色。微闭着双眼听着大夫的叮嘱,却自始至终只是沉默。 伸手慢慢地按在右侧腰间,疼痛随之散漫开来。五指缓缓上移,抚上右胸那一处跟随自己太久的旧伤。不知为何,腰腹间的疼痛,似是也随着自己五指的移动蔓延到了右胸。 这些年来,那亲手洞穿自己右胸的那一刀并未真正地退出自己生命而痊愈。
实则每逢天气寒凉的时候,右胸口便会有些隐隐作动,然而这种疼痛分明存在,却又不着痕迹,仿佛早已融入自己骨血之中,无法轻易地分离开来。 时日久了,便也已然习惯。 可是今日,右胸口却仿佛被什么堵住了一般,只觉得用力呼吸之下,竟也会连带起几分隐约的疼痛。
一个念头忽然闪过:莫非是前日收的那新伤,竟再度牵动着旧伤复发了? 五指不动声色地在按住那旧伤疤,面上却仍是平静如常。 而面前的大夫仍是滔滔不绝地叮嘱着休养事宜,慕容冲此时方才侧耳细听,半晌之后打断道:“孤何时能重回战场?” 那大夫闻言笑了起来,道:“陛下这伤……十日之后方才能下床走动,若要尽数痊愈,只怕需得半载的时日。
至于上战场……一时半会儿万不可心急。” 慕容冲听出他话中之意,只是默然颔首。实则这伤有多深重,他自己心里亦是明白。
只是……摇头轻笑了一声,只对大夫道了声“有劳了”,便将人辞退出去。 大夫推门而出。一直候在外面的韩延引着他从后门离去之后,片刻之后推开门走进了房间。
“冲儿,那大夫这一个月每日都会前来替你换药,我叮嘱过,绝不会走漏风声。”韩延走到他床边坐下,道,“这几日你便好生休养一番,待到……”然而他话未说完,慕容冲已然挣扎着慢慢地下了床。
“冲儿,你……”韩延怔住,刚欲开口阻拦,却忽地想起这一幕太过似曾相识。于是他只是自嘲地笑了一声,道,“冲儿,你就如此急不可耐么?” 慕容冲站在床边,慢慢地披上外袍,平静道:“我受伤之事,不能让苻坚知晓,便连这军中,也不可走路半分风声。
” 韩延看着他毫无神情却是惨白如纸的面容,心知这必定是由于隐忍到了极致,才会平静至此。顿了顿,叹息一声,走上前去,拿开他动作迟钝的手,替他一点一点系好了衣袋。 待到打理好衣着之后,慕容冲抬头淡淡看了他一眼,一言不发,便径自转身走出房间。
***** 便只在燕军趁夜攻入长安的数日后,秦太子苻宏便主动请缨,率领大军进攻阿房。苻坚心知那日为了救火,让慕容冲从掌中生生逃走,苻宏今日之举多少有些请罪的意思。
然而对此,实则他心内亦是惋惜无比,故应允下来,只是对方离开之际,他口中仍是那句一成不变的叮嘱:务必生擒慕容冲。 他仍能清楚地记得,那日火光之中二人,四目相对地立着。一时间,周遭俱是昏暗无声。然而他纵有千言万语,却再无法开口说出一个字,因为对方的眼中是分明的决绝与憎恨。
面对这样的眼神,自己纵是开了口,又能说什么?或许该说的话,那日小溪流边,对方已然说尽。可是自己,分明却还有太多未及开口,亦不知如何开口的心内之言。
这种感觉是凌迟在心头的一种折磨,每一次相逢,便会经历一次。苻坚已然受够。既然这一场兵戎相向已是无可避免,那么无论如何,他要胜出。唯有如此,他才能将慕容冲活生生地带到自己面前。也唯有如此,二人之间事已至此的一切一切,也才能有转桓的余地。 由是他时常立在长安城的宫阙至高处,目光扫过大火过后余下残烬的长街,最后落在不远处的骊山上。根据前线传来的在战报,他已然知晓这几日两军对阵之下,苻宏是占了上风的。
而事实上,自打苻宏出兵骊山之后,可谓是接连取胜。 一方面,燕军由于那日城中折损大半,只是被长安百姓生生咬死的,便有近两千余人。那惨绝人寰的景象,无一人能忘却。并且,据说那夜死在长安城里的燕军,都被投入大锅中煮熟分吃了。故此时此刻遇上了协助秦军的百姓,便不免心有余悸。在苻宏大军压境之下,便大有节节败退之势。 另一方面,苻坚虽然一心想着生擒慕容冲,而慕容冲却并未出战。
纵然在军中的诸事虽然仍是一如往常,然而他却也深知自己伤势过重,便不再亲自领兵,只命弟弟慕容永为大将军,带领燕军迎战苻宏。然而慕容永比不得苻宏狡猾,由是几次对战之后,竟是在苻宏手上一连折损了三万余人。 这日慕容冲如往常一般在营中巡查了一番,便回到房中。
掩上门,将身子靠了上去。伸手按住胸口,长长地吐出一口气。 醒来之后次日他便开始在军中走动,并未露出半分破绽来。他深知自打那日偷袭失败之后,军中士气便大受打击,如若他受此重伤一事为人知晓,不光苻坚会愈发步步紧逼,就连军中自身,也许亦会大受动摇。
作为主帅,他不能容许自己露出半分的孱弱来。更何况,他的对手,是苻坚。 然而伤口终究是未曾愈合的,隐痛自腰腹绵延到胸口,几乎连带着整个右侧的身体都在隐隐作痛。在军中尚能隐忍下来,可每每回到房中便变本加厉起来。 “陛下,慕容将军求见。”而这时,门外忽然传来一声奏报。
“让他进来。”伸手擦了擦前额的汗,慕容冲平复了呼吸,咬牙慢慢地站起身子,走到房中间。 可他不能对自己有任何宽容,尤其是在这接连败退的时候,万万不可有半分松懈。 因为他深知,此时此刻的自己便有如已经搭在弓弦上的箭簇,不可不发也不得不发。积蓄了太久的力道倘若有半分松动,也许他会立刻倒下也说不定。 念及此,不由得再度深吸一口气,稳住气息。而这时,慕容永已然推门而入。
“陛下。”他一进门,便叩首在慕容冲面前,“慕容永前来……请罪。” 慕容冲神色平静地立在他面前,沉默不语。自己这弟弟在败绩之下仓皇归返,其目的他怎会不知?请罪是假,求援才是真罢。
“又败了?”然而他不动声色,片刻之后,只是声音低沉地吐出几个字来。 “是……”慕容永倍感羞愧,长伏不起。
慕容冲朝前走了几步,慢慢握紧了袖中的拳。即便深知战败之过在士气而不全在慕容永,更何况自己这弟弟比起苻宏而言,终究是生涩了几分。可是这一个个“败”字落在耳中,却仿若长出倒刺一般,直教心头一阵阵抽痛。 败给苻坚。自己竟是接二连三地败给苻坚。 每一次听到战败的消息,他都恨不能立刻将这无用的弟弟杀了解恨。可是他终究是按压了下来,因为毕竟此刻的自己,仍是不能出战的。
而军中真正可信的,除了韩延,便也只有自己这同胞弟弟了。 于是他强抑住心中的怒意,面色反而变得平静异常。 “起来罢。”片刻之后,方开口淡淡道。 “谢陛下。”慕容永此番前来求援,也实是万不得已之举。
此刻见他并未发作,便索性大胆地开口道,“望陛下再给我数万人马,我定然收了苻宏那小儿!” 慕容冲闻言不置可否,只淡淡问道:“听说这数战之下,你已折损三万余人?” “是……”慕容永迟疑了片刻,道,“秦军本不足为惧,然而长安百姓彪悍异常,一见我大军,便蜂拥而上,虽手无寸铁,却……”说到此,面上不由有些变色。
“……却生生将人咬死?”慕容冲淡淡接口道。
慕容永那夜并未参与偷袭,可他却再清楚不过,那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情形。 “是……正是如此……”慕容永说到此,声音已然低了下去。纵他上过战场的次数已不下千百,可如此惨烈的情形,却着实是初次见到。 长安百姓空口咬人,满嘴是血的画面,无论何时想起,都不由得有些胆寒。 然而慕容冲闻言,面色慢慢地沉了下去,却始终不开口。
慕容永素知他心思毒辣,见他眉目间似是笼上了一层阴云,便只得噤声等待着,不敢再言。 然而这般默然许久之后,慕容冲却慢慢地挑起了嘴角,轻笑了一声,“既然这些百姓为了他们的秦王是如此的奋不顾身,那么孤又岂能不成人之美?” 慕容永闻言面露讶异,“陛下此言……何意?” 然而慕容冲却不答,只是转身走到墙上挂着的地图前,伸出指尖在上面慢慢掠过。
“骊山南侧乃是苻宏陈兵之处。孤再给你两万人马,明日一早你便率军前去骚扰,若胜不了则逼退几分,不可硬碰。”顿了顿,指尖停在一处,道,“却也决不能然他的人马越过此处。”说罢回身望向慕容永,“可以已然明白?” 慕容永虽听得清明,却到底不知此举究竟为何。
此刻不由出言问道:“不知陛下此策有何深意?” 而慕容冲闻言却垂下眼,嘴角泻出三分笑意,淡淡道:“孤自有打算。
” 他平日素来极少露出笑意,加之面色因着那不为人知的伤,本就比平日愈发苍白了几分,此刻不动神色地一挑嘴角,竟是说不出的阴郁刻毒。 慕容永忽然有些不寒而栗,他发现慕容冲的所思所想,自己从来无法看清半分。
不仅如此,每每同他立于一室,都隐约觉得有些寒气逼人 于是他也不再追问,领命之后,便匆匆离去。 慕待人走后,慕容冲慢慢地走到椅子边坐下。面上本就不分明的那一缕笑容,此刻慢慢地也荡然无存。深吸了一口气,他微微扬声,唤来了一名偏将。 “即刻点一万精兵待命,孤……明日出城。”
第三十三章 孤注一掷
“陛下,城外忽然涌来大量流民!”一名将士匆匆步入,跪倒在苻坚面前。 苻坚闻言面露诧异之色,却不及多问,只是即刻带着人上了城头。 时近夏日,烈日当空。苻坚立于高城之上,在刺目的骄阳之下微微眯起眼,俯瞰着城下。
只见城下已然聚集了不可计数的流民,他们有如水道一般,蜿蜒盘旋着自远处不断地涌来。 终点是这长安城,而源头,却是骊山。 苻坚不由得皱起眉,抬起眼朝远处望去。然后在炽日炎炎之下,他这才看清,偌大的骊山,乍看之下,竟是笼罩在一片风烟之中。
在凝眸细看,便可见山间燃起的星点火光,便已然隐约可见。 “怎么回事?”苻坚转过身子,问一旁的将士。 “回陛下,下官不知,”那将士略一迟疑道,“前几日派出去打探的队伍……无一人回来。” “竟有此事?”苻坚再度抬眼,望向那烟尘四起的山间。
然而及至问出口时,他深知其实自己心内便已然有了答案。 除此之外,还会有何人? “陛下,这些流民该如何处置?”一旁的将士见他沉吟许久并不言语,便试探着开口问道。 “自然是让他们进城!
”苻坚回过神来,斩钉截铁道,“速速打开城门!” “可是陛下,城中的粮草只怕……”将士迟疑了片刻,犹豫道。
“即刻开城门!”苻坚却没有一丝犹豫,果断出言打断道。 “是!”那将士只得领命,匆匆地下去了。 而那将士方下去,伴随着急急促的脚步,一名宫人的声音便在身后响起,“陛下,太子遣人送回的战报。” 苻坚立刻接过三两下展开,然而及至目光扫过其上最后一行字迹之后,他面色一点一点地变得阴沉,握在布帛边沿的五指却是一点一点地握紧。
许久之后,他忽然松开了手,对那宫人道:“告诉太子,若撑不下去了,便回城罢。” 宫人得令,亦是转身离开。城头霎然只剩下苻坚一人立在城头的骄阳里,定定地盯着远方。墙头风大,吹得他的袍角猎猎作响,分明是烈日炎炎的天气,而他的心却忽然觉得倍感寒凉。
苻宏带走的人,原是城中最为精锐的人马。他将所有的赌注都压在这里,只愿能尽快地结束这场战乱,至少是结束长安这燃眉的危机,也尽快在他和慕容冲之间做一个了结。
他自视秦军精锐之师,又享有地形之利,击溃慕容冲应是势在必得的。事实上,战事之初,苻宏不负他所望,连胜之下,传回的皆是捷报。 可是他未曾想到的是,慕容冲在窘境之下,竟会走出一步他如何也未曾想过的棋——带人在骊山一带游走,见人便杀,见村便烧。 据苻宏在战报中之言,此刻骊山一带腥膻遍野,横尸满地。
长安周遭的百姓,不是死于屠刀之下,便是携家带口地奔长安而来。由是整座骊山上下,竟是百里绝无人烟。 而他被慕容永困在南麓数日,纠缠骚扰之后,方才知晓此事。而大肆劫掠之下,燕军满载而归,秦军却是再没了后勤补给。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此时情形可谓已然倒置,他只得在战报之中征询苻坚,究竟是该坚守还是退兵。 听闻一阵喧嚣,苻坚不由垂眼望向城下。城门已然开启,等待了太久的百姓如洪流一般迫不及待地涌入城中。
苻坚定定地看着,脑中却浮现出骊山之上可能的惨状。苻宏战报之中不过的寥寥数语,而彼处的狼藉,却仿若历历在目地出现在他的眼前。 慕容冲的变化,十年之后他已然亲眼见过,可是他万万不曾想到的是,他竟能决绝至此。
只因为他恨自己,便要将和自己有关的一切,都尽数毁灭么?还是说,为了将自己逼至山穷水尽,其他的一切他都可以浑然不顾? 可是死在他刀下的这些人,不过是手无寸铁的百姓而已。他究竟有多无法释怀,才能下狠手至如此地步? 苻坚慢慢地闭了眼,只听见城下的喧嚣声在风中慢慢地飘入耳中。
他知道,自己绝无法对这些流民弃之不顾,即便城中已然数月唯有降雨,一场大旱许是近在眼前,即便苻宏败退之后,前路如何自己亦是未有考量…… 可是他不能。不只是由于他们都是自己的臣民,也不紧紧是因为他亲眼见到过他们为了维护自己而啃咬燕军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