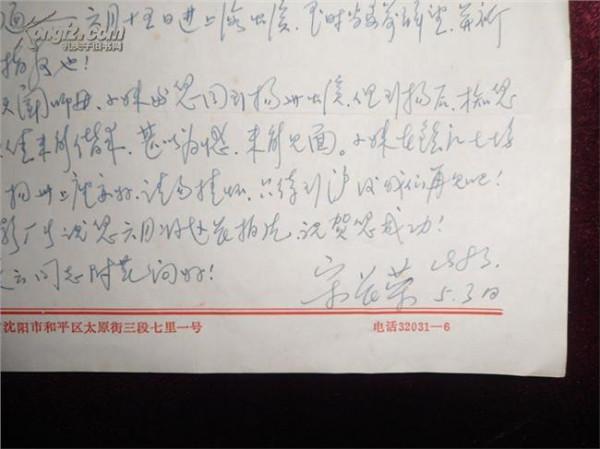童芷苓的红娘 最后的风流——童芷苓及四大皇后
童芷苓是跑过江湖的艺人,风里走,雨里行,自然和李玉茹这样的科班学生、言慧珠这样的摩登小姐不同,黄裳不喜欢她,说她有股极恶劣的风尘气。台上不严肃,倒是这股风尘气,使她演起《大劈棺》、《纺棉花》来,格外传神,有时候还能来个彩旦。
据老戏迷回忆,40年代,童芷苓大红大紫的时候,经常因应酬误场,忘词也是家常便饭,唱《铁弓缘》,一开口却是“青春整二八,生长在贫家。”不过她台缘极好,捂着嘴一乐,台上台下笑成一片,一场舞台事故就这样过去了。
顾正秋回忆录里,说当年戏院约《八五花洞》,一边是童芷苓等四个名角,一边是她们几个戏校刚毕业的学生,顾正秋们自知名气不如,就认真排练,演出时,童芷苓又误场了,台下观众起哄,童一点也不在乎。
台上,戏校学生的四个潘金莲的手势、眼神、台步完全一样,台下立刻掌声如雷,把名角们压下去了,童芷苓回到后头,把扇子一扔,“姑奶奶不唱了。”顾正秋很羡慕她这种大腕派头。 当年她和言慧珠、吴素秋、李玉茹并称四大皇后。
这四人年纪相仿,戏路相近,色艺双绝,是坤旦艺术的代表人物。她们虽然是四大名旦的学生,但基本完成了旦角艺术的女性化(四大坤旦即雪艳琴、新艳秋一辈还带有较重的男旦痕迹),表演清新美丽、大方自然。
言慧珠专工梅派青衣花衫,在戏路上是继承梅兰芳最全面的学生。但也能演《得意缘》、《战宛城》这样的花旦戏和《扈家庄》这样的武旦戏。据说也演过《大劈棺》。当年她和童芷苓打对台时,童芷苓祭出“劈纺”这两出票房法宝,因这两出戏带点“粉戏”色彩,王瑶卿对自己的弟子下了戒严令“王门弟子不许演纺棉花”,言慧珠就别出新裁,搞了一出《戏迷小姐》,也是南腔北调,各显其能。
吴素秋和李玉茹是同学,同是中华戏校“玉字科”的学生,吴素秋没出科就自己跑码头去了,拜尚小云学荀慧生,四大皇后中她红得最早,“劈纺”二剧也是她最先演红的。
她大红大紫的时候,童芷苓才暂露头角,雄心万丈的童芷苓就敢和她打对台(童就是一部对台史,除了自己的老师四大名旦,基本是神挡杀神,佛挡灭佛)。
不过才二三年,吴素秋就激流勇退,结婚息影了。 李玉茹是科里红,“四块玉”之一,青衣花旦两门抱,青衣从程砚秋的二旦吴富琴学程派(程砚秋是中华戏校的校董,中华戏校的旦角们几乎都会哼几句程腔),花旦戏得芙蓉草、何佩华(先后为荀慧生的二旦)真传,并得荀慧生本人亲授,有“小荀慧生”之称,后来长期傍周信芳。
50年代,吴素秋复出来北京四团,但此时的北京剧坛,已经是张君秋、杜近芳、赵燕侠三足鼎立,吴虽风韵犹存,但总不能得现昔日光辉。
李玉茹、童芷苓、言慧珠先后“公私合营”,参加了上海京剧院,李玉茹“参加革命”最早,童芷苓次之,而那个“资产阶级小姐”言慧珠最晚,因此三人的工资也是三级跳,谁说“革命不分先后的”?(引章诒和语)。
当时的上海京剧院一窝旦,言慧珠没戏演,在报纸上呼吁“我要演戏”,结果被当个人主义的耙子批判,出走北京,加入过吴素秋所在的四团,二人交恶。
回上海后心灰意冷,干脆去上海戏校唱昆曲去了。 李玉茹、童芷苓都是荀派兼演别派,戏路重复,这要是在挑班时代,大家大可百花齐放,现在不行了,各人有各人的戏,否则就是没有集体主义观念。言慧珠走了之后,上海京剧院实在缺个叫得响的青衣,李玉茹干脆拾起她在中华戏校时学的程派,最有名的是《梅妃》了。
文革之后,言慧珠香销玉埙,李玉茹、吴素秋力图复出,无奈物是人非,风华不在;童芷苓倒是迎来了第二春,剧院不是让我给青年演员让戏吗?好,我让!
我到别处演出,带着自己的班子全国巡演,闯出一番新天地(四五十年代的名旦中,能成功复出也只有她和赵燕侠二人矣),应该在说在这一时期,她的戏已入化境,对比一下她和吴素秋此时留下的《铁弓缘》和《乌龙院》,明显高出后者。
和李玉茹相比,论花旦戏,李玉茹规矩,童芷苓出彩,童似稍高一筹。 四人之中,除了言慧珠,其余三人,戏路相近,都是荀派本工,青衣花旦刀马兼演,四大名旦一脚踢。
非要在青衣、花旦上分出个比例来,李玉茹五五开,吴素秋四六开,童芷苓三七开吧。也就是说李玉茹偏青衣,吴素秋近花衫,童芷苓则重花旦。 现在除了吴素秋,其他三人业已作古,她们是京剧坤伶最后的风流,建国后的名旦,无论是杜近芳、还是赵燕侠,抑或关素霜,虽然功力非凡,但总觉得“革命劳动妇女”气质太重,缺少那一种风流蕴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