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歌主持的节目 女主持人田歌的生存法则
评论家张颐武说,这个节目“给普通人过节的感觉”。
类似于这期《喝酒的人》,《荧屏连着我和你》在16年中讨论了近千个时代话题,约10万人走进了节目。他们中有下岗职工、空巢老人、作家、小保姆、出租车司机、修脚工、剃头师傅、修自行车的人、居委会大妈、看门的老大爷、外来务工人员、艾滋病患者、流浪孤儿、捡垃圾的人……所有的观众都觉得,下一个节目的主角应该就是自己。
但是,已经没有下一个。死的理由实际上,撤掉《荧屏连着我和你》的决定,在2006年底前就做出了。这两年的中国电视荧屏,是一个选秀乱舞的年头。你选好男儿,我选好女儿,他弄“绝对唱响”,51个上星频道,竟然出现了53个选秀栏目。
在湖南卫视、东方卫视之后,田歌所在的北京电视台,决定向“娱乐第三大台”迈进。他们请了李湘、刘仪伟、杨澜等大腕主持加盟,推出《红楼梦中人》、《龙的传人》选秀,同时,对内部栏目进行整顿。“砍掉”连续十几年都排在收视前十名的《荧屏连着我和你》,似乎表达了上层的改版决心。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北京电视台资深编导说:“栏目时间长了就是老化?我看不一定,外国谈话节目几十年不变的很多。”他说,电视在中国有特殊的“国情”,国内的电视台换一个领导,就要重生一批“孩子”,“有了后妈,就不认你这个孩子了。”
田歌本人对此不愿多言。节目刚被撤的那段日子,她在接受《青年周末》采访时,曾表达了自己的担心,“怕别人想会不会因为是人际关系的原因才被撤的呀?”
其实,节目坚持16年的同时,她始终处于非议中——她靠的到底是谁?
有丈夫尤小刚的时候说她靠的是丈夫,离婚后,她成了中国第一个既当导演又当主持、制片人的女人,外界就说她为了忘记失败的婚姻,争强好胜。
对节目的突然“死亡”,曾任节目组策划人的乔卫感受复杂,他不愿言及电视台内部复杂的人际关系或者潜规则,更愿意理解成“文化势力对栏目的压迫”。他说,这是过分的娱乐化倾向对正常电视形态的压迫,“个人很难阻挡那个文化潮流”。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喻国明,曾为节目撰文,盛赞其“每一句话、每一个细节就是最好的评论”。
作为关注媒体改革的前沿学者,他与主导此次改革的北京电视台高层保持着密切联系。他认为,北京台当时处于整体风格的转型时期,对某些节目也被迫忍痛割爱,“任何改革者都需要这样做。”
对于外界某种“潜规则”的猜测,他坦承“整个电视台就是一名利场,不是某个人怎么样的问题”。
不理解之余,田歌的内心隐隐有点解放的快感。16年了,一个女人与一档节目的马拉松“恋爱”,终于结束了。
花瓶,或者“发球型”
从1990年开始,《荧屏连着我和你》在16年中经历了三个最重要的转型:开创时期的谈话加文艺表演,第一次让名人与普通人面对面;随后变成板块式的电视杂志,每期50分钟,比《东方时空》还早一年;最后变为彻底的谈话节目,瞄准平民,基本不再做明星访谈,而央视推出的平民类谈话节目《实话实说》,已经是1996年3月的事情了。
每一次转型,每一个“第一次”,都让这个节目具备了标本式的价值。
“那时候,国内的谈话节目还在草创阶段,我们也在摸索,逐渐确立了关注平民的价值趋向。”田歌当时的同事乔卫,现在已经是国际广播电台普通话节目的副总监,他从1995年到2003年是节目的主力策划之一。“这个平民趋向不是刚开始就被大家接受,但随着民众思想与表达欲望的急速生长,节目风格也很快得到承认。”
与央视《生活空间》、《实话实说》等节目一道,电视人开始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从早期“官兵们纷纷表示”、“专家们一致认为”,到“我认为”、“我觉得”,抽象一致的群体性声音逐步被个体性的言说代替了,《荧屏连着我和你》等借着新的媒体形式,提供了平民表达个人观点的话语空间。
著名编剧史航,去年参与过100多场电视谈话节目的录制。让他不爽的是,嘉宾有时变成了编导手中的一颗肆意摆设的棋子,他曾数次遇到这样的编导,对他说:“史老师,你就是这一派的,持反对意见的。”
史航认为,目前谈话节目的“小煤窑倾向”很严重。“主持人不专业,很大的一个话题资源与嘉宾资源就被浪费了。就比如小煤窑,那么好的煤层,它挖几下就不挖了。”
对比田歌,文化人司马南认为目前很多谈话节目主持人是“发球型”主持人:“编导给他写十几个问题,他一条条照念。就像只管发球、却不会接球的乒乓运动员,节目要靠后期一针一针编出来,掌声也是接上去的,所以节目像塑料花一样没生气,味同嚼蜡。当然,只指责主持人是不公正的,问题的症结在领导者的判断力。”
在喻国明看来,田歌的主持人、制片人一体的状态,使她获得了比其他主持人更大的创作空间,“作为电视人,她已经很幸福了。”
但田歌没有觉得自己幸福。在接受上海一家媒体采访的时候,田歌曾给充斥荧屏的选秀热浇了一盆冷水。她说,选秀节目的好坏成了一个电视台领导业绩的考核标准,这是很可怕的。“满荧屏的选秀,我想知道这些电视人的创新精神在哪儿?他们的创作尊严又在哪儿?”
“我一直觉得在出丑”
“每次播出节目,我都感觉自己在露丑。”田歌说。几年前,就有很多电视研究者开始将她和她的节目作为研究对象,但没有人触及她内心的自我冲突,甚至分裂。
对电视这个职业,她内心充满了极度的爱,同时还有极度的恨。
“爱这个职业,因为它让我在这样的年纪,观念也不落伍,甚至思维比很多年轻人还要前沿。我恨电视,因为本质上它是快捷的、粗糙的、大众的,而我追求的是经典。”作为创作人,她导演的《美在广西》曾经获得帕·萨撒国际电影电视奖等国际奖项,现在已经作为国内传媒院校教材的典型案例。
但这样的创作机会,在电视台太少了。每周一期的节目,她都感觉是在制造垃圾。虽然现场的她,每次主持都笑如夏花,实际上每次录制她都紧张,内心有个声音说:我又在露丑。
她一再说,真正的困惑是:创作生命有限,自己却在用有限的生命制造垃圾。
压迫她的根源,还是那令不少人诅咒的收视率,虽然表面看来,她的节目收视率一直没让她担心过。“我不能拖台里收视率的后腿。但如果一味地迎合收视率,节目将无可避免地走向低俗,你做暴力型的节目,收视率能不高吗?所有电视台的领导都在关注收视率,它的真伪先不说, 这个冰冷的数字真的那么有价值吗?”
她曾经觉得幸运,她与很多主持人面对的时代,是一个社会急剧转型的时代,很适合做这行。但最终发现,“这一行有那么多的紧箍咒”。更多的人选择了妥协。田歌说,她不知道该怎么办?
记者追问田歌,你的主持生命还能坚持多少年?
“如果按照国内这种媒体价值观,也许我之后没什么生命力了。但你看国外,哪有年轻人在主持新闻或者访谈节目?”
几乎跟她同龄的主持人倪萍,从《综艺大观》退出后,重新回归影视表演行当。而《综艺大观》陪伴中国观众13年后,也于2003年彻底谢场。
很多人最早认识田歌,也是从她做演员开始的,曾出演吴子牛的处女作《候补队员》。但田歌不想像倪萍那样,再去做一个演技派的演员。她说,她的创作意识强过她的表演意识,即使不主持了,她也会选择专心做导演。
而导演,只要你在这个行业,同样难以逃避收视率的困扰。
“喝酒的人”之哀叹
《光荣绽放》最近几期的收视率不错,黄晓明、陈好、邓超等一系列明星相继来做客,在业界被喻为收视低潮的“黑色星期二”,到了《光荣绽放》这里却成为了“红色星期二”。领导开始表扬节目“包装很美,舞台很漂亮”,还开玩笑说“收视率别太高了啊!”
同时,对她的质疑也马上来了。在一篇题为《田歌转型,福兮祸兮?》的批评文章中,作者批评《光荣绽放》“本质上还看不到创新的迹象”,并担心她随波逐流,“被表面娱乐淹没”。
田歌承认,做《光荣绽放》对她来说确实是一种妥协,之前她策划的一档定位更人文的节目被毙掉了。她心里也明白,目前的高收视率多少有点沾明星嘉宾的光。她还是试图坚持,不想把节目做成明星影视剧的剧情介绍。
她质疑前来做客的导演高希希:“你一年导演那么多作品,到底几个是亲生的?”
艺人苗圃到节目组带来了自己新制作的单曲,田歌听了,不仅没有夸奖,还坦言:“你的歌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
她试图揭示真正的问题,同时又担心,这样做观众是不是喜欢?
她打消不掉内心的平民情结。在《光荣绽放》的栏目定位中,“平民情怀”赫然在其中。她悄悄打了一个伏笔。她内心里,盼望有一天,普通人也能在她的新节目中“光荣绽放”。纵然,这让她再次顶着“节目定位不准”的压力。
多年前的那位“喝酒的人”,还惦记着田歌,还惦记着那个平民节目能再回来。“真的忘不掉您,现在电视连续剧那么多,为什么《喝酒的人》,就没有个续集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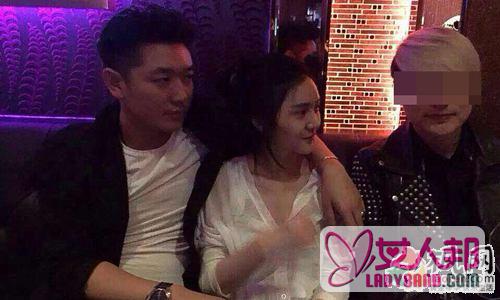

![美食节目孙夏 [坛蜜美食节目]美食节目女主持人孙夏](https://pic.bilezu.com/upload/0/6f/06f79185a71c18b24fa114c30efb30cc_thumb.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