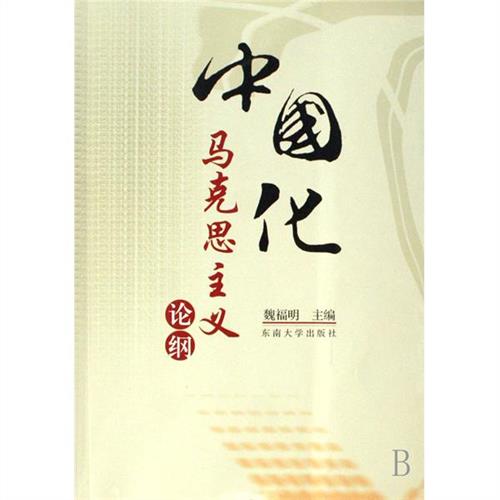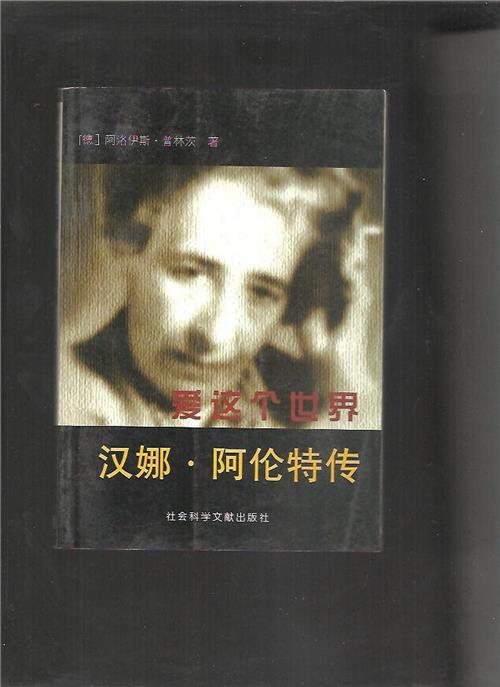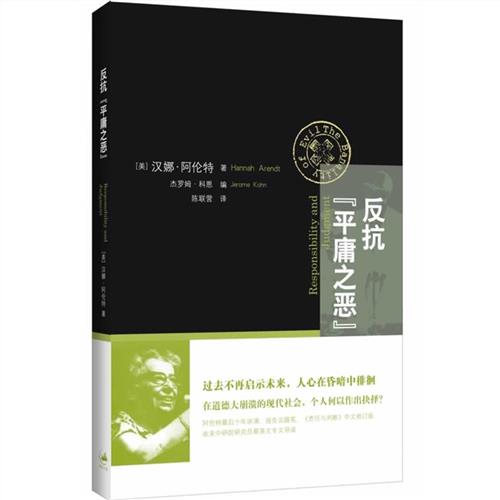阿伦特艾希曼 汉娜·阿伦特: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份关于平庸
一个看上去要复杂得多,但实际上比探究无思想性与恶之间那种奇怪的相互依存关系要简单得多的一个问题是,这里所讨论的究竟是什么样一种罪――既然所有人都同意这是一种没有先例的罪。种族灭绝曾被拿来专门指称一种前所未知的罪,但这个概念也只是在某种程度上适用,原因很简单,对整个民族的屠杀并不是没有先例的。
在古代,种族屠杀干脆就是社会法则;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几个世纪中,种族屠杀的例子同样层出不穷,尽管并非每次都同样成功。
也是还是用“行政性屠杀(administrative massacres)”比较适合。这个词是伴随着英国的帝国主义出现的;英国人坚决拒绝用这种方法来维持对印度的统治。这个词的妙处在于它排除了这样一种偏见,即这种残暴的行为只适用于对付外国或异族。
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希特勒在开始实施集体屠杀时,打的旗号是对“患有不治之症者”实施“安乐死”,而为了加速他的灭绝计划,他甚至不惜处死那些“患有遗传性疾病”的德国人(心脏病和肺病病人)。
但事情并不到此为止,很显然,屠杀可以是针对任何一个特定的集体的,也就是说,只不过选择的原则会因不同情况而发生变化罢了。不难想象,不远的将来,随着自动化经济的实现,人们没准儿会试图将智商在某个水平线以下的人全部清除掉。
因为法理上确实很难把握,所以在耶路撒冷,这个问题没有能够得到充分的讨论。我们曾听到辩护方的抗议,说艾希曼只不过是最后解决这部机器上的一个“小齿轮”而已,我们也听到公诉方说,他们已经在艾希曼身上发现了那部运转着的发动机。
我本人并不比耶路撒冷法院更看重这两种理论,因为既然整个“齿轮”理论在法律上毫无意义,那么艾希曼这个“齿轮”的尺寸大小也就无关紧要了。
在判决书中,法院承认此种犯罪,只有一个庞大的官僚体制通过运用政府资源才能够实施。但是既然是犯罪――当然,犯罪是审判的前提――那么,这部机器上的所有齿轮,不管其作用大小,在法庭上马上就变成了罪犯,也就是说,都要还原成人。
如果被告为了开脱罪责说,他并不是作为一个“人”,而仅仅是因为职务要求才犯罪的,任何人在这个位置上都会这么做的。这就好比一个罪犯指着犯罪统计表――该统计表显示,在这样那样的地方,每天都差不多会有这么多人犯罪――说,他不过是做了统计表所预期的事情罢了,换言之,既然总得有人犯罪,那么只不过碰巧是他而不是别人罢了。
当然,对政治学和社会学来说,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极权政府的本质,抑或还有科层制的特点,正在于把人非人化,使之完全变成一个个的职员,变成行政机器上的齿轮。
当然,对“无人统治”(the rule of Nobody)――它被认为是作为一种政治形式的科层制的本质――还可以作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但有一点必须清楚,在司法实践中,这些因素都只能作为犯罪的外因在一定程度上予以考虑――就像在一个盗窃案中,经济上的窘迫固然要酌情考虑,但决不能成为盗窃的理由,更不用说免予起诉了。
的确,由于现代心理学和社会学,更不用说现代科层制,我们已经非常习惯于用这样或那样的决定论来为某人的行为开脱责任。
尽管这些貌似高深莫测的对人类行为的解释对错与否还众说纷纭,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没有哪种司法活动能够以这样的理论为基础;以这些理论为标准的司法制度,不仅是过时的,更是完全反现代的。
希特勒曾经说过,总有一天,在德国人们会以当一名“法学家”为耻。在其雄辩的言辞背后,希特勒所要表达的正是他那个美仑美奂的科层制之梦。
据我所知,能够用来处理这一系列问题的法学范畴只有两个,即“国家行为”和“服从上级命令的行为”,而在我看来,这两个范畴并不完全适用。无论如何,在此类审判中,这些范畴常常是由于被告方的请求,才被讨论的。
国家行为理论基于这样一个命题,即一个主权国家不能审判另一个主权国家,par in parem non habet jurisdictionem 。从实践层面上讲,这个命题在纽伦堡就已经被否定了;这个命题从一开始就站不住脚,因为如果接受这一命题的话,那么连希特勒,这个唯一一个无论如何都必须被追究责任的人,也无须惩罚了――果真如此的话,就连最基本的正义都无法保障了。
然而,在实践中很难站住脚的命题在理论上却并不必然会被否弃。
最常见的遁词――第三帝国是由一群罪犯统治的,对他们来说,既谈不上什么主权,也谈不上什么公平――几乎没有任何说服力。一方面,谁都知道,罪犯之类的比附,只在特定的范围内适用,用在此处显然不妥,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的是,所有这些罪都是在“法制”秩序中发生的。
这正是这些罪最显著的特征。 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在国家行为理论背后,还有国家利益理论(raison d’etat)的话,我们对问题的理解或许能更进一步。
按照国家利益理论,国家的主要职责是维系国家的生存、保障法律的运行,但国家行为和该国公民的行为所遵守的规则却并不一定相同。拿法律规则来说,它由全体制定,并且适用于全体,其目的是削除暴力和战争,然而它自己却需要暴力机器来维持自己的存在。
同样,一个政府也会发现,它自己不得不通过一些在通常意义上被认为是犯罪的措施来确保自己和法律的存在。战争正是常常以这样的理由被合法化的,然而国家犯罪行为并不只是存在于国际关系的领域之中,文明国家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许多例证:从拿破仑处死笛昂大公,到暗杀社会主义领导人马提奥第 ――一般认为墨索里尼应该为此事负责。
国家利益理论――对错与否要视情况而定――强调的是一种必要性:以国家名义实施的犯罪(即使按照该国占统治地位的法律,也是不折不扣的犯罪)被视为是紧急措施,是对现实政治中的严峻形势做出的让步,目的是维护权力,以确保现存法律秩序作为一个整体能够运行下去。
在一个正常的政治和法律体系中,此种犯罪不受规则约束,也不受法律的惩罚(用德语来说,是免于起诉的[gerichtsfrei]),因为当一个国家的生存受到威胁时,没有哪个外部的政治实体有权否定它的存在,抑或为它开出一副保存自己的灵丹妙药。
然而――正如我们在第三帝国的犹太政策史中看到的那样――在一个建立于犯罪原则上的国家,情况正好相反。在那里,无罪的行为(比如,1944年夏末,希姆勒下令停止驱逐犹太人)倒变成了对现实必要性――这里指的是即将战败――的让步。
这样,问题出来了:对这样一个政治实体来说,其主权有何特征?难道它不曾破坏“地位平等者之间相互无管辖权”的原则?难道同主权相比,“地位平等”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摆设?抑或二者在本质上是平等或相似的?难道我们可以把完全相同的一条原则,既适用于将犯罪和暴力视为例外和边缘事件的统治机构,又适用于将犯罪合法化和章程化的政治秩序? 如果说现有的法学概念在处理这些审判中一些关键的犯罪事实时已经勉为其难了,那么,在处理“执行上级命令的行为”时,问题就更为突出了。
为了反驳辩护方的意见,耶路撒冷法庭不厌其烦地从文明国家,尤其德国的刑法典和军事法典中引经据典;在希特勒统治时期,相关法律并没有被废除。
所有这些法律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决不能服从明显是犯罪的命令。不仅如此,法庭还例举了几年前在以色列发生的一件事:一些士兵因为屠杀了边境线上一个阿拉伯村庄中的平民百姓,被带上了法庭。
事情发生在西奈战役前不久,这些村民被发现在军事宵禁期间走出了他们的房屋,但事实表明,他们对宵禁一无所知。遗憾的是,如果仔细分析这种比较的话,就会发现它在两个方面是有问题的。
首先,我们必须再一次注意:例外和原则的关系――这对于判断下属执行的命令是否构成犯罪至关重要――在艾希曼的行为中被颠倒了。按照例外和原则的推论,艾希曼没有服从希姆勒的某些命令,或者即使服从了、却非常犹豫的行为确实可以得到辩护:因为这些命令明显是普遍原则的例外。
然而法官们却认为这些行为尤其是艾希曼的罪行所在,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在逻辑上却出现了不一致。这在以色列军事法庭的法官们所援引的相关裁决中可以清楚地看出。
这些裁决认为:拒绝服从的命令必须是“明显不合法的”;“不合法”,“作为写着‘禁止’的警示,应该像一面黑旗那样飘扬在(它的)上空。”换言之,被士兵认为是“明显不合法”的命令,一定是通过一种反常的形式违背了他已经习以为常的法律制度。
在这些问题上,以色列法律和其它国家是完全一致的。毋庸置疑,在制定这些条款时,立法者一定预想到了诸如此类的情况:一个军官突然发疯了,并命令其手下杀死另一名军官。
如果真的发生了这样的案件,那么通常的审判都会很快得出结论:这个士兵没有听从良心的召唤,没有听从“每个人内心深处都会有的对合法性的感知的召唤,也没有听从那些对法律条文并不熟悉的人的召唤……只要他眼睛不瞎,不是铁石心肠,良心还没有完全堕落。
”进一步讲,人们希望这个士兵能够在规则和明显违反规则的例外之间做出区分。至少,德国的军事法明确认为,只有良知是不够的。第48节写道:“个人的良知或宗教戒律,不能成为其行为是否应受惩处的理由。
”以色列法律所遵循的逻辑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即每个人内心深处的正义感,都只不过是他对法律熟悉程度的一个反映。这个推论的前提是,法律所传达的也正是良知对人们的劝谕。
如果我们在严格意义上将上述整个推理适用于艾希曼案,那么我们不得不说,艾希曼的行为根本没有超出被要求的判断框架:他依照规则行事,依据“明显的”合法性亦即常规来检验施加于他的命令;他完全不必诉诸于自己的“良知”,因为他并非不熟悉自己国家的法律。
于是,事情正好走向了它的反面。 前述类比的第二个缺陷与司法实践有关:在司法实践中,“执行上级命令”往往被视为减免罪责的理由,这在判决书中也明确地提到了。判决书引用了我刚才提到的那个案例,即发生在卡法?卡萨姆的屠杀阿拉伯人事件,用以证明以色列司法机关决不会因为“执行上级命令”而免除被告的责任。
的确,这些以色列士兵被控杀人,但是“执行上级命令”构成了强有力的从轻理由,所以他们只是被判处了相对而言非常短期的监禁。
确实,这个案件所处理的是一个仅此一次的行为,而不是――比如艾希曼案中――长达数年之久、一次接一次的累犯。尽管如此,既然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艾希曼一直是在执行“上级命令”,那么按照一般的以色列法律,就很难对他处以极刑。
问题的关键在于,和其它国家一样,以色列的法律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不得不承认,即使是“明显”不合法的“上级命令”,也会严重影响一个人的良知活动。
这只是众多例子中的一个,但也足以表明,现行法律制度以及司法概念在处理由国家机器组织的行政性屠杀时,是多么地捉襟见肘。如果作更深入的研究的话,那么我们将不难发现,在所有这些审判中,法官们仅仅是依据行为的残暴来实施判决的。
换言之,他们的判决完全是想当然,并没有真正依据或多或少能让他们的判决更有说服力的准则或法律先例。这一点在纽伦堡就已经非常清楚了,当时,法官一方面宣称“反和平罪”是他们所要处理的所有罪中最严重的,因为它包含了所有其它罪,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却只是对那些参预了最新的一种犯罪,即行政性屠杀的人处以了死刑――按照他们的说法,这是一种比反和平罪轻的罪。
在一致性如此不可或缺的法学领域中追究这样或那样的不一致,想必是一件很有吸引力的事情。
但这显然是本书力所不及的。 然而,必须指出,还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没有解决。在所有的战后审判中,这个问题都隐约出现过,而且这个问题关乎各个时代最核心的道德问题,也就是说,关乎人类判断力的性质和功用问题。
在这些审判――这意味着,被告犯了“法”――中,我们有一个诉求:人类可以明辨是非,即使是当他们只能指望自己的判断力、甚至当他们的判断力与周围所有人公信的判断完全相左的时候,也是如此。
正如我们所知,当少数“高傲自大的”人坚信他们的判断与那些信守旧的价值标准或者恪守某种宗教信念的人截然不同时,问题将变得更为严重。既然一个高尚的社会全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臣服于希特勒了,那么可以说,那些曾经用以规范社会行为的道德信念、那条用以引导良知的宗教戒律――“毋杀戮!
”,全都被否弃了。尚能明辨是非的少数人只能依靠自己的判断力,此外便别无依凭;没有任何规则可资借用,以应对他们所面临的绝无仅有的情境。
面对随时出现的所有问题,他们必须自行作出判断,因为对于没有先例的事情来说,不可能有规则存在。 上述判断问题(或者,换一个更通常的说法,那些胆敢“高坐于审判席”者)究竟给现时代的人带来了怎样的困惑,从围绕本书、以及在很多方面都非常相似的围绕霍赫夫斯的《代理人》所展开的论战中即可见一斑。
出乎某些人的预料,(论战)呈现出来的既非虚无主义,也非犬儒主义,而是在基本道德问题上的异常混乱――正如我们的时代,一旦涉及此类问题,最后便只能靠直觉来作想当然的处理。
论战中出现的一些离奇的观点似乎尤其发人深省。比如,美国的一些学者表达了他们天真的信念:诱惑和强迫实际上是一回事,没有人能够抵御诱惑。
(如果有人用手枪抵住你的脑袋逼迫你向你最好的朋友开枪,你肯定会开枪的。同样,正如人们所说――几年前曾经有过一次丑闻,一个大学老师在一次智力竞赛节目中作弊欺骗了公众――当这么多钱放在面前时,谁能抵挡住它的诱惑呢?)其中包含了这样一个推论:不在现场且不是当事人者,无权评判。
看起来这一推论适用于任何场合下的任何人,尽管果真如此的话,那么显而易见的是,司法审判和历史书定都将变得不可能。
与这些混乱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对司法人员的明哲保身的谴责却由来已久;尽管这种谴责完全与事无补。即使是一个刚刚惩处了一个杀人犯的法官,回到家里后,依然可以说:“没错,但是上帝保佑,我才那么做的。
”所有的德国犹太人都异口同声地谴责1933年德国人对纳粹的妥协,认为正是这种妥协使得犹太人一觉醒来便沦为了贱民。难道他们中间从来没有一个人扪心自问:在同样条件下,他们中间有多少人会做出同样的选择?但是他们的谴责声不是至今仍丝毫不减其正当性吗? 自己在同样的情形下也可能会做出恶行来,这种反思可能有助于产生一种宽恕精神,但是将这种宽恕精神与基督教之宽容联系起来的人,似乎又奇怪地将问题搞乱了。
不妨读一读德国福音教派,即新教教会在战后发表的申明:“我们在仁慈的上帝面前坦白,我们的国民对犹太人犯下了令人发指的暴行,由于不作为和沉默,我们理应和他们一起分担罪责。
” 在我看来,如果一个基督徒以恶报恶,那么就可以说他在仁慈的上帝面前是有罪的,同样,如果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是因为他们犯下的某些恶而被杀,以示对他们的惩罚的话,那么仅此就可以说教会在仁慈的上帝(God of Mercy)面前是有罪的。
但是如果诚如教会所坦白的那样,他们参预的是一桩纯粹的、没有理由的暴行,那么问题便仍需在正义之上帝(God of Justice)的领域内被考量。
如果有人认为这是一个笔误的话,那么它是有意为之的。正义而非仁慈,才是审判的关键。
现在,所到之处,公共舆论似乎无不欢欣鼓舞于空前的一致,甚至远非在“谁也无权审判他人”问题上表现出来的一致可以比拟。正义与这些公共舆论毫无关系。公共舆论允许我们审判或谴责的,只不过是一些趋势,或者是一些集体――越大越好――,简言之,一些不需要进行划界、不需要指名道姓的普遍性的人或事物。
无须赘言,一旦事关权要名流的言行,这条禁忌就会起到双倍严格的作用。这从一个不无夸张的说法中可以清晰地看出:纠缠细节、针对个人是“肤浅的”,反之,说话时遵循诸如“所有的猫都是灰色的”、“所有人都是有罪的”这样大而化之的原则,则是深明世理的标志。
因此,当霍赫胡斯对一个特定的主教提起诉讼时――这个主教是一个有名有姓、所指明确的人――立即遭到了整个基督教会的反诉。
鉴于基督教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一般而言,对它的指控是不能被证实的,因为一旦被证实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既然从来不涉及人,也就难怪长期以来没有人会为此费心劳神,如果再进一步,安全起见,还可以更进一步,明确指出:“毫无疑问,有理由提起更为重大的诉讼,但是被告却是作为整体的人类。
”(罗伯特?韦尔施语,参前引《Summa Iniuria》一书,着重号为本书作者所加。
) 从确定的事实和个体责任的论域中逃脱出来的另外一条路径,是不可胜数的基于各种笼统、抽象、假定前提的理论――从时代精神到俄狄浦斯情结,不一而足――这些理论无所不包,足以解释并正当化一切事情、一切行为:这些理论根本没有考虑过任何一种改变过去的方案,甚至认为没有人能够摆脱过去的行为方式。
在这些通过模糊细节来“解释”一切事物的概念中,我们发现了诸如此类的观念:欧洲犹太人的“犹太区心理”;从对德国历史的特别阐释中推导出来的德国人的集体罪责;还有同样荒诞的犹太人集体清白的断言。
所有这些陈词滥调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它们全都认为判断是多余的,因而言说这些陈词滥调是万无一失的。我们可以理解这些人(对判断)的拒斥。
由于受德国人和犹太人灾难的影响,他们试图深入地检讨那些看上去受到了、或者肯定受到了集体道德崩溃影响的团体或个人的行为,比如基督教会的行为、犹太领导人的行为、秘谋反希特勒者1944年7月20日的行为等。
尽管如此,这种可以理解的(对判断的)冷淡并不足以解释,何以到处都对基于个体道德责任感的判断表现出了明显的拒斥。 现在,许多人认为,正如不存在集体清白一样,也不存在所谓的集体罪责,因为如果存在的话,那么就没有哪个个人是有罪的或清白的了。
这当然不是要否认诸如政治责任这样的东西,事实上,政治责任完全不同于集体中的某个个人的行为,既不能从道德的角度对经进行评判,也没有办法将它带上法庭。
所有的政府都要为前任政府的政绩以及罪行承担责任,所有的民族也都要为该民族的过去负责。拿破仑在通过大革命攫取了法兰西政权之后,说:我将对法兰西过去所做的一切负责,对从圣路易斯到公共安全委员所做的一切负责。
但他只强调了所有政治生活中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易言之,他所表达的远非是这样一个意思:既然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绵延不断的历史过程中,那么,受惠于其祖先的每一代人,也都应该背负起祖先的罪。但是这种责任并不是我们这里所要讨论的;它不关个体,而且人们只是在比喻的意义上说,他觉得自己对祖先或民族的所作所为负有罪责。
(从道德上讲,为某件实际并没有做的事情有负罪感,与理应对某件事情承担罪责却毫无负罪感是同样错误的。
)不难想象,总有一天,将会有一个国际法庭来仲裁国家之间特定的政治责任;难以想象的是,这会是一个宣判个人是否有罪的刑事法庭。 个人是否有罪、如何对被告和受害者双方都给予正义的判决,只有这些才是刑事法庭亟待解决的问题。
艾希曼案也不例外,尽管法庭遇到的是一种在任何法律书籍中都找不到的罪,一个至少到纽伦堡审判为止、在任何法庭上都不曾见到过的罪犯。我的这个报告如果还有可取之处的话,那就是呈现了耶路撒冷法庭在何种程度上成功地满足了正义的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