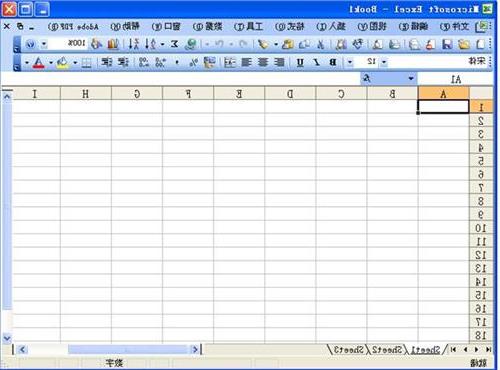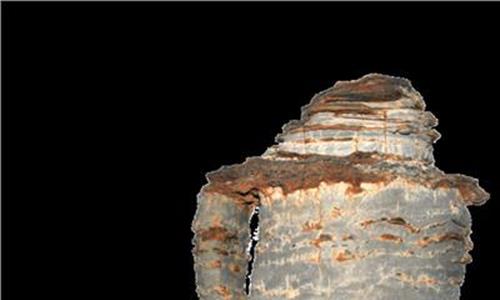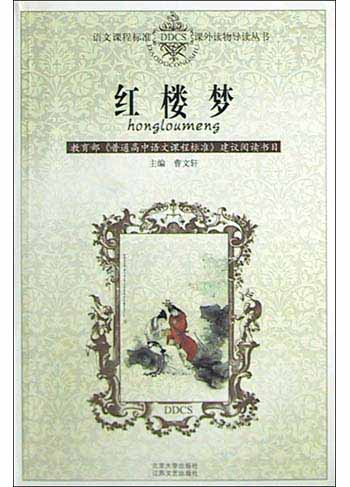俞平伯解读红楼梦 毛泽东的《红楼梦》美学观点解读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关于《红楼梦》的社会背景的讨论展开以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更加引起学术界的兴趣。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红楼梦》的必然产物。人们提出这样的政治“惊奇”:是在什么情况下产生了《红楼梦》这部作品呢?它的社会基础是什么?《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反对科举、尊重妇女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他骂念书人,骂那些举人、秀才都是禄蠹,说女孩子是水做的,男人是泥做的,这样的思想认识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1955-1956年,邓拓先后发表了《论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意义》和《从万历到乾隆———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一个论证》两篇文章,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进行了集中思考。
这两篇文章从崭新的研究角度,以独特的研究方法,对长期以来争执不休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
邓拓认为,《红楼梦》鲜明地反映了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主要是18世纪上半期)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当时的中国是处在封建社会开始分解、从封建经济体系内部生长起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正在萌芽的时期”,其标志是“在封建经济内部生长着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萌芽,代表着资本主义关系萌芽的新兴的市民社会力量有了发展;同封建主义思想意识相对立的市民思想明显地抬头了”,同时,通过历史的考察,邓拓认为从明朝万历年间到清乾隆年间(约16世纪80年代到18世纪90年代),是中国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时期。
“其中,从万历到明末和从清初到乾隆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前一阶段是资本主义萌芽开始的阶段;后一阶段是资本主义萌芽发达的阶段。”这个应用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红楼梦》的创造性论点,至今仍然闪烁光芒,熠熠生辉,就是在当时的学术氛围中,邓拓能够摈弃政治的许多干扰,与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扎实地做一些史学研究工作,其中所体现出来的学者的良知和勇气,是极为难能可贵的。
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接受了邓拓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论点,在提到《红楼梦》时说:“十七世纪是什么时代呢?那是中国的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通过一个世纪,到十八世纪的上半期,就是清乾隆时代,《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个时代,就是产生贾宝玉这种不满意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的时代。乾隆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还是封建社会。这就是出现大观园里那一群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
每个人都是从自身的“实践智慧”里接受前人的政治哲学,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也不例外。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与几个哲学工作者谈话说:“《红楼梦》写了二百多年了,研究红学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之难。有俞平伯、王昆仑,都是专家。何其芳写了个序,又出了个吴世昌。这是新红学,老的不算。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由于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归结为一句话:阶级斗争。因此,“斗争论”成了毛泽东当时解读《红楼梦》的典型范式。
的确,“斗争论”的红学范式是根据政治需要而产生的。如余英时所说,“它不是被红学发展的内在逻辑所逼出来的结论。我们必须承认,在摧破自传说方面,‘斗争论’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但‘斗争论’虽可称之为革命的红学,却不能构成红学的革命。
(第二个‘革命’取库恩之义。)其所以不能构成红学的革命,是因为它在‘解决难题’的常态学术工作方面无法起示范的作用。(按:这是指‘斗争论’所示之‘范’乃唯物史观应用于文学作品的一般‘典范’,而不是为了解决红学本身特有的难题而建立起来的。
)更确切地说,它只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历史理论在《红楼梦》研究上的引申。换言之,这是一种借题发挥式的红学。既是借题发挥,则它的结论是否有效便不能单独取决于所借之题———即红学的内在标准,而必须取决于历史唯物论在清初社会史研究方面的整个成绩。
这一层自然越出了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外。……到了五十年代,由于‘自传说’典范本身的局限性,考证派实已成强弩之末。大陆上‘斗争论’之适于此时崛起,正如海外索隐派的复活一样,是红学发展将要进入新的突破阶段的一种明确表示。”
然而,余英时之所以把“斗争论”的毛泽东的红学思想,作为外加的政治需要,乃是建立在接受美学的维度,才把它排除在红学范围之外。余英时希望按照俞平伯提出的“回到曹雪芹的意思”这个主观观念来确立红学的新范式。“斗争论者”对曹雪芹最苦心建构出来的大观园和太虚幻境,也就缺乏同情的了解。按照历史本来的面目,实事求是地回到曹雪芹和《红楼梦》的时代,正是红学的题中之义。曹雪芹和《红楼梦》的主观意图研究,与我们今天作为一个读者所应有的历史和美学的态度,对于曹雪芹和《红楼梦》所作出的评价,是两个互相区别而又有联系的命题。红学范式的确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如果说,“题中之义”是指曹雪芹和《红楼梦》主观的主题思想,那么,“借题发挥”则是接受美学者客观阐释的主题思想。
在《红楼梦》结构的问题上,根据周汝昌的回忆史料,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出版系统召开过一次人数很多的会议,正式传达毛泽东的一次谈话,其中,在谈到《红楼梦》原著和续作时,明白指出:“前八十回是曹雪芹作的,后四十回是高鹗作的;高鹗学了曹雪芹的一点笔法,但是思想很不相同。”
在那个“两个凡是”的时代,难怪几乎所有的出版社统统接受胡适的这个观点,原因就是毛泽东曾经有过这个“最高指示”。
1975年4月,北京大学讲师卢荻替患白内障的毛泽东读书。8月13日晚,卢荻向毛泽东请教关于几部中国古典文学的评价时,有篇采访记述道:
“卢荻说《红楼梦》她只读一遍半,高鹗的续书不喜欢读。毛泽东说:我读了五遍,要读后来的部分,还特别谈了封建社会的妇女命运问题。”
这个史料说明,毛泽东本人对于胡适的观点从批判到给以适当评价,到晚年给以纠正有一个过程。当面临着接班人选择的危机时,他对于蔡元培整体结构和政治历史小说的观点,开始接受了。
1973年7月4日,毛泽东同王洪文、张春桥谈话,谈的也是《红楼梦》:“贾母一死,大家都哭,其实,各有各的心事,各有各的目的。如果一样,就没有个性了。哭是共性,但伤心之处不同。”
《红楼梦》第一百零六回“贾太君祷天消祸患”与第一百一十回“寿终归地府”,描写贾府的老祖宗,因见贾府被抄家革职,子孙在监质押,邢夫人、尤氏等日夜啼哭,凤姐病在垂危,因此,愁眉不展,忧患成疾。各人有各人的心事。贾府的内部,本来就充满了倾轧、猜忌、勾心斗角、你争我夺的现象。毛泽东发现“四人帮”之后,对新选的接班人王洪文很快就感到失望。王洪文不行,毛泽东准备进一步重用复出的邓小平。
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会上,毛泽东指着在座的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说:
“你就知道打仗。你以后搞点文学吧。‘常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你能看点《红楼梦》吗?要看五遍。《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随陆无武,绛灌无文’。绛是说周勃。周勃厚重少文,你这个人也是少文。”
毛泽东的目光离开了许世友,提高话音对大家说:‘如果中国出了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啊!’许世友激棱一下明白过来了。他拍着桌子站了起来,大声地说:‘把它消灭!不怕,那有什么关系!’
听了许世友的话,毛泽东很高兴,说:‘不怕啊,你就当周勃嘛!你去读《红楼梦》!’”
毛泽东又回到了《红楼梦》上。他所说的“修正主义”,在他的词典里,就是“假马克思主义”。《红楼梦》里真假的政治哲学被毛泽东“借题发挥”了。他从《红楼梦》时代,联想到了西汉刘邦晚年的政治形势。他完全以自己的接受美学的理解,来谈《红楼梦》。
“随陆无武,绛灌无文”随、陆:随何、陆贾,汉高祖时的文官;绛、灌:绛侯周勃,灌婴,汉高祖时的武将。此典出自《晋书·刘元海载记》:“吾每观书传,常鄙随陆无武,绛灌无文。”说的是:人才的片面性,能文者不能武,能武者不能文。西汉的随何、陆贾、周勃、绛灌四位高官,在汉高祖刘邦去世后,他的妻子吕后逐渐掌权,大有以吕氏取代刘氏之势。吕后死,周勃与陈平采取措施,除了诸吕,迎立刘邦之子代王刘恒为帝。周勃对巩固汉刘政权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当许世友弄明白毛泽东让他读《红楼梦》,原来有一番的深意之后,大吃一惊:“天啦,毛主席哪里是与我谈《红楼梦》啊,他这是在暗示我许世友,在他死后要怎么办啊!”
毛泽东一直以来是主张以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红楼梦》的。现在又以真假接班人的观点让人们知道,《红楼梦》是一部反皇帝政治历史小说,烂熟于心的《红楼梦》,让毛泽东通悉了他死后的一切……
马克思主义诞生在《红楼梦》创作后的一个世纪。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和美学批评于《红楼梦》,则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从高语罕的《红楼梦宝藏》1945年问世,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亲自发动并领导从《红楼梦》开始“反唯心论的斗争”,“要建立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的干部队伍”,李希凡、蓝翎的《红楼梦》评论派的初步形成,直至以李希凡、冯其庸先生为代表的《红楼梦学刊》发表的大量文章,七十年代毛泽东晚年对于《红楼梦》结构的反思,强调雍正时代大兴文字狱,曹雪芹家境不衰写不出《红楼梦》,以董志新《毛泽东读红楼梦》为代表。这是一部研究毛泽东解读《红楼梦》的观点和“实践经验”的学术专著,也是一部有着填补毛泽东论《红楼梦》的政治哲学的学术新著。
诚然,毛泽东的红学观点是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维度提出来的。但是,这是否意味着一切从政治需要出发的红学,其中就没有具有学术价值的学术典范?这个问题,值得具体分析。
中国是《红楼梦》伟大小说的诞生国,又是毛泽东发动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唯心论,开展《红楼梦》研究”的策源地,更是利用《红楼梦》,全民批读《红楼梦》,以提高干部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文革”实验国。
政治和学术自己各有其独特的规律。《红楼梦》的评价和研究也有自己的学术规律。唯心论与唯物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在人类认识历史中是长期存在的。一万年后也会有。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由批判《红楼梦》开始的一场清理资产阶级唯心论的运动,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为旗帜,支持“小人物”批判俞平伯与冯雪峰及至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把不同学术观点之争同政治斗争联系起来。这次批判采用政治运动的方式解决学术思想问题,在学术问题上,只有批评没有反批评,缺乏百家争鸣的气氛。由最初的学术观点、思想观点之争发展为政治、路线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说,余英时认为这样的毛泽东式的红学批判,实际上是强加给“红学”的“斗争论”,也是权力专制的“马克思主义红学”。
那么,毛泽东用马克思主义方
法论研究《红楼梦》,批评俞平伯,是不是完全错误的呢?毛泽东的红学观点,是不是借题发挥的外加政治实践需要呢?根据现在公布的毛泽东读书笔记史料来看,研究《红楼梦》的著作中,毛泽东圈画和批注都比较多;特别是俞平伯的《红楼梦辨》,毛泽东读得很仔细,差不多从头到尾都有批画,不少地方,除批注、画道道外,还画上了问号。毛泽东认为,这本书“错误思想集中”在“作者的态度”、“《红楼梦》的风格”两节,对这两节圈画最多。
如在“作者的态度”一节中,作者俞平伯写“《红楼梦》是感叹自己身世的”一句旁,粗粗地画了一竖道,在竖道旁边还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在“是情场忏悔而作的”这句话旁边,也用铅笔画上了竖道,而且还画上了问号。
在“《红楼梦》的风格”这一节,毛泽东画的问号更多,有的一页上就画了7-8个问号。如果说一个问号是表示毛泽东对原著的一个疑问,或者是毛泽东认为的一个错误之处,那么,这一节中毛泽东有疑问的或者认为有错误的地方就有30多处。
比如,就在这一节的开头,俞平伯写道:“平心看来,《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中的位置是不很高的。这一类小说,和一切中国的文学———诗,词,曲———在一个平面上。这类文学的特色,至多不过是个人身世性格的反映。
”俞平伯认为,《红楼梦》的性质“亦与中国式的闲书相似,不得入近代文学之林”。这种“消遣作品说”,与毛泽东认为《红楼梦》是古典现实主义小说的观点是有很大差距的。毛泽东读了这一小段话之后,在“位置是不很高的”7个字旁画下两条粗道,然后又画了个大大的问号。
显然,作者对《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的评价,与毛泽东本人对《红楼梦》的极高评价是相悖的。俞平伯认为,文学批评的眼光是很容易有偏见的,所以“甲是乙非,了无标准”,即“麻油拌韭菜,各人心里爱”。毛泽东认为,“这是胡适哲学的相对主义,即实用主义”。
消遣娱乐功能和政治哲学的教育功能,是文学艺术作品的不同层次的功能。《红楼梦》的作者应用消遣娱乐功能掩盖他的政治哲学教育功能。他利用轻松活泼的美学密码,掩盖了背后的血雨腥风的专制政治历史密码。对于当今读者来说,我们完全有自由选择如何欣赏《红楼梦》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