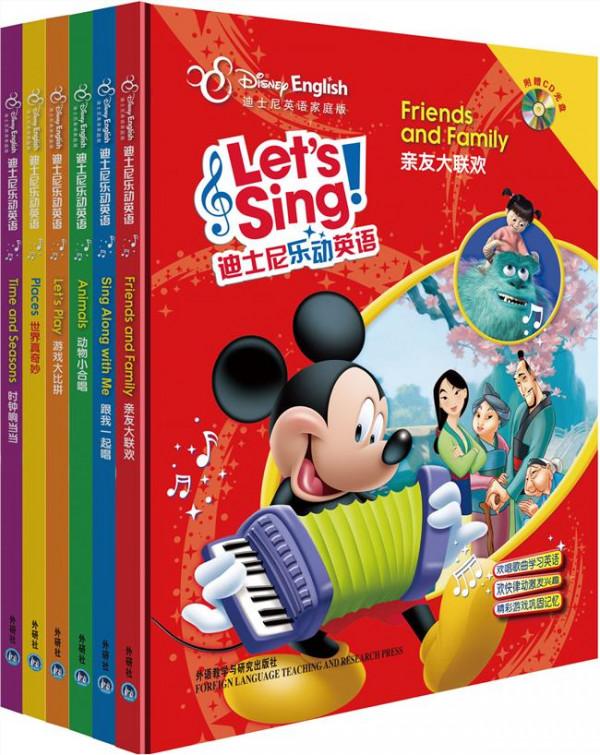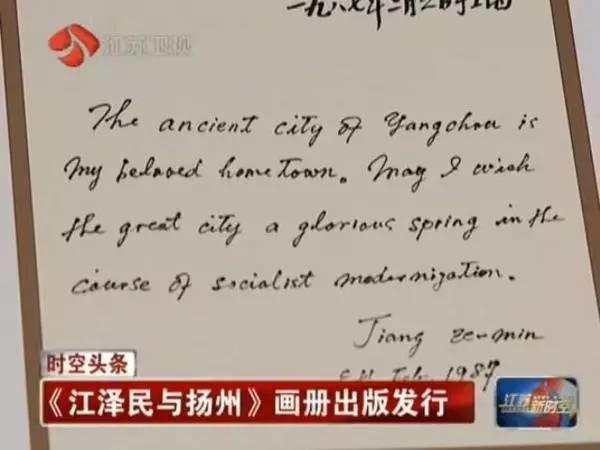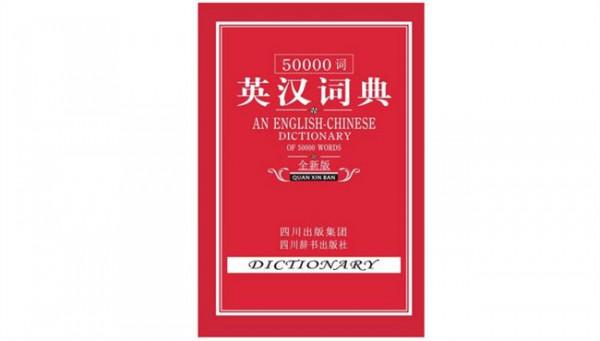陆谷孙杨天石 杨自伍:英语大师陆谷孙
从事文学翻译和学术翻译近二十年。1987年以前曾在《外国文艺》发表译作,1997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译著《近代文学批评史》前四卷,执笔第一卷,其父杨岂深校改全文,共同署名。二至八卷独立完成。上世纪90年代初翻译儿童文学作品《神灯》和《绿野仙踪》之一《林基汀克》。
1992年出版艾·阿·理查兹《文学批评原理》,此书为20世纪欧美文论丛书之一,为国家社科项目。1997年至2000年间主编《英国散文名篇欣赏》和《英国文化选本》及《美国文化选本》(共4册)。
2004年出版外国经典散文丛书之一《英国经典散文》。1997年至1999年出版《英语诵读菁华》(5册)。1993年由台湾联经出版社出版译著《傲慢与偏见续集》。2002年至2006年出版《近代文学批评史》五至八卷翻译。
采访手记
20年,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不过短短一瞬,但在一个人的一生中,却是弥足珍贵的时间概念。1985年,杨自伍着手翻译国际比较文学权威韦勒克的《近代文学批评史》(下称《批评史》)第一卷时,刚届而立。在他翻译的《批评史》第八卷今年年底即将付梓之际,他已年过半百。
记者日前拨通了杨自伍上海家中的电话。他忆及父亲,回顾了自己二十余载翻译生涯的甘苦,也表达了对翻译事业乃至治学、做人的见解。他高兴地告诉记者,前两天,他刚刚阅毕《批评史》第八卷的清样。至此,《批评史》八卷本、共计350余万字的浩大翻译工程终告完成。
电话中的他兴致很好,谈锋甚健。说起这些年独守书斋译笔不辍的日子,他用一句话概括:“用老老实实的态度去做一件值得去做的事情,同时要善始善终。这是我治学的基本原则。”
父子若师徒
杨自伍的父亲杨岂深先生长期执教于复旦大学,为国内研究英美文学的专家,解放前就曾在《文摘》杂志发表过几十万字涉及西方文史哲领域的翻译文章,上世纪50年代与人合译《夸美纽斯教育学》,其主编的《英国文学选读》和《美国文学选读》是改革开放后国内最早出版的英美文学阅读选本,成为多家高校研究生的必备教材。
在父亲的熏陶下,他走上翻译之路似乎是必然的。但是,跟很多同龄人一样,他的成长经历并非一帆风顺——文革期间初中毕业后当过工人,接着辞职自学,后来还在上海外国语大学教过两年书,现在是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英语编辑。
据他回忆,父亲对其的教育是循循善诱式的,“小时候父亲对我耳提面命,到我青年时代准备自己干一番事业,他进而给我一些指导,因为他觉得我似乎可以独立做一些事情了。”由于没有上过大学,他的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和英文都是在父亲的指点下自学而成的。
他至今记得父亲教他修习古文的独特方式:“他手抄古文,然后让我在上面加标点,这令我加深对古文的记忆,理解得更透彻。”直到现在,《世说新语》、《唐宋文举要》等古代典籍仍是他案头常备的读物。
在复旦读书执教一生的杨岂深,工作之外便是读书,心无旁骛,做人和做学问都相对单纯,处于一种为学问而学问的境界。父辈知识分子那种不急功近利的治学心态令杨自伍受益终生:“父亲对我的影响无形大于有形。他教给我做学问应有的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我常常会想起他,这种想念除了父子情深之外,更缘于父亲的精神始终在激励我。”
他觉得,自己虽然身处这个经济飞速发展、技术日益进步的时代,内心反而更倾向老一辈学人的治学状态:“想想父亲那代人,最好的年纪都在动荡中度过,等到终于可以安心做学问,人也老了,这是多么遗憾的事情。更遗憾的是,我们这一代,做学问的很多客观条件远比父辈优越,但是态度却大不如前。”
推开译介韦勒克之门
最初推开翻译之门的杨自伍,兴趣焦点放在译介外国文学作品上。他在《外国文艺》等杂志上陆续发表了一些散文、诗歌、儿童文学作品的译作。上世纪80年代初,年事已高、身体欠佳甚至写字都会手抖的杨岂深计划翻译《批评史》第一卷,杨自伍决心协助父亲完成这一工作。
那时他一边研读中国古典文论、外国文论,一边在父亲的指导下试译《批评史》。经过一年多的锻炼,他逐渐进入状态,正式开始与父亲合译,从此亦拉开他翻译《批评史》的序幕。这之后,他就很少有时间翻译小说了,只是为台湾联经出版社翻译过《傲慢与偏见续集》(1993年)。
记者从《批评史》第一卷“译者前言”中了解到一段插曲:早在1964年,杨岂深在复旦大学外文系资料室初识《批评史》头二卷,便打算将之译介到中国。第二年,高教部拟将此书列为高校文科辅助教材,复旦校方希望他来翻译。他在一年内译出三章,此后便因文革而中止,译稿也因抄家而不知去向。等到他再度提起译笔,已是改革开放初期……
应该说,最终跟读者见面的《批评史》第一卷凝聚了父子二人的心血,该书由杨自伍翻译全稿,杨岂深逐章校改、定稿。杨自伍坦言,当时的翻译过程中自己和父亲有些分歧和争执,也不乏争论得面红耳赤的时候。“毕竟是两代人,对于翻译的理解有所差别。
”杨岂深认为翻译应力求平实,“辞达而已矣”,而年轻的杨自伍则认为,这类学术性比较强的外国文艺理论及批评文字有些枯燥,为便于读者阅读及接受起见,理应在翻译的时候适当提高译稿的可读性。
那时候,父子二人常常对译稿一页一页甚至具体到段落地展开探讨,若无法达成一致,就在不违背翻译原则和减损译文水准的前提下尽量寻求一个彼此都能接受的程度。这样严谨的翻译过程令杨自伍获益匪浅,如斯记忆也令他至今怀念。
从《批评史》第二卷开始,杨自伍独自踏上翻译这部韦勒克皇皇巨著的“不归路”。这条路走得艰辛而孤寂,也充实而执着。如此规模的翻译工作由他一个人来完成,自然需要巨大的精神力量来支撑。“既然开了头,就不能半途而废。”他这样说。
在翻译中提升自己
同时下译界算作热门的海外文学作品翻译相比,翻译韦勒克的《批评史》无疑要求译者具备更高的起点。事实上,翻译《批评史》,篇幅浩大固然是对译者的莫大考验,更大的困难还来自文本内容本身漫长的时间跨度、丰富的信息量和广博的知识含量。
诚如杨氏父子在《批评史》第一卷“前言”中所说,作为一位享誉世界的学者,“韦勒克既博又专”,学术视野异常开阔,跨越多个领域,其广度和深度都令人仰视。而八卷本的《批评史》是他积大半生治学之功,耗费几十年才完成的学术巨著,书中涉及欧美七个国家,时间跨度为两个世纪(1750-1950)的文学批评史,牵涉到众多文学流派、事件、人物和作品。翻译的难度可想而知。
要想顺利翻译韦勒克的《批评史》,译者至少在知识积累、学术深度和译笔上应有基本的“对话”基础,这犹如武侠小说中跟高手过招一样。杨自伍能够明显地体会到翻译《批评史》对自己很多方面的提升有很大帮助。“我觉得自己现在的学术素养及治学状态与当年有不小的差别。
现在有些人所理解的‘比较文学’还是比较狭义而言的,有时停留于具体文本进行对比的层面。而通过翻译韦勒克的这些著作,让我对此有更深更广的认识。他堪称20世纪比较文学专家当中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谈到如何在翻译《批评史》的过程中遵循信、达、雅三项标准,杨自伍表示,任何一种翻译,信都是第一位的,“信、达、雅很难作为衡量所有翻译作品的统一标准。不同文本类别的翻译要视译者对作者及其作品的了解程度、通过作品与作者神交的深浅来界定。
这当中也有悟性的成份。”他强调,翻译学术著作和翻译文学作品有所不同,“学术翻译首先要确保内容严谨,文学作品翻译则以传神达意为要。其实在学术翻译过程中,门外功夫要甚于翻译本身,有时查对资料花费的时间要远远超过翻译的时间。”
翻译《批评史》第二至第八卷的过程中,杨自伍曾经建议出版社找人共同参与,早日完成这项工作,因为这样可以提高翻译的效率,早日完成工作也可腾出精力再去翻译一些自己感兴趣的其他作品,“但是出版方上海译文出版社为了保证整套书的翻译质量,对译者人选宁缺毋滥,最终还是坚持由我一个人完成。”杨自伍苦笑说。
在20年的翻译历程中,杨自伍放弃了很多。特别是在翻译第五至第八卷的将近5年时间里,他除了必要的休息时间,其他几乎所有业余时间都用来翻译。“我在大年初一也只是休息半天而已。”在出版社担任英语编辑的杨自伍,八小时之内朝九晚五,天天上班,做英语教材的编辑、改稿工作。
“那些稿子基本上跟文学和文学批评没有关系。”他半开玩笑地形容自己这种状态是完全分裂的。这些年来他翻译的作品将近400万字,有一半以上是业余时间完成的。
为了节约时间,他很少与外界联系,也尽量减少应酬,还为此牺牲了个人兴趣范畴的文学作品翻译。“上海的方平、吴劳等翻译界的前辈,看到我这些年专注于韦勒克《批评史》的翻译而无暇翻译文学作品,偶尔也会为我感到一丝遗憾,甚至劝阻过我。”他说,“对我来说,翻译《批评史》更多是一种责任感,是非常强烈的文化责任感。《易经》上讲‘靡不有始,鲜克有终’,我一直以此自勉。”
虽然已经将《批评史》八卷全部译完,但杨自伍的工作仍未结束,他还要对这八卷进行一番修订。特别是前四卷,由于翻译得比较早,修订的幅度会更大,甚至会逐句逐句地。他希望修订后的前四卷译文水平能向后四卷靠拢。“《批评史》第八卷的翻译稿一交稿,我就开始修订第一卷了,目前第一卷已经修订完毕,第二卷的修订正在进行中。
”他告诉记者,等到自己将八卷全部修订完毕之后,会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同时推出。他对出版方的做法表示赞许:“这些年来,出版社从未向我催过稿,他们非常理解我的处境,使我能够比较从容、平静地完成翻译工作。
”对于自己译完的东西,他时常觉得不完美:“在这方面我是个完美主义者,或者说希望能做到完美。我很认同傅雷先生的说法,在翻译这件事上,‘少一点则不完美’。我宁可译得慢一些,也要保证质量。”第八卷五十几万字的稿子,即使是二校样,他的改动也不下数千处,之后还要再仔细看。“校对对红之后我还是要再拿回来看一次。”
杨自伍不否认这些年潜心翻译《批评史》会不时感到寂寞,但他也认为,翻译这套书是需要耐得住寂寞的:“我用了这么长的时间,花费这么大的精力来做这件事,当然不是为了名利,否则我随便做什么都会比做这个得到的名利大。
但是从文化积累和学术价值的角度来看,《批评史》要比很多其他的海外著作更值得译介到中国。”面对如今国内翻译界的很多翻译者追逐热门选题来译或者搞重复翻译的情况,他平静地说:“这些年来,我翻译过的书目和文章基本上都是首次介绍,未有重译的。”
坚守超然 自得其乐
说今天的杨自伍心境更加超然并不为过,在翻译《批评史》的过程中,他感受到有形或无形的快乐。
身居中国最具经济实力、最富国际化大都市色彩的上海,杨自伍却觉得这个城市的繁华与他关系不大。他笑称自己并不太喜欢这个生于斯长于斯的城市,因为“上海太摩登了”。隔着窗外的喧嚣,书房中的他过着一种隐士般的生活。
他有时候会想到晚年的王国维,想到那一代学人的选择。除了使用电脑,上网查查资料收发电子邮件,他现在的物质生活同15年前相比没有太大的区别,“这一点是受我父亲的影响,他不太讲究物质生活,一生中也没有什么积蓄。”他理解并尊重其他人的生活方式,同时近乎顽固地坚守自己的方式。“如果不能左右大的环境,至少要独善其身。我只是觉得做一件事情就要争取做好,没有必要考虑那么多,没什么好患得患失的。”
伏案翻译之余,杨自伍最喜欢聆听古典音乐。歌剧、钢琴曲、交响乐都是他喜欢的,疲劳的时候,翻译的时候,陪伴他的常常就是巴赫、威尔第、莫扎特等音乐家的作品。在他每年屈指可数的外出活动中,带着女儿去听古典音乐会是难得的放松和享受。这些年来,由于埋头翻译,他几乎没有时间做家务,“好在妻子和女儿对我十分支持,我也尽量在周末略尽家庭义务。”
在结束采访之前,杨自伍说起他在青少年时期接触了尼采的著作,受尼采影响很大,觉得自己“是个悲观主义者”。小时候,父亲对他说的一句话深深刻在他的心底:“对一个人来说,生命只是面临一个选择——选择做一头快乐的猪,还是做一个痛苦的人。
”他对此的理解是:“要做一个真正的人,免不了有痛苦,即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人还是要有一种境界,这种境界需要修炼。”父亲对他的这种心情十分理解,曾在晚年对他说,希望他40以后能够活得稍微轻松一些,不要有那么大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