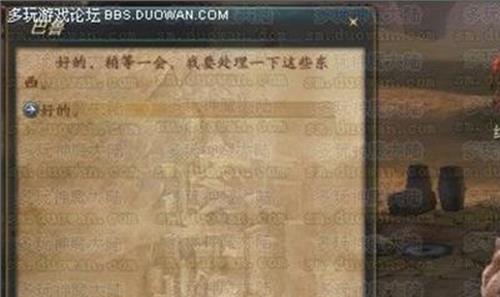谢有顺谈诗 谢有顺:对世界那天真的吟唱——谈谈田湘的诗歌
田湘是我这些年交往最密切的诗人之一。我们认识的时候,最先是聊红木、沉香,接着才聊到诗歌,不知不觉,这已是多年以前的事情了。但我每次见他,总能感受到他作为一个诗人的率真和热烈。我经常在手机里读他发来的诗作,也经常在酒桌上听他朗诵自己的诗歌,每当这个时候,我就想,这是一个真正的诗人——只有真正的诗人,才会如此自然地把诗歌带到日常生活之中。
而我认为,这正是诗歌最富生命力的特征之一:既是精神的私语,也是日用的艺术。
很多人都害怕说出这个事实——诗歌是可以日用的,总是假想诗歌只能活在一个纯洁的精神空间里,这其实是对诗歌的误读。诗歌的发生,缘起于劳动,缘起于感怀,缘起于行走或送别,这就是日用;最初的诗歌,不仅是写生活,它本身就在生活之中。诗歌最辉煌的唐代,诗人并不是躲在书斋里写诗,而是一直在生活、行动中写诗,他们的写作实践,把诗歌变成了极具大众性的日用的艺术,但这并没有降低诗歌的品质。
因此,我们今天要重建诗歌的尊严,不仅要恢复一种诗歌精神,更要恢复一种诗歌生活。
田湘在任何场合,都不讳言自己是一个诗人。他像许多诗人一样,有真性情,但他的诗歌却和很多诗人不一样。他的诗,和当下一些重要诗人比起来,要简单、朴素得多,似乎谈不上什么复杂的诗艺,也不乏随意、粗糙之作,从观感上说,他的诗真是其貌不扬。
而我之所以对他的诗歌怀有浓厚的兴趣,首先是感佩于他的写作状态,他真是接续上了一个重要的诗歌写作的传统:有感而发。他不写所谓的“纸上的诗歌”,不无病呻吟,极其尊重自己的感觉——写作既是对感觉的找寻,也是从感觉出发,用语言为感觉塑形。
如果照现代诗歌的标准看,凭感觉写诗已是古老的行为,诗歌也可能会因此而过于直白,而匮乏可以分析和阐释的高深诗意。可是,假若诗歌只是语言的精妙组装,或者只是为了表述精神的迷途结构,而诗人偏偏不愿意直接说出自己的第一感受,诗歌就会因此而变得深沉而重要么?当代诗歌的深奥、晦涩、繁复,已经相当普遍,它对于解析一种精致、复杂的现代经验而言,或许是必要的——一眼就能洞穿一切的时代过去了,我们必须正视这样一个经验极为复杂、缠绕的时代,但我们是否也要为诗歌留存一份简单和直接?
诗歌的核心是情感,而我以为,有感而发依然是表达情感最有价值的方式之一。
正因为一直坚持有感而发的写作习惯,田湘的诗或许才远离当下诗坛的风习,以自己单纯、质朴、有时也直抒胸臆的诗歌语言,观察、分析、阐释、质询,自由表达,也坦率直言。一些诗句,是生活的偶得,一些诗句,是反复吟咏之后的语言提纯,他的诗,有一种古典与现代相结合的风神。他明显是一个抒情主义者,拒绝用玄奥的意象、过分晦涩的词,他也许认为,直白其心反而可以直达事物的本质。
一朵即将消逝的花/没有人来怜惜/我也无法替她说出内心/但我在见到她的瞬间心就痛了起来/好像凋落的不是她,是我自己/好像是我在这无人的地方/悄然死去了一次//没有人能阻止一朵花的衰败/正如没有人能阻止她的盛开 ——《残花》
一个人老去的方式很简单/就像站在雪中,瞬间便满头白发 ——《雪人》
田湘写花的凋落,写人的白发,这些都是古老的主题,关于年华、时间,多少诗人感叹过了,但他觉得依然有话可说,因为这朵“花”,这些“白发”,是他个人看见和感受到的事物:见到花,想到的是“凋落的不是她,是我自己”;见到镜子里自己的白发,他说,“我不忍老去,一直站在原地等你”,“除了你,哪怕是上帝的眼泪/也不能将我融化”。
这就是属于田湘的“个体的真理”,他说出自己的心痛,说出自己的悲伤,他抒情与感怀——这样的时刻,他需要诗歌记下自己真实的心情。这些细小的“个体的真理”,只是情感的碎片,但对于诗人来说,这就是他的世界,他很容易就通过一朵花,一根白发在这个世界里确证自我的存在。
所以,这个诗歌里的“我”,从不冷漠,甚至还显得过于炽热了,以致田湘的一些诗歌,似乎缺了点隐忍和节制,沉潜下来的东西还不够丰富,一切都抒发得太白了。这似乎已经成为田湘的诗歌性格。他已无意改变这点,但我发现,他的诗歌中写得最好的部分,恰恰来自于这种情感的真挚、锥心,因为有情,所以动人。
“夜深了/女儿的心思/和她望着镜子迷茫的表情/我放不下//天凉了/母亲的关节痛/和父亲的胃窦炎/我放不下//”——读到这样的诗时,我着实心动了一下,许多时候,我们对亲人和世界的挂怀,不就是这么简单么?但在我们的人生中,何曾如此简单地说出自己的“放不下”?太多的伪饰,太多的知识,已经无法让我们直接说出自己心中所想,我们可能更理性、深刻地认识了人生,但我们却漠视了自己的无情。
田湘正是通过简单的抒情,重新成为了一个有情人,他的世界是有温度的世界,他的爱和恨,都有明确的指向。
他不空洞地抒情,他重视人与物的对话、凝视,进而从物中返观自己。他热爱世界,并在这个世界里,建立起了自己的物象系列,所以,他的诗歌中,不仅有他的精神,也有物的精神。物象的建构,不仅使他的情感落地了,同时也让一些看起来平常的事物具有了诗学的意义,使它们在诗的视野里获得了出场的机会。他经常写的物象,有车站、火车、河流、云、雨、月亮,等等,而最经典的是“黄花梨”与“沉香”:
让我用一百年的光阴/为你绣出飓风的纹路/绣出琥珀金丝/绣出山水、森林、天空的倒影/绣出虎豹在树丛中漫步//让我用一百年的光阴/绣出种种鬼脸/使你拥有人类最滑稽可爱的一面/绣出贵妃斑/铭刻你的青春 ——《黄花梨》
被你爱/只因我受过伤害//刀砍。雷劈。虫蛀。土埋/在苦难中与微生物结缘/在潮湿阴暗之地/结油 转世/一截木头换骨脱胎/腐朽化为神奇//安神。驱邪。醒脑/把最好的眼泪给你/别人被爱是因为完美/我被爱是因为/遭遇伤害 ——《沉香》
田湘诗歌中的“黄花梨”与“沉香”,已成了具有他鲜明个人印记的物象符号。木头的美,如此诗意、飞扬,那些灿烂的花纹里蕴藏着风雷的声音;木头的结香,如此沉实、内敛,那些伤害,泪滴,全是生命的细语。李敬泽说:“考察田湘的沉香诗,要把它放进传统背景中去,一是古典诗歌的大传统,特别是其中咏物抒怀的诗学风范。
另一个是小传统,是‘袅袅沉水烟’的传统,是大传统中的支脉,就是关于沉香这种物质,关于焚香这种生活方式的书写。
田湘在现代语境中复活了关于沉香的书写传统。他把一种已近消散的文化和诗学脉络重新接续起来。或者说,他发现了、激活了沉香传统的现代活力。”确实,这种对物的再书写,并使之具有诗学的维度,这是还原了诗歌写作中极为重要的一面——诗歌正是通过语言创造世界:它创造生命与文化的世界,也创造物的世界。
其实,中国诗歌一直有不太及物的传统,长于抒情、言志、感时忧国,往往对于物的世界、经验的世界过于写意,大而化之,这也构成了中国诗歌崇尚情与志、长于务虚的传统;而缺乏实证支持的诗歌,有时,它的现代品质也难以建立起来。
现代诗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对于复杂经验的分析、阐释和表达,这之中,当然也包括物的经验。在现代生活中,精神的落实往往是通过物来完成的,甚至许多的时候,物质本身就是精神。因此,20世纪以来,现代作家从不藐视物质的力量,物质的繁殖和增长,既挤压着人的精神,也扩展着人的精神。
这是一种诗歌的灵魂辩证法。田湘的写作证实了这一点。他对一些物象的反复吟咏,寄寓着他的诗歌情怀,也包含着他对世界和自我的省思。“你若打开自己的美丽/爱情和王座就属于你/”,这说的是黄花梨;“谁能守候百年的寂寞/把苦难升华/让枯木再生/谁能在纷乱的世界里/凝固脆弱的承诺/让生命与爱永恒”,这说的是沉香——但这些何尝不是一种自我凝视、自我省思?物不仅仅是物,它成了田湘通向内心的一个入口;他的诗,不是心灵的空转,而是落实于日常事物之中。
他是一个有世俗心的诗人,他通过一系列核心物象的再造,建构起了自己的诗歌风格。
这些核心物象,除了“黄花梨”和“沉香”,还有“老站房”:“老站房站在黄昏里/像一块旧伤疤/更像一座孤独的坟/埋着我的旧情感”;还有“火车”:“ 动车开的时候,我的身体就有了/高铁的节奏,有了莫名其妙的快”,“旋转的车轮/就像这旋转的世界/ ;还有“月亮”:“ 只剩下一弯镰刀了/要割掉谁的疼痛”。
田湘还写秋风、河流、树,等等,一切生活中的事物,都可进入他的书写视野,但他对于那些最有心得的事物,是不断推敲、琢磨,谨慎地选择用词,为一个佳句的偶得而狂喜,最终的目的,无非就是要找到他在这个世界上最深情、难忘的角落,甘愿为之歌哭。
有时,他对一种事物的歌咏中,之所以会显得用力过猛,就在于他用情专一、爱的深切,在他的内心,一直存着一个希望,那就是希望这个世界是有温度的,人也是有所爱的。
但这还不是田湘诗歌的全部。他的诗歌,还有一个重要的品质,那就是关于生命的思索。以诗歌的方式思考,这在现代诗中我们并不陌生,但这样的思索,常常是把现代人置放于一个卑微、痛苦、幻灭、绝望之中,人多是稻草人、虫豸、悲观主义者、绝望的弃儿的形象,人类失爱、失信,生活在惶惑、迷茫之中,人似乎只能匍匐在地面上生存,再也难以站起来歌唱了。
这当然是不可回避的现代人的生存处境之一。但田湘的写作告诉我们,这并不是生活的全部。
他试图以自己的方式对现代诗中这一普遍存在的黯淡品质提出抗辩,进而对生命、存在作出新的思索。对此,张清华评论到:“他并不缺乏对世界、对生命与生存的亲近哲学的思考,只是他的这些思考并不借助谱系学意义上的‘知识’,而是靠了对世界的忧患而直接进入。
”这一点非常重要,它使得田湘的诗歌维度显得更为丰富,他明白人的渺小与脆弱,但也不放弃歌唱的权利,尤其对世界中那些卑微的事物、低处的生活,他一直存着爱与同情。他似乎要向这个世界作一个相反的见证,如他自己在诗中所言,“在加速的时代寻找缓慢的爱”,在现代世界里寻找传统生活,在卑微的事物里发现坚韧、明亮的品质。
我用加法/计算我逐渐增加的年轮/和增多的白发、心酸、痛苦、回忆/我用减法/计算我逐渐远去的青春/和减少的黑发、激情、快乐、童心//……/但有时我也在加减法中找到惊喜/比如我用加法/增加花园里的小草和花朵/让春天多一些美丽和情趣/我用减法/去掉树上的几根枯枝/让冬天少一些忧伤 ——《加法·减法》
虚掩的门里/有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有着童年、少年和青春的梦想/有着虚空、孤独、忧伤和甜蜜//它似乎在等待一个人/轻轻地把门叩开/可直到青春逝去/那扇门依然虚掩着/那个叩门的人依然没有出现 ——《虚掩的门》
田湘习惯思索生活的两面,加法与减法,打开与虚掩,快与慢,他相信生活的另一种品质总有一天会出现,所以,他的诗歌精神并不阴郁,相反,他能给人以信心,因为他一直相信生活中还有值得守护、值得为之献身的事物。他感伤,但不绝望。
他能在“小草”身上看见“微笑”,能在“河流”里听见“唱歌”的声音,他珍重一切生活中细小、柔软的碎片,而这些碎片,更像是他的心灵穿越各种眼泪、苦难之后一点点积攒下来的,明亮,坚韧,充满暖意。他反思现代文明的各种症候,但也相信生命的本然、世界的本然终究可以为人类的生存敞开新的道路。
而像这样的诗,更是把他对世界、生存的感悟内在成了一种哲学般的思绪:
哪怕你读书万卷/也无法阅尽/他醉卧秋风的/无限愁绪 ——《秋风醉》
江南的庭院很深,白墙黑瓦/住着前朝的商人,富可敌国/却也敌不过,一场雨//雨在秋天打开了菊花/走出瘦瘦的美人/美人送来窒息的一吻/雨便不停地哭泣/菊花就掉了头颅
——《在雨中复活一朵菊花》
在这些诗里,田湘不再是直白地感怀,而是把情绪藏得很深,他是用一种感性的方式思索,但这样的思索,因为诉诸于形象,而更富诗的品质。他的诗,既是对世界的直觉,也是对一种事物与生活的沉思;他有诗人的豪放与旷达,也有一个思索者的警觉;尤其是他对生命与世界那天真而偏执的看法,更是构成了他诗歌中独特的精神底色。
诗歌中的田湘,饱满、激扬、大步前进,但他同时也抗争、内省、反诘、默想。他相信生命的价值、人的意义,相信活着的尊严不可冒犯,看到生之喜悦,也看到死之悲哀——那种生命的热烈与凉意,构成了他诗歌的内面,所以,他的诗,既沉重又轻盈,既复杂又简单,背后贯注的是一种他对灵魂的寻找,对人生的觉悟。
我知道,这些年田湘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写作状态,即便一次漫步、一次茶饮,也会诗兴大发。他有感而发,他创造物象,他思索生命,这是我在他的诗歌中读到的最重要的三个特征,为此,他把诗歌还原成了人类生命的吟唱,而不仅是个人的窃窃私语。那些被他用诗歌大声说出来的事实或思绪,我总觉得,更像是我们平庸生活中残存的精神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