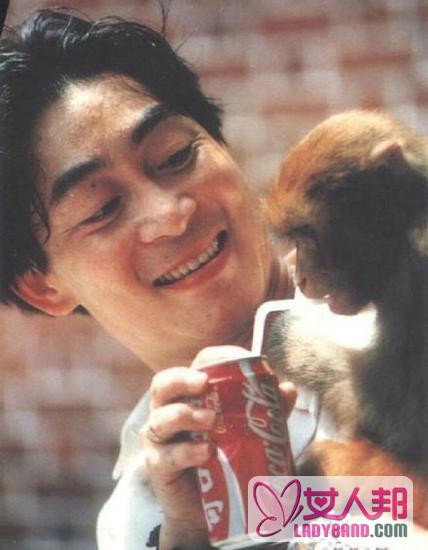郑小琼铁钉 分享生活的苦:郑小琼的写作及其“铁”的分析
你们不知道,我的姓名隐进了一张工卡里 我的双手成为流水线的一部分,身体签给了 合同,头发正由黑变白,剩下喧哗,奔波 加班,薪水……我透过寂静的白炽灯光 看见疲倦的影子投影在机台上,它慢慢的移动 转身,弓下来,沉默如一块铸铁 啊,哑语的铁,挂满了异乡人的失望与忧伤 这些在时间中生锈的铁,在现实中颤栗的铁 ——我不知道该如何保护一种无声的生活 这丧失姓名与性别的生活,这合同包养的生活 在哪里,该怎样开始,八人宿舍铁架床上的月光 照亮的乡愁,机器轰鸣声里,悄悄眉来眼去的爱情 或工资单上停靠着的青春,尘世间的浮躁如何 安慰一颗孱弱的灵魂,如果月光来自于四川 那么青春被回忆点亮,却熄灭在一周七天的流水线间 剩下的,这些图纸,铁,金属制品,或者白色的 合格单,红色的次品,在白炽灯下,我还忍耐的孤独 与疼痛,在奔波中,它热烈而漫长…… ——郑小琼:《生活》[1]
写这首诗的诗人叫郑小琼,她因诚恳地向我们讲述了另外一种令人疼痛的生活,而受到文坛广泛的关注。这个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四川女孩,从2001年至2006年,一直在广东东莞的一家五金厂打工,工余时间写作诗歌和散文,近年在《诗刊》、《人民文学》、《天涯》等刊发表了大量作品。
一个在底层打工的年轻女子,短短几年,就写出了许多尖锐、彻底、有爆发力的诗篇,而且具有持续的创造才能,这在当代堪称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诗歌事件。
面对郑小琼的写作,有些人试图以“打工诗人”、“底层写作”、“女性写作”等概念来命名她,但是,这些名词对郑小琼来说,显然都不合身。命名总是落后于写作的实际,正如生活总是走在想象力的前面。真正的写作,永远是个别的,无法归类的。
郑小琼的写作更是如此。她突出的才华,旺盛的写作激情,强悍有力的语言感觉,连同她对当代生活的深度介入和犀利描述,在新一代作家的写作中具有指标性的意义。或许,她的语言还可更凝练,她的情感陈述还可更内敛,她把握时代与政治这样的大题材时还需多加深思,但就着一种诗歌写作所能企及的力量而言,她已经做得很好了。
我尊敬这样的写作者。在一种孤独、艰难的境遇里,能坚持这种与现实短兵相接的写作,并通过自身卑微的经验和对这种经验的忠直塑造来感动读者,至少在我的阅读记忆里,并不多见。
我没有见过郑小琼,但通过她的文字,可以想象她笔下那种令人揪心的生活。生活,实在是一个太陈旧的词了,但读了郑小琼的诗,我深深地觉得,影响和折磨今日写作的根本问题,可能还是“生活”二字。
生活的贫乏,想象的苍白,精神的造假,在我看来,这是当代文学普遍存在的三大病症,而核心困境就在于许多人的写作已经无法向我们敞开新的生活可能性。
在一种时代意志和消费文化的诱导下,越来越多人的写作,正在进入一种新的公共性之中,即便是貌似个人经验的书写背后,也隐藏着千人一面的写作思维:在“身体写作”的潮流里,使用的可能是同一具充满欲望和体液的肉体;在“私人经验”的旗号下,读到的可能是大同小异的情感隐私和闺房细节;编造相同类型的官场故事或情爱史的写作者,更是不在少数。
个人性的背后,活跃着的其实是一种更隐蔽的公共性——真正的创造精神往往是缺席的。
特别是在年轻一代小说家的写作中,经验的边界越来越狭窄,无非是那一点情爱故事,反复地被设计和讲述,对读者来说,已经了无新意;而更广阔的人群和生活,在他们笔下,并没有发出自己的声音。 这种写作对当代生活的简化和改写,如果用哈贝马斯的话说,是把丰富的生活世界变成了新的“殖民地”。
他在《沟通行动的理论》一书中,特别论到当代社会的理性化发展,已把生活的某些片面扩大,侵占了生活的其他部分。比如,金钱和权力只是生活的片面,但它的过度膨胀,却把整个生活世界都变成了它的殖民地。
“这种殖民,不是一种文化对另外一种文化的殖民,而是一种生活对另外一种生活的殖民。……假如作家们都不约而同地去写这种奢华生活,而对另一种生活,集体保持沉默,这种写作潮流背后,其实是隐藏着写作暴力的——它把另一种生活变成了奢华生活的殖民地。
为了迎合消费文化,拒绝那些无法获得消费文化恩宠的人物和故事进入自己的写作视野,甚至无视自己的出生地和精神原产地,别人写什么,他就跟着写什么,市场需要什么,他就写什么,这不仅是对当代生活的简化,也是对自己内心的背叛。
若干年后,读者(或者一些国外的研究者)再来读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无形中会有一个错觉,以为这个时期中国的年青人都在泡吧,都在喝咖啡,都在穿名牌,都在世界各国游历,那些底层的、被损害者的经验完全缺席了,这就是一种生活对另一种生活的殖民。
”[2] ——我愿意在这个背景里,把郑小琼的写作看作是对这种新的生活殖民的反抗。
她是“八○后”,但她的生活经历、经验轨道、精神视野,都和另外一些只有都市记忆的“八○后”作家有着根本的区别。她在同龄人所塑造的锦衣玉食的生活之外,不断地提醒我们,还有另一种生活,一种数量庞大、声音微弱、表情痛楚的生活,等待着作家们去描述、去认领:他们这一代人,除了不断地在恋爱和失恋之外,也还有饥饿、血泪和流落街头的恐惧;他们的生活场,除了校园、酒吧和写字楼之外,也还有工厂、流水线和铁棚屋;他们的青春记忆,除了爱情、电子游戏、小资情调之外,也还有拖欠工资、老板娘的白眼和“一年接近四万根断指”[3]的血腥……郑小琼说,“我不知道该如何保护一种无声的生活/这丧失姓名与性别的生活,这合同包养的生活”(《生活》),她惟有依靠文字的记录、呈现,来为这种生活留下个人见证: 我在五金厂,像一块孤零零的铁 从去年到今年,水流在我身体里 它们白哗哗的声响,带着我的理想与眺望 从远方到来,又回到远方去 剩下回声,像孤独的鸟在荔枝林中鸣叫 ——郑小琼:《水流》[4]
小小的铁,柔软的铁,风声吹着 雨水打着,铁露出一块生锈的胆怯与羞怯 去年的时光落着……像针孔里滴漏的时光 有多少铁还在夜间,露天仓库,机台上……它们 将要去哪里,又将去哪里?多少铁 在深夜自己询问,有什么在 沙沙地生锈,有谁在夜里 在铁样的生活中认领生活的过去与未来 ——郑小琼:《铁》[5] 黑夜如此辽阔,有多少在铁片生存的人 欠着贫穷的债务,站在这潮湿而清凉的铁上 凄苦地走动着,有多少爱在铁间平衡 尘世的心肠像铁一样坚硬,清洌而微苦的打工生活 她不知道,这些星光,黑暗,这些有着阴影的事物 要多久才能脱落,才能呈现出那颗敏感而柔弱的心 ——郑小琼:《机器》[6] “铁”是郑小琼写作中的核心元素,也是她所创造的最有想象力和穿透力的文学符号之一。
“当我自己不断在写打工生活的时候,我写得最多的还是铁。”“我一直想让自己的诗歌充满着一种铁的味道,它是尖锐的,坚硬的。”[7]对“铁”的丰富记忆,和郑小琼多年在五金厂的工作经历有关。
她在工作中,观察“铁”被焚烧、穿孔、切割、打磨、折断的过程,她感受“铁”的坚硬,尖锐,冷漠,脆弱。“铁在机台断裂着,没有了声音,没有了反抗,也没有它挣扎。可以想象,一块铁面对一台完整的具有巨大的摧残力的机器,它是多么的脆弱。
我看见铁被切,拉,压,刨,剪,磨,它们断裂,被打磨成各种形状,安静地躺在塑料筐中。我感觉一个坚硬的生命就是这样被强大的外力所改变,修饰,它不再具有它以前的形状,角度,外观,秉性……它被外力彻底的改变了,变成强大的外力所需要的那种大小,外形,功能,特征。
我从小习惯了铁匠铺的铁在外力作用下,那种灼热的呐喊与尖锐的疼痛,而如今,面对机器,它竟如此的脆弱。”[8]郑小琼说,铁的气味是散漫的,扎眼的,坚硬的,有着重坠感的;铁也是柔软的,脆弱的,可以在上面打孔,画槽,刻字,弯曲,卷折……它像泥土一样柔软,它是孤独的,沉默的——所有这些关于铁的印象,都隐喻着它对人的压迫,也可以说是现代工业社会物对人的挤压。
人在物质、权力和利益面前是渺小的,无助的。尤其是在中国,社会底层的劳动制度还不健全,廉价劳动力一旦被送上机床和流水线,它就成了机器的一部分,不能有自己的情感、意志和想象。一天工作十六个小时甚至更多,一周只能出工厂的门一次或者三次,工伤得不到应有的赔偿,倒闭的工厂发不出工资……这种被践踏的、毫无尊严的生活,过去我们只能在媒体的报道中读到,如今,郑小琼将它写进了诗歌和散文。
由于她自己就是打工族中的一员,所以能深感这种打工生活正一天天地被“铁”所入侵,分割,甚至粉碎,“疼痛是巨大的,让人难以摆脱,像一根横亘在喉间的铁”。
而更可怕的是,这种饱含着巨大痛楚的生活,在广大的社会喧嚣中却是无声的: 我把头伸出窗外看,窗外是宽阔的道路,拥挤的车辆行人,琳琅满目的广告牌,铁门紧关闭着的工厂,一片歌舞升平,没有人也不会有人会在意有一个甚至一群人的手指让机器吞噬掉。
他们疼痛的呻吟没有谁听,也不会有谁去听,它们像我控制的那台自动车床原料夹头的铁一样,在无声被强大的外力切割,分块,打磨,一切都在无声中,因为强大的外力已经吞没了它们的叫喊。
[9] 甚至,也没有一个人会在意这种疼痛: 疼压着她的干渴的喉间,疼压着她白色的纱布,疼压着 她的断指,疼压着她的眼神,疼压着 她的眺望,疼压着她低声的哭泣 疼压着她…… 没有谁会帮她卸下肉体的,内心的,现实的,未来的 疼 机器不会,老板不会,报纸不会, 连那本脆弱的《劳动法》也不会 ——郑小琼:《疼》[10] 我相信,目睹了这种血泪和疼痛之后的郑小琼,一定有一种说话的渴望,所以,她在自己的写作中一直艰难地描述、指认这种生活。
她既同情,也反思;既悲伤,又坚强。她要用自己独有的语言,把这种广阔而无名的另一种中国经验固定在时代的幕布上;她要让无声的有声,让无力者前行。“正是因为打工者的这一身份,决定了我必须在写作中提交这一群体所处现实的肉体与精神的真实状态。
”[11]她还说,“文字是软弱无力的,它们不能在现实中改变什么,但是我告诉自己一定要见证,我是这个事情的见证者,应该把见到的想到的记下来。”[12]于是,她找到了“铁”作为自己灵魂的出口,在自己卑微的生活和坚硬的“铁”之间,建立起了隐秘的写作关系。
——“铁”成了一个象征。它冰冷,缺乏人性的温度,坚不可摧,密布于现代工厂生活的各个角落;它一旦制作成各类工业产品进入交易,在资本家的眼中比活生生的人还有价值;它和机器、工卡、制度结盟,获得严酷而不可冒犯的力量;它是插在受伤工人灵魂里的一根刺,一碰就痛。
铁,铁,铁……郑小琼用一系列与“铁”有关的诗歌和散文,向我们描述了一个被“铁”包围的世界,一种被“铁”粉碎的生活,一颗被“铁”窒息的心灵——如同“铁”在炉火的煅烧中不断翻滚,变形,迸裂,一个被“铁”所侵犯的生命世界也在不断地肢解,破碎,变得软弱。
“生活让我渐渐地变得敏感而脆弱起来,我内心像一块被炉火烧得柔软的铁。”[13]郑小琼在写作中,以自己诚实、尖锐的体验,向我们指认了这个令人悲伤的过程。她的诗作里,反复出现“铁样的生活”、“铁片生存”、“铁样的打工人生”等字眼,她觉得自己“为这些灰暗的铁计算着生活”(《锈》),觉得“尘世的心肠像铁一样坚硬”(《机器》),“生活的片段……如同一块遗弃的铁”(《交谈》),觉得“明天是一块即将到来的铁”(《铁》)。
“铁”的意象在郑小琼笔下膨胀,变得壮阔,而底层人群在“铁”的挤压下,却是渺小而孤立,他即便有再巨大的耻辱和痛苦,也会被“铁”所代表的工业制度所轻易抹平。至终,人也成了“铁”的一部分:
我在五金厂,像一块孤零零的铁(《生活》) 这真是一种惊心动魄的言辞。人生变得与“铁”同质,甚至成了“一块孤零零的铁”;“生活仅剩下的绿意”,也只是“一截清洗干净的葱”(《出租屋》)。这个悲剧到底是怎样演成的?郑小琼在诗歌中作了深入的揭示。
她的写作意义也由此而来——她对一种工业制度的反思、对一种匿名生活的见证,带着深切的、活生生的个人感受,同时,她把这种反思、见证放在了一个广阔的现实语境里来辨析;她那些强悍的个人感受,接通的是时代那根粗大的神经。
她的写作不再是表达一己之私,而是成了了解这个时代无名者生活状况的重要证据;她所要抗辩的,也不是自己的个人生活,而是一种更隐蔽的生活强权。这种生活强权的展开,表面上看,是借着机器和工业流水线来完成的,事实上,机器和流水线的背后,关乎的是一种有待重新论证的制度设计和被这个制度所异化的人心。
也就是说,一种生活强权的背后,总是隐藏着更大的强权,正如一块“孤零零的铁”,总是来源于一块更大的“铁”。
个人没有声音,是因为集体沉默;个人过着“铁样的生活”,是因为“铁”的制度要抹去的正是有个性的表情: 每次上下班时把一张签有工号245、姓名郑小琼的工卡在铁质卡机上划一下,“咔”的一声,声音很清脆,没有一点迟疑,响声中更多的是一种属于时间独有的锋利。
我的一天就这样卡了进去了,一月,一年,让它吞掉了。[14] 她们作为一个个体的人,身体里的温度,情感,眼神间的妩媚,智慧,肉体上的痛疼,欢乐……都消失了。
作为流水线上的某个工序的工位,以及这个工位的标准要求正渐渐形成。流水线拉带的轴承不断地转动着,吱呀吱呀地声音不停地响动着,在这种不急不慢,永远相同的速度声里,那些独有的个性渐渐被磨掉了,她们像传送带上的制品一样,被流水线制造出来了。
[15] 看得出,郑小琼的文字里,表露出了很深的忧虑和不安:一方面,她不希望这种渺小的个体生活继续处于失语的状态,另一方面,她又为这种被敞开的个体生活无法得到根本的抚慰而深怀悲悯。
她确实是一个很有语言才华的诗人。她那些粗砺、沉重的经验,有效地扩展了诗歌写作中的生活边界,同时也照亮了那些长期被忽视的生存暗角。她的文字是生机勃勃的,她所使用的细节和意象,都有诚实的精神刻度。
她不是在虚构一种生活,而是在记录和见证一种生活——这种生活,是她亲身经历过的,也是她用敏感而坚强的心灵所体验过的。所以,她的写作能唤起我们的巨大信任,同时也能被它所深深打动。
这样的写作,向我们再次重申了一个真理:文学也许不能使我们活得更好,但能使我们活得更多。郑小琼的许多诗篇,可以说,都是为了给这些更多的、匿名的生活作证。她的写作,分享了生活的苦,并在这种有疼痛感的书写中,出示了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对生活本身的体认、辨析、讲述、承担、反抗和悲悯。
读她的诗歌时,我常常想起加缪在《鼠疫》中关于里厄医生所说的那段话:“根据他正直的良心,他有意识地站在受害者一边。
他希望跟大家,跟他同城的人们,在他们唯一的共同信念的基础上站在一起,也就是说,爱在一起,吃苦在一起,放逐在一起。因此,他分担了他们的一切忧思,而且他们的境遇也就是他的境遇。”[16]——从精神意义上说,郑小琼“跟他同城的人们”,也有“爱在一起,吃苦在一起,放逐在一起”的经历,她也把“他们的境遇”和自己个人的境遇放在一起打量和思考,因此,她也分担了很多底层人的“忧思”。
这也是她身上最值得珍视的写作品质。
她的写作,刚刚起步不久,尽管还需对过分芜杂的经验作更精准的清理,对盲目扩张的语言野心有所警惕,但她粗砺、强悍、充满活力、富有生活质感的文字,她那开阔、质朴的写作情怀,无疑是“八○后”这代作家中所不多见的。
尤其是她对“铁”这一生活元素的发现、描述、思索以及创造性表达,为关怀一种像尘土般卑微的生存,找到了准确、形象的精神出口。同时,她也因此为自己的写作留下了一个醒目的语言路标。 当然,我也知道,郑小琼的作品数量庞大,她不仅写了“铁”,还写了塑料,写了故乡,写了河流和落日,写了医院和黄麻岭;她不仅写了很多优秀的散文和短诗,还写了《耻辱》、《在五金厂》、《人行天桥》、《魏国记》、《挣扎》、《完整的黑暗》、《活着的记忆》、《幸存者如是说》、《兽,兽》等多部颇有气势的长诗——要全面论述她的写作,并非这篇短文所能完成的;其他方面的研究,只能留待以后再写了。
2007年5月28日,广州
注释:
[1] 黄礼孩主编:《异乡人:广东外省青年诗选》,38页,花城出版社,2007。 [2] 谢有顺:《追问诗歌的精神来历——从诗歌集〈出生地〉说起》,载《文艺争鸣》2007年4期。 [3] 郑小琼新近以散文《铁·塑料》获得《人民文学》杂志颁发的“新浪潮散文奖”之后,她在获奖感言中说:“听说珠江三角洲有四万个以上的断指,……而我笔下瘦弱的文字却不能将任何一根断指接起来。
”相关报道见《南方都市报》2007年5月24日B11版。
[4] 黄礼孩主编:《异乡人:广东外省青年诗选》,37页,花城出版社,2007。 [5] 黄礼孩主编:《异乡人:广东外省青年诗选》,40页,花城出版社,2007。 [6] 载《行吟诗人》总第九期,2006年7月。
[7] 郑小琼:《铁》(散文),载《人民文学》2007年5期。 [8] 郑小琼:《铁》(散文),载《人民文学》2007年5期。 [9] 郑小琼:《铁》(散文),载《人民文学》2007年5期。
[10] 载《新京报》2005年6月“京报诗刊”专版。 [11] 《郑小琼访谈:在异乡寻找着内心的故乡》,载《诗歌月刊》2005年9期。 [12] 《郑小琼:文字软弱无力,但我要留下见证》,载《南方都市报》2007年5月24日B11版。
[13] 郑小琼:《铁》(散文),载《人民文学》2007年5期。 [14] 郑小琼:《诗歌是一次相遇》,载《诗刊》2005年12月合刊。 [15] 郑小琼:《流水线》,载《联谊报》2007年3月13日。 [16] [法]阿尔贝·加缪:《鼠疫》,第三十节,顾方济、徐志仁译,林友梅校,译文出版社,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