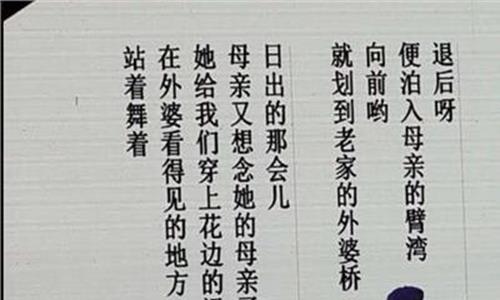郑小琼的诗 艰难世事的诗性担当——读郑小琼《时代的疼痛》
王家增《东方红号列车》,以下均为王家增作品
《时代的疼痛——100个中国女工的个人生存史》以客观而朴素的叙事,出色地呈现出我们时代的特征——建立在底层百姓血淋淋生存基础上的资本积累的特征。这里的事实是触目惊心的,形象是鲜明的。它是以良知或设身处地的体验来处理这些素材,它以明白如见的真实感撼动人心。
这里没有荒诞不经的比喻象征,空想的形而上,没有凌驾于内容之上的崇高的思想,也没有故作高深的形式感,但它却是和处在潜伏中隐隐欲发的时代精神完全融合。这种时代精神已经再次在隐隐轰鸣起来了,而郑小琼预先将对被时代所感知到的,想到的,要求的,愿望的做出了积极的回应。
诗歌想象如何与生存现实相结合,促成其作为公正的公共话语和民主进步的有效成分。在一个科学理性、金钱效用占据主流意识形态和话语氛围的社会中,诗歌还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抒情还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社会真相是否可以和想象力互补,促进更加正义的话语体系,进而为闭锁的社会环境导入自由的声音?郑小琼在对生命的纯朴的认知上显示了她的担当,郑小琼以忧伤而凝重的诗篇回答了这些问题,将这些看似不相关的问题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她的诗歌中表达了一种悲悯而平实的力量。当然,这首先要归因于她对自己女工身份的认同、回归和出离。这种认同、回归和出离,使她的价值判断从生存本体向着诗性本体飞跃,从本质上来看,显然超越了一般诗人认知的眼界。她几乎是从悲剧中去寻找相应的主题,她因坚守心灵的纯净,而具有了某种牺牲精神。
当诗人沉下心来采取一种调研的方式去认识女工,了解普通女工日常生活的形态时,她无形已采取了某种自己所不了解的文化人类学的原则来为自己的工作建立基点。显然,正是具体而微的细节、情节构成了郑小琼诗性叙事的重要因素。
女工们生活的基本状况,即在世事中的变化、演绎,比起抽象的正义理论往往更为真实、更为即时,也就更为敏感、更为有力。由于众多的底层女工悲惨境遇的揭示,而使我们社会结构得以立足的正当性受到极大的质疑,甚至面临合法性的拷问。
《城迹25》,100x80CM,布面丙烯,2014年
郑小琼的《时代的疼痛:100个中国女工的个人生存史》一作表明:诗歌,当然具有畅想承当道义的能力,培育人们同情他者与申讨压迫的能力。正是这些畅想与同情的能力,最终将锻造一种悲天悯人的诗歌新标准,一种我们这个时代稀缺的诗性正义。郑小琼在还原了一百个女工生命原貌的同时,也完成了自己脱胎换骨的变化,使自己回到人的位置,回到了一个真正的人的位置。
郑小琼在《中国一百个女工生存史》代前言中的一段表述,对于她的有关女工的写作来说至关重要,她整个的创作的核心正是围绕着被沦为“麻木的器具者”和“血腥的暴力者”聚拢并展开的,这个临界的状态,开启了她诗歌中语言自性的同时,也为普世诗性价值的回归召回了那古老的出路:它就是诗歌言志和载道路径。
《工业日记十五》,140x200cm,布面丙烯,2006年
现实中,我们的诗人陷入了一种普遍的尴尬,写诗,或者成为一件最容易的事,或者成为一件越来越艰难之事。生命有不能承受之轻,更有不能承受之重,郑小琼祈望从自己的思考和写作中为那些被压在最底层的女工找到一个倾诉的出路,为我们这越来越多的承受暴力压力的社会找到深层的原因,她的诗写无疑是一种承重的诗写。
她看到“悲伤/已沦为暴戾 不幸的人用伤口/测量大地的深度 黝黑的春天/看见底层的人群不断分裂” 为此,她几乎绝望。
这个世界是一个轻浮的世界,能够承担命运,承受重力的人已是凤毛麟角般稀罕。她只好与“低头啃食着寒霜”的马交谈,她的担忧只能“从心间投射到马眼”,能够与“啃食着寒霜”的马交谈人,一定是一个寒冷浸入骨髓的人;能够投射到马眼中的担忧,一定是一种接近绝望的担忧,因为她的忧伤和马眼的忧伤叠加在一起时,就是整个世界的忧伤。
马作为一种被工业文明逐渐湮灭的物种,几乎就是一个象征物。机器取代了马,而人又成为机器的役使者和工具,而实际的情形是人正在步着马的后尘。
为了把诗思所启示的命运承担起来,为了不使自己也像女工们那样沦落到深渊,不得超生,她写作,让自己的声音从深渊里发出来。她为了写作,从一个城市辗转另一个城市,从一个乡村辗转另一个乡村,她跟踪、接近、结交数不清的女工们,记录她们的故事、探寻她们的踪迹、倾听她们的心声。
“成为了一个倾听者与记录者”。 同时她也揭示出我们社会为亡羊之牢所提供的修补和维护,是非常可怜和有限的。尤其是那可耻的部分,依然十分刺目的显现出来。暴力所引发的仇恨的聚集会产生连锁反应,会使暴力不断上升,它最终会触动这个国家赖以维持的基础。
郑小琼为之申辩的女工们和她们的悲惨生活在我们的社会上是“无足轻重”的,尽管她们的命运沉重。作为打工者一员的郑小琼是“无足轻重”的,但是她的诗写所牵引出的 “重”却值得我们所有人反思。尽管整部诗集的主题具有极为鲜明、尖锐而单一的倾向,但是只要我们仔细聆听,就不难发现,该主题中许多不同要素所混合而产生的巨大的爆发力。
同时,自由抒情的思维方式,将意象和隐喻嫁接在主体表述的直接意义上,而呈现出一种承重的独特调性。
《欲望》,150X180cm,布面丙烯,2008年
目前社会上流行着一种道德伦理已死,语言已死的说辞,这种说辞的目的是在为那些应该承担社会责任的部位和人寻求开脱,其论调显然是荒唐的。伦理道德和语言的死活不是在什么理论说辞中,而是在具体实在的处境中。在某个具体实在的处境中,你,或者有人承担了,伦理道德和语言就活了,你,或者所有在场的人都放弃了承担,那么伦理道德和语言就死了,这是无需辩论的常识。郑小琼所选择的承当,让我们肃然起敬。
郑小琼旗帜鲜明地拒绝被人为地贴上某种成功典型的标签,被人当作偶像一般的玩弄,或用来糊弄不明就里的群众。郑小琼诗性沉思具有一种超越世俗的力量,并启发对苦难的敬畏,对生命价值恒久的坚守。由于其诗歌中的重力因素的契入,恰恰成为了对许多虚假社会典型的反讽。
郑小琼的诗写打破了什么样的禁忌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她给那些回避社会责任的写作者以迎头痛击。对于端庄者来说,诗写就是一种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当郑小琼在她的诗写中似图为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申辩,维护她们人的地位,还原她们的生命原貌时,任何柔弱的伤感和空想都无济于事。她切实的举动,显示天理法则仍再人间,也为诗人赋予了一个存在的依据。而她诗性的重力,最终将触动的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底基。
郑小琼的《中国一百个女工生存史》所写的都是真实的人与事,她所揭示的都是在我们生活日常秩序背后隐没的存在。当她以一个诗人的眼光发现并挖掘它们的时候,她身为其中的一员,又不同于其中一员,因为她已在她的生活、生存中植入责任和道义,这是她的命运,也是她和她所写到的那些女工们共同的命运。
而命运中的吃苦受累、担惊受怕是和思想、行动连在一起的,无从忽略和回避。她明白自己身处的那个境域中一切都是那么具体和确实,可也是那么隐秘和潜在,它是我们这个社会不愿触碰和说出的隐疾、癌变、切肤之痛。
《情感的迷惘》,32X32cm,铜版画,2000年
只有这种在场的观察和审视,从生活的表面进入生存的底部,探询或还原生命本身的样貌,理解和表述才能最大限度地贴近真相。郑小琼的诗写获得了最大限度上的真实性的支撑,这种真实性使她的诗歌向着时代史的向度上靠拢。对具体的人与事以诗歌的方式来表述,最容易流于表面化和肤浅化,甚至流于口语化,而词不达意。如果过度的情绪化或阐释,又会令诗性失真。在用何种方式表述的问题上,郑小琼曾有过徘徊、犹豫。
2010年,当郑小琼把“整整准备了六年多的素材的诗歌”那些“写在碎纸上的东西”;那些“模模糊糊的印象”;那些“清晰的记忆”付诸写作时,她已经被一种诗性的力量牵引,不自觉地进入到实实在在诗写中了。因为诗歌才是她灵魂的启蒙者,只有语词的神秘性才能呈现内心深处无从传达的东西,而不是纯粹叙事性的叙述。
在语词中她发现了命名的可能,为那些处于流失之中的底层者命名的冲动,驱使着她的诗写付诸实施。她藉着诗歌使自己的写作获得了最大的自由度。
理性主义和物质主义的魔法所推进的所谓社会进步和现代文明,究其实,是与意识形态乌托邦同质异构的一种象征体系,它同样具有掩饰人性黑暗和自我迷惑的性质。它促使人们将欲望投射到具体的物质之上,从而使个人的幸福和满足超越自己的丑陋、龌龊和罪恶感,表面上看来它是为这个社会建立起一个富足、和谐的美景,实质上是用那些底层普通民众的巨大牺牲为代价的一种换取。
在这个过程中,底层生命中惟一的真实往往被不屑一顾, 个体、自我,这个的生命的唯一载体随时都有被碾成粉末的可能。
当郑小琼意识到要将被类群化,被抹杀了个性的女工,还原到一个个有血有肉,有感情、有思想的个体的时候,她“尖锐的敏感”被激发了出来。这里“尖锐的敏感”其实就是一种诗性直觉,它成为这部热情的作品的基石,也是这部作品的基本立场和出发点。
她要为女工们辩护,让她们从那“低贱”处所或称谓中逃离出来,获得人的尊严,她就必须让她们每个人从个性上,从不同的经历、境遇上得到甄别,然后她们才可以获得一种人性上的认同和维护。
是诗性的方式给躯壳以血肉,给思考以力度,使材料变成揭示和见证。我这里所说的诗性的方式,是因为郑小琼的写作,没有流于平铺直诉式的口语,她所保存的最基本的诗歌语言传统,赋予她的诗歌以客观的、朴素的、反省的重力。
郑小琼的诗写,我们可看作是生存与语词肉搏的一种结果,是具体实在的生存情境与词语的狭路相逢中,碰撞出了惊心动魄的呻吟、呼唤和哀嚎。《女工之尖叫者周阳春》一诗的女主角,以每夜梦魇中发出的尖叫,传递着自己的存在,令我们每个感受者的心都会为之颤栗。女工们有权利表达自己的痛苦和绝望,但是当她的痛苦和绝望只变成一声尖叫的时候,我们在哪里?我们世界的良心在哪里?
为凸显每个女工的个性和她的悲剧的显在性特征,如果郑小琼将每首诗的标题做以醒目的标示,如《女工之疯女》《女工之跪着讨薪者》《女工之尖叫者周阳春》,这样具体人物事件便更会呼之欲出,更具震撼力。
“思想走在行动之前,就像闪电走在雷鸣之前一样。”郑小琼的思想使被蹂躏、受辱弄者坚强,使强横者被鞭笞。当她的诗写把那一个个被遗忘的女工从角落里唤了出来,让她们自由的表述她们自己的同时,也是对我们这个冷冰冰的世界,报以怜悯的讽刺。
中国历史上的叙事诗写的经典范例,诚如《孔雀东南飞》《胡笳十八拍》和《琵琶行》这三个作品,标示了诗写女性或女性诗写的高度,也标示了中国古典叙事诗的最高水准。一种个人身世命运的写作,却让我们获得一个时代史实和史诗的认知。
这样的作品既不是什么异象,也不是什么来自天界的声音,它只是一种内心深处的哀痛和颤栗的表达、表白,当这种表达和表白深刻地触及到了当时社会的背景,以及人性的本质层面,就具有了普世而恒久的价值。
郑小琼与蔡文姬、无名氏的和白居易的诗写同出一源,其诗性中透彻的认知力,对于时代悲剧疼痛的承担,至为深邃。
《车间里的男女》,84X70cm,铜版画,2000年
在南都报的采访中郑小琼曾对记者说:
郑小琼诗写之初,尽管采用了文化人类学方式,但是她付诸的写作方式却是叙事和抒情相糅合的诗歌方式。从诗歌的语境来看,她仿佛又是对一般叙事和抒情的反拨乃至抵制。郑小琼的表现是让人惊异的。审视她的诗歌,除了让人震惊的众多的详情细节,同时众多女工生活场景的揭示,所表现的不再是一般的一个个体,而是地狱中默默挣扎、忍受的群像。
实际上这种诗写过程是一种深刻地体验苦难,发掘悲剧的审美活动。索尔仁尼琴曾说过这样的的话:“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的份量还重。
”阿多尔诺也有过类似表述:“让苦难有出声的机会,是一切真理的条件。”斯皮尔伯格说的更是直接:《辛德勒名单》是“用血浆拍成的”。审美活动就是如此:见证苦难,觉察悲剧。因为生命的苦难和悲剧是自古而然的,审美活动就是要真实地呈现它们,而不是伪装加以规避。郑小琼的诗写整个就是在体验悲惨人生的疼痛战栗。
随着郑小琼调查的深入,许多更加让人触目惊心的社会悲剧浮出水面。这些悲剧并非毫无来由,依阿多诺之见,在现代化的大工业生条件下:“通过管理手段对数百万人的谋杀,使得死亡成了一件样子上并不可怕的事情。”难道真的并不可怕吗?阿多诺的话大概只说对了一半。
《工业日记234号》,180x250cm,布面丙烯,2010年
对一个诗人而言,写诗无须任何理由,它就像呼吸一样自然。但当说到承当悲苦,我们许多诗人的口舌或许就会结巴,语焉不清,或者要么选择沉默,要么绕道而行,任世界陷入混乱与无名,继续制作自己的风花雪月、闲情寂寥。他们生怕自己被卷进这悲剧的轮子,被碾轧得浑身伤残。而真正的诗人不会去计较个人得失,他的诗与文字本身将显示见证的力量,写作终于不得不成为这样一种见证的方式。
在郑小琼诗写中任何漂亮的空话、假话,似是而非的话都被排除在外,因为当她经历了那样的鲜血淋漓的现实之后,再以那种媚俗的方式去写诗是野蛮的,要让真正的写诗重新成为可能之事,就必须记录正在完成原始积累的现代工业化和商品化的真实状态,就必须涉及工业机器对底层社会的压迫和蹂躏。
写作即意味承担人性及其所有后果,这是诗人的良知绕不过去的。郑小琼的悲剧人物尽管处境悲苦,但是仍然展示了某种面对生活的姿态,这种姿态让一个人即使身处绝境,仍然会为爱情、乡情、友情而守望、坚持,并从中体会到某种活着的意义。
诗神青睐的始终是这种个体的经验,哪怕它只是工厂里一个工人残缺的个体体验,甚至是暗娼耻辱的经历。诗歌不能制止一次对弱者所实施的杀戮或戕害,甚至不能使我们躲过一次小小的磨难。但是诗歌可以让我们选择记忆,拒绝遗忘。
郑小琼对于惨烈的人间悲剧的察觉、揭示和担当,使得那些披着光明外衣的写作显得相形见绌。当一种写作撕开了“野蛮”的外衣,“悲剧”的帷幕时,它就会为文明开启一个空间。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的“虚伪”、“野蛮”,正是由于审美的误导所致。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郑小琼是获得了成功和荣誉的,但是她并没有因为这些表象的东西而冲昏了头脑,从而与那些“低贱”的打工者划清界限。她非常清楚她与生俱来的善良加诸她的观念是和经历、记忆密切相关的,因为她的认识在她的心灵显现,并付诸诗写时,并不是那种异想天开和天马行空式的幻想,而是来自真实经验的汲取,她诚实地使用了这笔资源。
当然她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抛开或者避开过去的一切东西,打开另一条或许更为畅通的通道,就她的感受力和写作的能力来说,她是可以的。
经历曾在她身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人性的立场与利益之间也或多或少地相互对立着。当她以人性担当者的名义为那些悲剧者代言时,她就必须亲自培养起自己的孤独,只有孤独能给以她更为详细的知识,赋予她诗性的直觉。她在对她所关注的世相作了解剖时,她也解剖了她的孤独。而她的孤独,就是整个世界的孤独。
《有序的无意识状态》,60×49㎝,铜版画,1997年
孤独是人天性中的本质,当它从内心显现出来,与相应的观念及其象征对接之后,它就越发显明而具体起来。孤独无处不在,有在人群中被淹没于无形的孤独;有独处时被寂寞窒息的孤独;有被名声绑架的孤独,有被失名沉溺的孤独。
我们每个人都留恋孤独,又害怕孤独,孤独所造成的矛盾,时常会在人心中激起一阵稀有的恐怖,一阵难以形容的压迫感。孤独所贯穿的意识,是人在存在中的基础被抽空的状态,处在这个状态中并有所知觉的人,会有不知道自己是谁,从何而来,往何处去的强烈的感觉。
郑小琼的孤独正是处在几种孤独情境的核心地带:当她想要为身处其中的这个弱势群体伸张之时,却怀疑这些人是否认同她的身份、需要她的出现;当她独处,并将试图将自己从这个群体中分离出去时,她又感到自己确是其中一员;当她想要在获得的名声中躲藏起来时,她的良心又会感到不安;当她出没在这个被漠视的人群中时,她又怕被无名的手掌掐死。
一个人会“变成一群人”,而一群个人也会“变成一张面孔,一个影子,一个数字的一部分”。在这个物质至上没有信仰的时代,个人和群体的失踪都在所难免,活生生的生命最终不过都变换成了一部机器的零件,一件商品,一张纸币,一种代用品。
物质享乐主义像所有绝对主义一样,以它的胜利和奇迹为自己提供自圆其说的辩护。被暴力埋在社会底基混凝土和石块中的失踪者,也只是沉默的失踪者。
在这里,在郑小琼的诗写里,她是一个惧怕失踪的孤独的跟踪者。当她把她的孤独感从理智中不加掩饰的释放出来,甚而宣告它的存在,那么她也为诗性开启了它的不可见的声音,让失踪者突然从地底站立出来,冲破了神殿的屋顶。
这正是郑小琼孤独诗写的处境,她不堪忍受孤独,从这个貌似安宁的氛围中突然冲了出来,我们所有的道德秩序就陡然增加了被颠覆的危险。当然,不是郑小琼要颠覆什么,而是这个社会正走在自己颠覆自己的路子上,这真是一个荒唐又可笑的境遇,这也是我们时代的孤独之所在。
郑小琼珍惜自己的孤独感受,并用感情的言词表达出来。她的孤独并不纯粹,其中有爱、有温情、有愤怒、有悲哀、有恐惧……但是她内心深处却是纯净而安宁的,这种纯净和安宁为具体的描述找到了尖锐的感觉。郑小琼处在她的悖论中,我们每个人都处在自己的悖论中,因为孤独在那里作祟。
郑小琼的诗写不是那种时髦的写作,也不是玩弄的,或卖弄噱头的写作。用愁肠满怀和愤世嫉俗来定义她的写作似乎也不确当。因为她并没有因了生活的重压,而被榨干了心灵的汁液而自暴自弃,相反她从命运的书写中觉醒,洞察到那些底层女工的血泪之于这个时代的意义。她也没有诅咒谩骂、怨天尤人,或与主流意识形态及体制形成一种紧张的关系。她从自己沉重的命运中走出来时,她从未间断过反思带给她们这种命运的社会背景和深层原因。
郑小琼诗写了自己的时代,却和自己时代的写作拉开了相当的距离;她反映了这个时代症结,却是对这个时代主体价值的一种无形消解。她的写作材料和依据都是真实的,而真实,却是我们每个人都还没有想清楚,或避之不及的事。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将自己定位在这样一种不合时宜的写作时,她就与我们的所谓的社会主流相悖了,因为我们的社会是一个盛行逃避的社会。诸如重力、真实、疼痛、悲哀、孤独等等都是人们避之不及的东西,但是郑小琼却在这逼仄的处境中选择了担当。
《归的企想》,33×43㎝,铜版画,2000年
郑小琼此类的写作是为了出名,或者为了招惹别人的注意吗?是出于梦想、心仪和神往吗?是寻找一种刺激或者自我的安慰吗?我们可以肯定的说这些都不是她想要的东西。是一种心灵的直觉,一种良知选中了她,让她来承担这对于她来说过于沉重的担子——道义和见证的担子。
她在这个写作中强烈地感觉到,自己的生活不在别处,就在这个被人忽略的逐渐变得模糊的地带,她逃不掉,也不愿意逃出去,她的炙热的良心不允许她逃脱。郑小琼的诗写对象都是坠入无底深渊的弱女子,在这里,她们仿佛都是国家的陌路人,郑小琼正是在这些“最无价值”的人身上发现了最重要的东西,因为那些被侮辱与受损害者需要她的证词,需要她的正名,需要她的诗写还她们以公道,还她们以天理。
在新世纪混乱而噪杂的拜金主义气息的笼罩中,在真正的诗写已成为禁忌的时候,郑小琼用血泪写成的诗章所表达的内心深刻的痛苦,与我们生活表象上的光鲜形成了极为鲜明而尖锐的对比,其中的主体立足于生存的真实:具体、具象、可感、可触。它控诉和控告的力量聚集了整个作品的底气,它是梦魇中的一声振聋发聩的尖叫,令我们在暗夜的沉睡中突然惊醒,出一身冷汗,令我们惶恐、颤栗。它穿越的力量具备一种象征的含义,具有挽歌的意味。
郑小琼的诗写,并不止于诗意的需要;并不止于绝望中的眺望;并不至于疼痛的化解和摆脱。我感到当我们的时代、我们的社会让郑小琼这样的弱女子来承担道义的重负时,我们的时代、我们的社会真的是可怜而可悲了。
从郑小琼的诗写中我们强烈地感受到她是那种真诚、天真的人,她只带着自己的心上路,其它的一切她都可以忽略不计,作为一个没有任何社会背景,没有任何实在资源的打工者,她的诗写无疑是寒风中的独唱,这是一种极易将人摧垮的写作。郑小琼是弱小的,她在风中聚集着的哀痛、忧思的能量能否使她变得强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