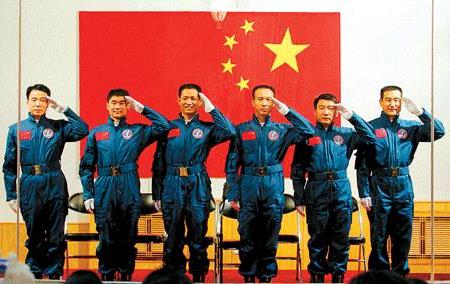司马光世称 专家称司马光是"官二代" 或非上佳的宰相人选
我立志为司马光作传的最大动力来自时代——我们身处忧思与改革的年代。我们应当相对理性地于“实事”中,“求是”地认识司马光和他的时代。
●司马光所处的时代存在一种可将该朝带出“朝代更替”宿命的力量
司马光所处的时代,矛盾重重,改革声浪高涨。如何化解矛盾,让本朝长治久安,走出“朝代更替”,是那个时代的精英念兹在兹、不敢稍有遗忘的大关怀。我固执地相信,就在那个时代,曾经存在着一种可以把这个王朝带出“朝代更替”宿命的力量,这些力量包括:尊重制度与传统的皇帝,有担当的知识分子官僚群,包容异见、接纳批评的政治风气与政治制度。
1043年至1044年,在仁宗大力推动下,范仲淹、富弼主导了一系列以制度建设为核心的改革,史称“庆历新政”。这是一次最为“对症下药”的改革,它触动的是上层的利益。按照通常说法,“庆历新政”以改革派被赶出朝廷而宣告失败。
但是,细读历史,你会发现,“庆历新政”的结局绝不是我们理解的那种“失败”——十多年之后,改革派重返朝廷,多项改革措施重新推开,只不过姿态更低,步伐更为稳健、更加有力。改革需要决心和勇气,也需要对现存状态的尊重,更需要长途跋涉、长期战斗的耐力。
司马光是“这一派”的改革者——如果我们不把“改革”跟“王安石变法”划等号,只用“改革”的原意“把事物中旧的不合理的部分改成新的、能适应客观情况的”,那么,司马光完全可以称为“改革者”。
在我看来,仁宗朝也许取得了帝制时代儒家政治所能取得的最好成绩。“吏治若媮惰,而任事蔑残刻之人;刑法似纵弛,而决狱多平允之士。国未尝无弊倖,而不足以累治世之体;朝未尝无小人,而不足以胜善类之气”——一种并不纯净整齐的中庸的美好,背后是复杂的人性与更加复杂的利益缠斗。
司马光和他曾经的朋友、后来的对手王安石都是仁宗朝宽容政治的产儿。只可惜,这种宽容经这两个人的手走向了终结。宽容的政治培养出不宽容的政治家,最终埋葬了宽容。
●皇帝保持中立,君臣间保有起码的信任,国家才有出路
皇帝制度是我们认识那个时代的最大前提。古代至少有两种皇帝:第一,是作为国家和朝廷象征的抽象的皇帝;第二,是宝座上那个具体的人。在整个帝制国家,抽象的象征性的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因而是政治斗争中唯一可称“公正无私”的最高仲裁人。
当然,宝座上那个具体的人能否承担这种责任是另外一回事。儒家信奉的是君子政治、贤人治国。谁有资格判定人物贤愚,区别君子小人?说到底,只有皇帝。宰相大臣的判定资格是不完全的。一个不避群议、以选优汰劣为己任的宰相,最有可能受到的攻击就是“结党营私”。
唯一可以为他辩白的人只有皇帝,只是这皇帝最忌讳的恰恰是朋党政治。“庆历新政”的搁浅,范仲淹、富弼的下台皆植因于此。宰相大臣不结党,政见可以不同,却能共商国是,皇帝保持中立,君臣间保有起码的信任,国家才有出路。
作为一个尊重历史、通达古今之变的人,司马光深知在宋朝之前没有一个朝代做到了长治久安。诚实的历史观察与大宋忠臣的美好愿望始终矛盾。从实践上看,司马光选择的是规劝、引导具体的皇帝扮演好抽象的角色。从担任礼官开始,司马光积极参与批评朝政缺失。
只不过,跟包拯的大炮轰鸣、欧阳修的敏锐高调相比,司马光的谏议风格是温和理性的,他总是站在皇帝的立场、说着为皇帝打算的话,他甚至能够把皇帝尚未作出的英明决定描绘成一幕歌功颂德的话剧,最终把皇帝拉回到正确的立场上来。司马氏谏书真是提意见的最佳范本。
●司马光有“道德洁癖”,这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也许并非好事
但是,司马光也许真的不是上佳的宰相人选。他的成长过程太单纯、太顺利,他是一个高级官员的小儿子,从小受到父亲的庇佑,父亲去世后又得恩师庞籍的提携照顾。如果跟王安石相比的话,司马光独当一面的地方工作经验,以及实际行政工作历练都太过缺乏。
说到这里,还得回到“时代”的话题——到司马光开始参加工作的时候,完全没有家庭背景的人已经很难上得来了,司马光是“官二代”,王安石也是。“官二代”意味着优质的教育条件,广阔的人脉资源,以及自幼的耳濡目染——即使选拔制度完全公平,他们也有更多机会胜出。
仁宗朝的游戏规则基本还算公平。司马光从父亲和恩师那里得到的,基本上是正面的官场教育。这让他对“诚实”“孝道”“守职”等道德信条终生保持了坚定信仰,也让他在现实政治的“灰色地带”面前痛苦不堪。
恩师庞籍违反制度,私藏文书,让司马光对其免于处分,给他带来了一生之中最大的痛苦和纠结。他的纠结多半来自内心,是内在的崇高道德标准与灰色现实之间的冲突,我们甚至可以说司马光有“道德洁癖”。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这也许并非好事。(赵冬梅 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