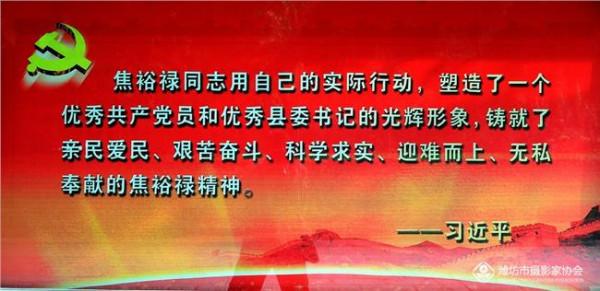焦菊隐妻子 焦菊隐最后的日子
▲1954年6月,曹禺(右)和著名戏剧家、导演焦菊隐参加北京人艺院庆大会。(资料片)
1954年春,我被调到北京人艺灯光组来工作。刚来没几天,听剧院邵惟秘书长的介绍——剧院有一位副院长是全国赫赫有名的大导演,他叫焦菊隐。又听到同事说,大家都尊称他为“焦先生”,是一个相当严厉的导演,有时候在排练场上,只要他一拍响导演桌上的手铃准备开始排戏,站在布景片子后边候场的演员,还没有上场两条腿就打哆嗦;有时,对演员的表演不大满意,焦先生竟然会大声喊着:“你再上一次场,如果还不行我就换人!”……
一次难能可贵的表态
1973年,北京话剧团(北京人艺在“文革”中的名字)排练了一个歌颂农村干部王国福阶级斗争精神的话剧《云泉战歌》,当时上边来了一个新精神——对于“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要实行“一批、二用、三养”的政策。于是,剧院“军工宣队”准备征求一下已经“在群众当中继续接受监督和改造”的焦先生对这个戏的意见。
接到看话剧连排的通知以后,一位和他关系不错的演员(也是他的学生),马上来到他住的小平房里以好言相劝:“如果非去不可,我提出三个办法供您选择——第一,是看完戏以后一言不发,这样他们就抓不住您的‘辫子’,顶多说您不够积极;第二,是光讲好的方面,一个字也不要批评,他们顶多说您有顾虑,不诚恳;第三,是凭着自己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想到说什么就说什么,这可能是最危险的。”
焦先生听后一阵沉思,没有吭声。
连排结束后第二天,“军工宣队”派人来找焦先生谈看戏的观后感。焦先生认真地想了一下,说出:“政治上刚及格,艺术上只能给20分。”
这个表态很快就上了剧团的第13期《情况简报》,当作一个“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的突出事件,既上报,又下发。
那位热心的演员马上找到焦先生说:“您可捅大娄子了!三种办法您为什么单单选了最坏的一种呢?”焦先生似乎是有所准备的,缓缓地解释道:“我这一辈子都是凭艺术家良心办事的。我知道你的办法都是出自善良的愿望,谢谢你对我的关心。至于他们对我的意见有什么看法和打算,我是根本不作考虑的。”
苦闷难排解
“文革”后期中的一天清晨,焦先生心灰意冷,在无处可走、无人可叙说的情况下,来到前夫人秦瑾的家里。
他们相对无言,停顿了许久以后,焦先生说:“老舍跳太平湖自杀了!你知道吗?”秦瑾说:“知道了。”又停了一下,焦先生继续说:“其实我很理解老舍,士可杀不可辱,读书人凛然正气嘛!告诉你吧!我多少次想走老舍这条路,为了可怜这两个孩子,我从护城河边又走回来了。
她们小小的年纪,读不了书,又当了狗崽子,任人欺凌,我什么也没有留给她们,要是再给她们背上一个沉重的政治包袱,她们怎么活下去啊!所以我一直硬挺着,忍受着不堪忍受的凌辱。
”秦瑾听着轻轻地叹了一口气,没有说什么。焦先生回忆说:“记得几年前在首都剧场开梅兰芳的追悼会,那天我紧排在老舍的后面,老舍回过头幽默而感伤地对我说——‘焦先生,在死神面前我们也正在排队呢!
’这话深深地埋在我心里。”他提高声音说了下去,“我多少年有个习惯,每天晚间上床脱鞋时,总要默念着明天该完成哪几件事,可现在我每天晚间上床脱鞋时,心里默念着老舍,我说,老舍啊老舍,我是紧排在你后面的一个,带我走吧!明天别叫我再穿上这双鞋了!”说到这里,焦先生强忍着满眼的泪水,赶忙摘下近视眼镜拿在手中,反反复复地用手擦起来……
撒手西归
就是在这样一种精神近于崩溃的情形下,焦先生感到胸部非常不适而住进了医院,并确诊为晚期肺癌,动手术也已经无济于事了。
焦先生为了不给亲朋好友们带来痛苦,面对这一切装作什么也不了解,只是平静地要求见见下乡插队的大女儿焦世宏。当他见到从延安赶回来的焦世宏以后,出人意料地竟然说出这样一席话来:“我在‘文革’中写了几百万字,可惜全是交待自己反动罪行的材料。
我的来日不长了,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留下来,只有一些多年做导演的心得体会,要把它留给后人。我自信自己还可以再活两年,你要把我说的都记录下来。我要争取把自己多年探索实践的收获,比较系统地整理出来交给后人。我现在是生命已经被判了死刑的人,什么顾虑也不会再有了……然而,这可就要为难你了,孩子!”
焦世宏还没有把父亲的话听完,就已经是泪流满面、泣不成声了。她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只能连连点头表示要照此办理。
在这以后,焦世宏为此准备好一个像样的大笔记本和一支钢笔。
然而,事与愿违,焦先生由于对化学放疗的反应非常强烈,病情急转直下,很快就进入了弥留的状态。
焦先生在病床上,疼痛难忍,唯一使其牵挂的事,是焦世宏按照政策规定早应办理却迟迟没有办成的回北京之事。当焦先生在病床上紧紧拉着女儿的手,用含糊不清的话问:“你……的户口……落上……了吗?”焦世宏点头答:“您放心吧,已经落上了!”这时,焦先生才面带笑容地合上了双眼,撒手西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