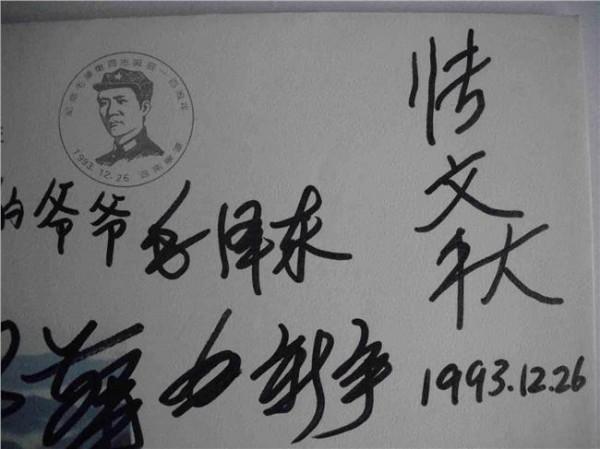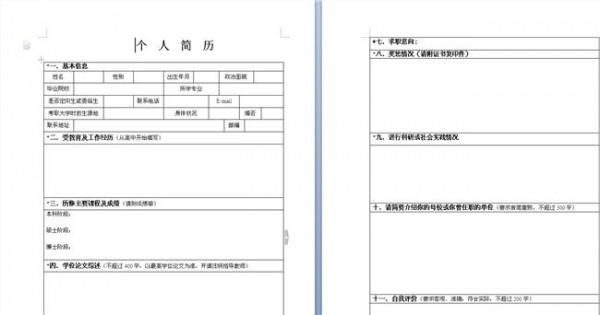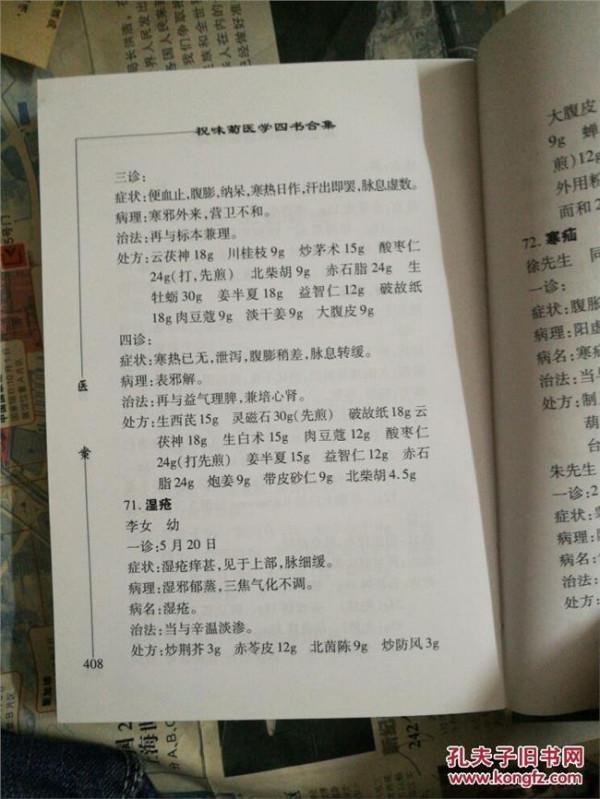焦菊隐俞平伯 不该忘了她——纪念焦菊隐想起李伯钊
近来在报刊上看到不少文章报道,纪念戏剧家焦菊隐先生百年诞辰和去世30周年。高度评价了他在全国解放后,特别是在北京人艺的艺术建树。不过许多文字从未提到一个人,而这个人对焦先生是至关重要的,焦先生在新中国初期的被请出山和委以重任,就是由这个人慧眼识珠,并顶着相当的压力,把他从学校“挖”到北京人艺,首先由他执导了老舍先生的《龙须沟》,不只使北京人艺“一炮走红”,更使焦菊隐和老舍一再合作,直至共同创造了我国话剧艺术的颠峰之作《茶馆》。
正是这个人,当初毅然任命焦先生为剧院艺术委员会主任、总导演兼副院长,这才由此奠定了北京人艺的基本风格,又因此使北京人艺成为我国话剧艺术的典范。也由于有了北京人艺这一“平台”,焦先生才有了用武之地,得以实现自己的抱负,展示了他的才华、主张和创见,从而造就出一位杰出的艺术大师。
遗憾的是,不只这些关于焦先生的文章没有提到她,近年来有关老舍先生当年的文章,也没有人写到她,连北京人艺的建院纪念文集史册之类,也似乎忘了她,不说这是“数典忘祖”,也是喝水忘了“掘井人”,而这是不应该和不尊重历史的,应该有人也为她说几句话。
这里说的她,就是我国老一代戏剧家,中国人民军队和革命根据地戏剧艺术的创业开拓者之一,为戏剧事业奋斗终生的老红军女战士——李伯钊同志。
在她生前我只偶尔见过,并未接触交往过,只是在她逝后参加她追悼会时,我看到莅会者党政军民各个层次的都有,除了大批著名演员和戏剧界、文化界人士,还有从中央机关到戏剧院校的工作人员和司机、公勤员等等,更来了许多老一代革命家甚至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一批军队高级将领与军中文人,他们都为逝者的过早辞世异常悲痛。
这引起了我的注意和思索,从关于她的“生平”中看到,她在革命经历上,其实与一批党和国家领导人,尤其是著名女革命家蔡畅、邓颖超、康克清和贺子珍等属于同辈战友,仅仅由于她一直从事文艺和戏剧工作,最大的“官”只当到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并曾任北京人艺开创时期的院长。
正是在党分派给她的这些岗位上,她作出了无愧于别的老革命家的重大贡献,在长期革命历程中起了独特的作用。
就是从人们悼念她时起,我认为应为这位虽不身居高位,却为党和人民奉献了毕生精力和全部才华的文艺同行树碑立传,便开始搜集她的资料,这才逐渐了解了她的历史及其业绩,其中之一就是她创建北京人艺,并决心请出了艺术家焦菊隐。
根据史实,李伯钊于1949年3月,作为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员和文化接管委员会负责人之一,和一批战友进入北平。繁重的接管工作之一,就是寻访、探望和安排大批的文艺界人士和老少新旧各种艺人。在清除旧中国文化垃圾的同时,开始了新中国文化事业的开拓和建设。
她作为人民首都的市委文委书记兼市府文教局副局长,以她原来领导的华北文工团为基础,充实了北京演艺界的各方面优秀人才,于1950年元旦,创建成立了我国第一座大型国家综合性剧院——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她成为首任院长。
她作为老革命家,深知如同革命战争要取得胜利,除了必须有人民群众和广大战士的英勇奋斗外,更要有优秀的指挥人员,人艺应该有杰出的艺术家。她了解到有位有着丰富学识和艺术创见的戏剧艺术家,在艺术界影响很大并众望所归,这就是戏剧理论家焦菊隐。
当时焦先生正在北京师范大学教书,是位艺术教育家。她立意把焦先生“挖”过来,但在进一步了解之后,却使她为难了,原来焦先生和他同代的知识分子一样,不只个人历史曲折,社会关系也很复杂,当时属于“不宜重用”之列。
她反复斟酌又作了深入考察,认为焦先生的以往历史和社会关系,只是他的一个方面,其主要方面即艺术学识上,却是无可非议的,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就努力说服持有“左”倾观点的同志,并且力排众议地大胆决定又多方设法,硬把焦先生从北师大“挖”了出来,请他担任了北京人艺的艺委会主任、总导演兼副院长,不只使北京人艺有了艺术上的“主心骨”,也为这位艺术家提供了一个实践舞台。
李伯钊对北京人艺和焦先生的决策和工作不止于此。剧院最初只排演了外来甚至解放前的剧目,她认为应该迅速推出自己的作品。由于她是老北平的解放者和新北京的建设者之一,对这座城市的两个时代两种社会的对比感受特深,人民政府正在市内进行各种改造和改善工作,北京南城的龙须沟等地,人民群众就享受到一些实际好处,这种新人新事新气象,很可以搬上舞台予以宣扬。
她又了解到回国不久的老舍先生,对北京群众生活特别熟悉,就几次亲自登门拜访他,请他去看看新生的龙须沟等地,感受一下正在发生的变化,又为他提供了不少资料,更创造了使他深入访问的方便条件,请他考虑能否为人艺写一部戏。
老舍面对如此热情,欣然接受邀请和建议,连续访问了龙须沟等地,获得了大量切实感受和生动素材,认真构思后写出了剧本。李伯钊看了,认为基础很好,决定作为人艺的第一个重点戏,马上进行排演,并由焦菊隐执导。
哪知在全院讨论剧本时,各种意见都出来了。有些人认为这个本子,缺少连贯故事和跌宕情节,没有通常的“戏剧性”,简直是个“活报剧”。听得连老舍自己也动摇了,不安地问焦菊隐:“你看这个能成吗?还像一出戏吗?”李伯钊考虑了各方面的意见,特别听取了焦菊隐的想法,认真商讨后肯定了这个剧本,一致认为其中人物性格鲜明,语言贴切生动,形式也简朴明快,内容更耐人寻味,虽然不合某些“编剧法”,但却自成一格很有特色,并且是第一部表现新中国新生活的戏,应该得到支持,便和焦菊隐共同决定,马上正式排演此剧,由焦先生作出导演计划,她则组织动员全院力量,深入领会和努力实现作家的创作意图及导演的艺术构想。
李伯钊作出了北京人艺的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
也许是好事多磨,就在全院投入紧张排练时,作家老舍和导演焦菊隐之间,在艺术见解和创作手法上,却发生了分歧,他们一个坚持自己的设想,另一个要作必要的改动,两人各不相让,争得戏都排不下去了。李伯钊马上细心又耐心地听了双方的意见,分别反复磋商后,为他们提出了一个协调方案,即老舍的剧本原作一字不动,作为文学本独立存在,焦菊隐则根据舞台要求,另编一个演出本,两个本子相辅相成互为补充。
这使作家和导演又愉快地合作起来。
他们不仅从此结成艺术友谊,更由于两位艺术家的密切合作,老舍不断为人艺写作剧本,焦菊隐则成为他每一部剧作的当然导演,由此形成并奠定了北京人艺的独特风格,并成为我国话剧艺术的典范,而这个成果正是在李伯钊的引导下实现的。《龙须沟》公演以后,不仅使人艺“开门红”,还使老舍成为政府授予的“人民艺术家”,也使焦菊隐总导演确立了他在戏剧界的崇高地位。他在《龙须沟》的导演总结中曾深有所感地写道:
这里,应该特别提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李伯钊同志认识之深刻,基本思想之卓越,和领导的正确而坚定,没有她那么英明果断的坚持,这个文学剧本很有可能不会和广大观众见面,而全国各大城市的文艺工作组织,也不会排除了顾虑之后,纷纷在筹备上演《龙须沟》。
上述这些都是有据可查、有史为证的,如焦菊隐这样,受到李伯钊赏识、支持因而取得成就的,决不止他一位。她从红军时代到其晚年,在文艺界特别是戏剧界,曾受教并得益于她的,又何止万千?可是如今在各种有关文章中,却几乎一字不提李伯钊在这方面的贡献,连中央电视台的《电影传奇》,关于《龙须沟》的专辑,也根本不说这部北京人艺以至新中国的“开门戏”,到底是谁促成并使其成功的。
连周恩来总理观看此剧的照片上,她和老舍正一左一右地坐在总理身边,也不介绍一下那是谁。
从大量史料中可以看到,李伯钊一生对革命文艺事业,有着一系列“第一”甚至“惟一”的贡献:她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个戏剧团体——八一剧团的创始人之一;是革命根据地第一座戏剧学校——高尔基戏剧学校的创办人和主持者;第一个用话剧、歌剧等艺术形式,正面表现了革命战争;主编、主导和主演了第一批影响巨大的戏剧作品;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她不仅是惟一一个参加了一、二、四方面军长征的老战士,又是三个方面军文艺训练班和剧团的惟一讲授者和领导人;长征刚结束,她又和丁玲共同创建了党领导的第一个“全国文艺协会”;抗日战争中又参与创建了解放区第一座最高文艺学府——延安鲁艺,于1938年创作并成功演出了第一部新型抗战歌剧——《农村曲》,这一作品不只传遍各解放区,还演到了国民党统治区;接着又创办并领导了第一个鲁艺分校——鲁艺晋东南分校,在此前后还参与或主持创建了延安第一个交响乐团、第一个电影制片厂等等;新中国诞生前,又主持并率领了我国第一个出国艺术团,将我国革命歌舞第一次推上了国际舞台;接着投入了新中国特别是北京市的新文化开创和建设事业,创办并领导了第一座大型国家剧院——北京人艺;又参与创建和领导了第一座话剧艺术学府——中央戏剧学院;亲自创作了第一部反映长征史诗的歌剧《长征》,其中塑造了毛泽东的第一个舞台艺术形象……她在艺术事业上的创造建树、业绩功勋,硕果累累,举不胜举。
当年长征结束时,李伯钊作为红军和根据地主要文艺活动家,于1936年11月在陕北保安会合了来自白区的作家丁玲,两人共同主持成立了第一个“全国文艺协会”,毛泽东亲自到会说,她和丁玲是红军和白区两个“方面军”的总代表,从此将胜利会师并一起战斗了。
然而正是分别来自解放区和国统区两个“方面军”的两位领军人物,在全国解放以后,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当时文艺界主要领导人的错误方针,丁玲被残酷地打了下去,李伯钊实际也被压了下去。
我在写作《李伯钊传》和参加编辑《李伯钊文集》时,她的丈夫和战友杨尚昆同志特许我阅读了她的各种日记、笔记和文稿资料,我从中看到,她对当时文艺领导人意见很大,但她只在日记中写,从不公开表示自己的不满,严格遵守着党的纪律和组织原则。以后历史已经表明,当时文艺领导人那么做是极不正常的,倒是李伯钊始终坚持了正确的方针。
“文革”风暴来临前,李伯钊的丈夫、正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就被打倒了,接着又成为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成员。她很快受到了严重冲击,又受到了残酷迫害。长期遭受批斗、劳改后,她被整得一身是病,几乎成了残废,但她在困境中仍不忘自己的事业和职责,“文革”后自己党籍尚未恢复,更不等着治疗疾病,立即投入了艺术创作。
由于自己体力不支,她动员并带领着儿子和一二个学生,组成了一个小小创作集体。她主持着反复商讨又分头执笔,八易其稿写出了一部大戏——反映长征史诗的话剧《北上》,并找到当年红一军团的老剧团——广州军区战士话剧团排出了此剧。
演出后又引起了轰动,除被调到北京为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献演外,又获得了国家优秀剧作奖。正当她拖着病残的身子,深入长征地点遵义等地继续搜集素材准备再写新作时,忽然一病不起,于1985年4月7日,带着遗憾,搁着残稿,溘然长逝!
刚刚过去的2005年,就是李伯钊逝世20周年,但我没看到对她的任何纪念或仅仅是表示,似乎她从未在世上和人间存在过。当人们纷纷著文追忆老艺术家焦菊隐时,我不由想到当初大胆决定请出焦先生的这位“伯乐”式人物,希望也能给她一个公道,让后人多少知道一下这位红军老战士、革命艺术家——李伯钊。
去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李伯钊不仅是中国八年抗战的亲历者,而且早年曾在苏联学习,以后又曾赴苏和东欧,她的活动和作品大量是反映抗日和反法西斯的,但是在纪念胜利时,没见有人提到过她。今年是长征胜利70周年,李伯钊不仅是一、二、四三个方面军长征惟一亲历的女战士,又曾三过雪山草地,漫漫长征路上,步步都留下了她的血汗脚印。人们还会不会又忘了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