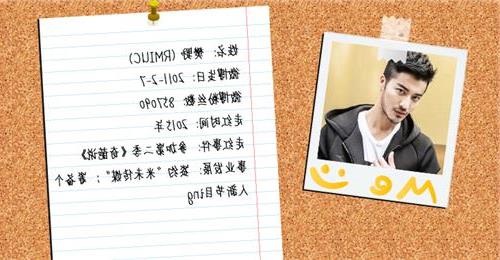红卫兵武斗打死人?为什么? 《红卫兵传》
一场红卫兵武斗中,16岁的他挥舞大棒打死了19岁的他……今天,62岁的王冀豫选择站出来向世人说出自己的罪。“忏悔太虚了,我不求原谅,我认账,活该受折磨,遭报应。说出来,是为历史留下证据”注册登录之后查看大图《一个红卫兵的反思》
一场红卫兵武斗中,16岁的他挥舞大棒打死了19岁的他。
43年,他常在暗夜中醒来,问自己:“我打死人这事儿该怎么算呢?”今天,62岁的王冀豫选择站出来向世人说出自己的罪。
“忏悔太虚了,我不求原谅,我认账,活该受折磨,遭报应。说出来,是为历史留下证据”
王冀豫
生于1951年,曾是北京中学***中“老红卫兵”一派的成员。16岁时,他在一场武斗中打死了人。他当过兵、务过农、干过工人,改革开放后最早的一批“玩马”者,自称“牧马人”。
1985年参与创办中国最早一家马场——北京稻香湖马场。
2013年6月,《炎黄春秋》杂志刊登了一则特殊的“道歉广告”,61岁的退休干部刘伯勤利用广告向“***”中受到自己批斗、抄家和骚扰的众多师生、邻里道歉。
在道歉广告中刘伯勤说:“垂老之年沉痛反思,虽有‘***’大环境裹挟之因,个人作恶之责,亦不可泯。”这则特殊的广告迅速引发了媒体的关注,更促使人们反思个体在集体行动中的责任。
四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的“革命小将”多数已经退休。那一代人,经历了疾风暴雨的革命,又经历了改革开放的大潮,沧海桑田,际遇或许大相径庭,但那段“革命”的共同记忆一定深深地刻在每个“红卫兵”的心里。
红卫兵们究竟如何看待?似乎是一个谜。公开反思自己曾经犯下的“罪”的人少之又少,触目可及的是沉默的大多数。
注册登录之后查看大图
早在2010年5月,《炎黄春秋》杂志就曾刊登过一篇名为《背负杀人的自责》的文章,文章的作者就是当年的“红小将”王冀豫。
时隔三年,记者再一次找到王冀豫,当问到“沉默的大多数”时,他说:“很多人不说也确实是因为这是一种集体犯罪。共犯时代,谁也不能说谁。当然,个人的罪恶是不能掩盖的。比如像我打死了一个人,这是不能掩盖的。”
红卫兵组织很像“义和团”
我是“大院”长大的孩子,“***”爆发时在铁三中读书,后来又在翠微中学混。
翠微中学并不是一个好学校,但由于地理位置的缘故,这里集中了大批的“大院”孩子。所谓“大院”,就是干部子弟聚居区。当时,公主坟以西有包括空军、海军、通信兵、总后勤部、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解放军军事政治学院在内的众多军队大院,也聚集着众多的“大院”孩子,“大院”孩子大多经过保育院和小学寄宿制教育,相互之间感情好、抱团。
1966年,我才十五岁,上初二。“***”初期,开始组建红卫兵的主力是高中生,以部队干部子弟为核心。我们初中生基本就是跟着高中生跑,跟着起哄,没脑子的那种。高中生则有思想、讲策略。运动初期,红卫兵组织也想搞“正规”,还有点假正经,恨不得拿入党的标准来衡量自己。
虽然红卫兵组织企图正规化,但红卫兵组织从来就不是一个正规的组织,它其实就是一个群众的乌合之众。各种红卫兵组织只有看似相近的意识形态,却没有统一的组织形态,更像是白莲教、义和团。
1966年8月,被人称作是“红八月”,是红卫兵打人最厉害的时候。
很幸运,当时我不在北京,不然我肯定参与打人。今天的人们都在说“红八月”,吞吞吐吐的,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血腥的行为。
“***”刚一开始,工作组就进入了我所在的铁三中,由于受高中生的影响,我感觉工作组的行为是压制群众,企图用一种正规的方式来把群众运动捆绑在笼子里。
我就开始写大字报,给学校提意见,批评工作组“束缚群众”,这下就有反革命的嫌疑了。工作组找到我爸谈话,听说我有反革命嫌疑,我爸马上就慌了,本来就是一野孩子,又有了反革命嫌疑还了得,“你干脆当兵去吧!
”就这样1966年6月份,我离开北京,到内蒙古当兵了。我当兵的时间并不长,10月我父亲便出了问题,“兵”就当不成了。到11月份,我的津贴被停了,也未能随部队南下参加抗美援越,只好留在驻地继续放牛。1967年初,大概是春节前,我回到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