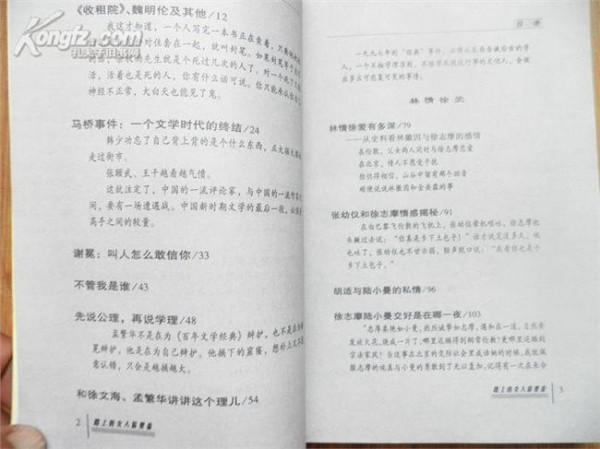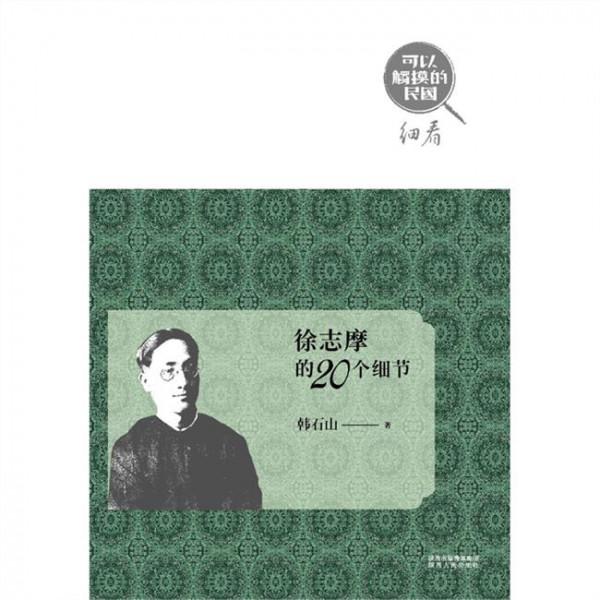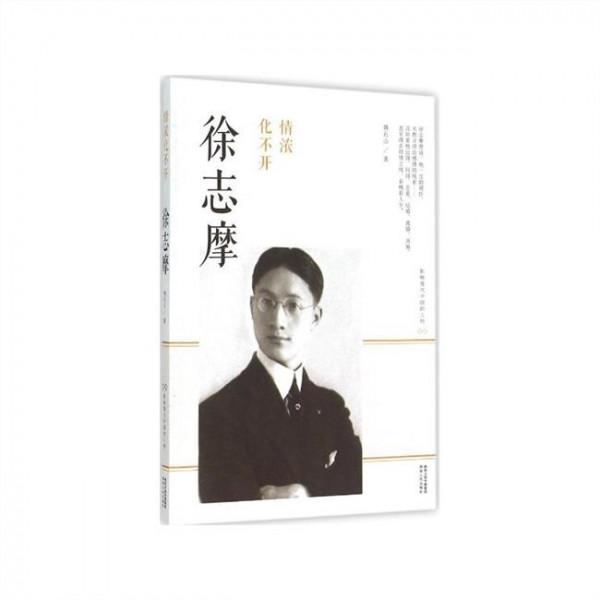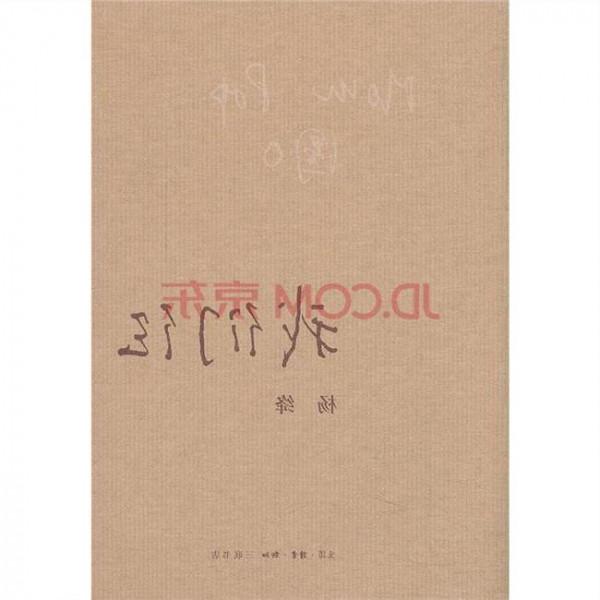韩石山婚姻 韩石山简介
或许是生于苍凉的北地,自小我就对颜色特别的敏感。不管是什么景致、诗句、人物或事件,只要有了感情,总能给它敷上相应的颜色,变成一幅画儿———我没有成为画家,实在是画坛的幸事。
因此,一接到沪上朋友的电话,说是可否为《朝花》50周年写点什么,应允之后,我的眼前马上就现出一个景致:碧蓝的海面上,波涛微微起伏,朝暾初起,清辉闪耀,一簇红艳的花朵,正吐出鹅黄的花蕊……
一写下短小的、适宜报纸副刊登载的文章,就由不得想到“朝花”———那两个朴拙却极见功力的毛笔字。多数情况下,自家先就摇摇头,判了它个“别处发落”。投往山西报纸的稿子,是给父老乡亲看的,我知道他们的口味,也就有几分的自信;投给山东、河南的稿子,我知道他们不过是富裕了的山西,也不会没有自信;就是投给北京的稿子,我摸得透他们的脾性,也就不会胆怯。
独独投给上海的稿子,总有几分心虚。那是中国最早浸染现代文明的都市,也是中国报业最早发达的都市,其眼光该是何等的刁钻,其口味该是何等的难调!
万幸,几经犹豫,偶或寄出的稿件,也居然有登载的可能。更让我大惑不解的是,有些我认为出言不逊的文章,也竟然不加删节,全文刊出。接到样报,读完自己的文章,再看那朴拙而极见功力的“朝花”二字,方始明白,这朝花不是娇嫩的初绽之卉,也不是虚有其表见水即湿的纸品,乃是傲然挺立于东海之滨,经历过半个世纪的狂风暴雨的洗礼,阅尽了共和国世事沧桑的历史的见证者、书写者。它的神韵,它的气度,岂是寻常报纸副刊可比拼的?
闲来无事,一面品味着这朝花二字,一面由不得就想到了中国报纸副刊的历史。据我简陋的识见,上世纪一二十年代,海内报纸初有副刊时,那个“副”字每作“附”字,比如有《晨报副刊》的报额上印的就是“晨报附刊”。用这个附字,有附送的意思,即正张之外再附送一张,供看过新闻之后,作茶余饭后的消遣。
然而,这最初的一点温情,随着时光的流逝,终于显示了它绝大的膂力。扭转了整张报纸的顺序,也扭转了人们阅读的习惯。反过来,也扭转了报纸老总的观念,报纸版面的编排。新闻要的是快捷,社评要的是犀利,而副刊,要的则是趣味与品位!
有趣味不难,迎合是也。有品位却不易,对于高品位者是俯就,对于低品位者则是引导。寓迎合、俯就、引导于一体,这该是何等的艰难,又是何等的高妙!
当此社会转型而又商潮汹涌之际,最见报人的操守与品格。有曳兵弃甲而走者———弃副刊而专事娱乐版者是也。有森严壁垒而固守者———弃副刊而专登大块文章者是也。概言之,不外是以娱乐而遮蔽其低俗,以高雅而文饰其粗鄙。副刊之副,遂成为媚世之粉黛,无味之鸡肋矣。
《朝花》则不然,迎风而挺立,逆流而愈艳。
我从未去过它的编辑部,但我能想象得出,在上海汉口路300号的那栋楼房里,该有一群怎样的人物,在辛勤地劳作着,精心地编排着。
50年了,若是一个人,正是他最为成熟也最见风采的年纪,然而,对于一个报纸副刊来说,如果它当初是年轻的,又一以贯之地坚守自励,不为世风所惑,不为穷达所移,它就永远年轻,永远亮丽。
愿这株永远年轻、永远亮丽的《朝花》,接受我这乡佬来自乡野的微薄的祝贺吧!(解放日报2006-1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