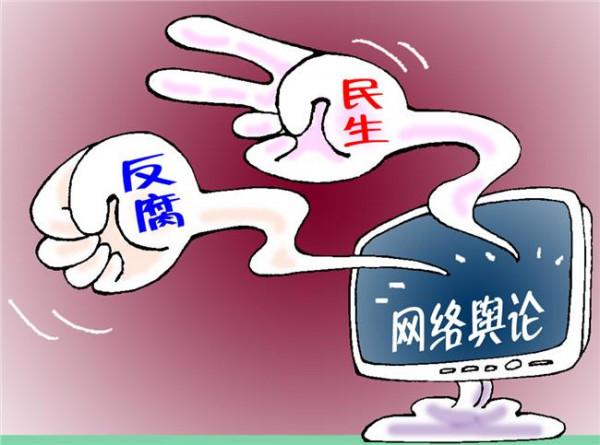阿伦特与政治的复归 理解政治生活:阿伦特与亚里士多德“自足”思想的分歧
在阿伦特的概念序列中,人类实践活动被区分为三种基本活动形式:劳动、制作与行动。这很容易使我们联想到亚里士多德对人类活动的区分,即理论、制作与实践。在亚氏看来,一种活动的目的(“善”)越是在其自身,而非在于任何他物,这种活动也就越是自足的,也就越意味着自由。据此,自由首先意味着从满足生存必然性需求的活动中摆脱出来,而满足生存的必然性需求的活动劳动被认为是奴隶的“专门活动”,不属于“人类活动”之列。
在亚氏看来,理论、制作与实践三种活动都是具有程度不同的“自由—自足”性的。但是,制作活动在本质上是受一个外在于它的目的引导的,这个目的就是产品,而活动本身成为了手段。而理论与实践活动所具有的都是“内在目的”,具有“自身显现”性。
对此,阿伦特的思路与亚氏基本保持一致。她认为制作活动会使人类陷入一种功利性的“目的—手段”深渊,在其中,一切事物的价值最终都会被贬抑为手段性或工具性的,作为“终极目的”的人本身最终也难免陷入价值虚无主义的深渊。她认为,要想突破制作活动具有强烈吞噬性的“目的—手段”逻辑,唯一的方法就是引入具有“自身显现”性的人类活动方式,即她所说的“行动”。
然而,我们对一种活动的“自身显现”作出判断的标准来自哪里?它有两种可能的来源:一是活动显现其中的作为共同体的“显现空间”,一是对承载该活动的主体的功能性剖析。但作为“德性”的来源,后者运用于人类之外的活动或事物尚可,一旦运用于对人类活动的评价,则很难形成某种共识性的标准。
因为在现代背景下,对人类的任何功能性论断(如人的理性优越于感性)都难免陷入某种缺少共识的独断论,而它的另一面就是相对主义与虚无主义。在现代背景下,我们所能寻求的似乎只能是某种“共识性”的而非“客观性”的标准,因为“客观性”所依据的正是某种功能性论断。
这种“共识性”的标准预设了作为“显现空间”的共同体的存在,这意味着这种标准在本质上是“政治性”的。正是在这里,阿伦特与亚氏的思路开始发生分歧。可以看到,亚氏对人类活动作出评判的标准是基于人的功能性,对人的诸功能部分及其活动的价值分级,则是以这些部分的活动方式所拥有的“自由—自足”程度为标准。
“自足”一词包含两重含义:因其自身(而被选择)与不役(依赖)于物(或人)。为亚氏所推崇的沉思生活在这两重含义中都走到了极致:沉思生活与实践(政治)生活一样,都是因其自身而被选择的;同时,与实践(政治)生活不同,沉思生活既不依赖于物,也不依赖于人,以至于达到了“遗世独立”的程度。
因此,理论理性是人的最高功能部分,其活动沉思被认为是人的最高等级的活动。
在此,我们可以看到阿伦特与亚氏的基本分歧。阿伦特在解读亚氏作品(主要是伦理学和政治学)时,已经敏锐地看到了亚氏对人类活动的理解中所蕴涵的这个深层问题。因此,她基本抛弃了前述的“自足”的第二重含义,而此种含义中的“自足”更应被称为“纯净”这在亚氏对人类活动的自足性,乃至对人类活动的整体价值秩序的理解中,都居于至关重要的地位。
据阿伦特看来,亚氏以“自足”概念串联起他对人类活动的理解,并不是一种十分妥当的做法。
在以“自足”程度衡量制作、实践和沉思,进而作出价值排序之时,亚氏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这样一点:制作活动的不自足与实践(政治)生活的“不自足”具有“质”的不同。由于制作活动的目的是外在于活动本身的,因此其“不自足”性是一种束缚,甚至具有奴役的性质。但实践(政治)活动与此截然不同。实践(政治)活动内在地需要他人的“共同在场”亚氏认为正是这种内在需要导致了它自足程度的不足。
这种看法显示出了亚氏对“自由”概念某种程度的轻忽。实践(政治)活动与制作活动的内在需要,在与“自由”的关系上是完全不同的:后者束缚了“自由”,甚至对活动者构成了某种“奴役”;但前者却是对“自由”的实现。
对此的论证涉及阿伦特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根基,也就是“自由”与“他人”的关系。简言之,每个人都通过与“他人”之间“相互给予”“新”的言行而获得“自由”。阿伦特认为,“自由”意味着我们不断地通过“新”的言行重新“开始”,创造“新”的开端,但这种“开端启新”的言行本质上是“朝向”“他人”的,是对“他人”言行的“回应”。
这种与“他人”本质关联的“开端启新”的“自由”概念,是在亚氏的视野之外的,但对于阿伦特而言却具有终极性。阿伦特的自由概念显然也与“自足”观念密不可分:阿伦特意义上的“自足”指的是“以自身为目的”。不过,她对“自足”的理解比亚氏要节制许多:后者追求的是最高程度的“自足”他认为一种活动只有抛开对一切人或物的“依赖”才算是“彻底”的“自足”。
阿伦特正是在此处与亚氏的思路发生了基本的分歧,同时正是在这里,亚氏自身的内部思想矛盾显现得最为突出。针对亚氏,阿伦特所要做的正是辨识出他的思想内部的这些“柏拉图的影子”,并由此达到对希腊政治思想的“正本清源”。


















![>《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于建嵘)扫描版[pdf]](https://pic.bilezu.com/upload/3/4e/34ee5eb09e18b6db12c7bfd79c631003_thumb.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