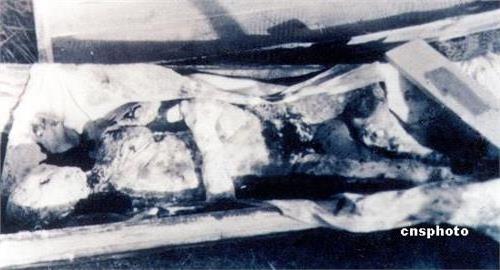蔡文姬焦菊隐 “文化大革命”中含恨而逝的焦菊隐
作者:赵起扬(文化部原副部长、前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
原载《纵横》 2005年第12期
1975年2月28日,焦先生悄悄地、冷清清地走了。没有发讣告,没有组织大家向遗体告别,没有开追悼会。他悲凉地戴着一顶“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历史反革命”的帽子离开剧院。他一生导演了许多戏,时代导演了他悲剧的一生。
听说剧院得到他即将死亡的通知后,军宣队和个别领导成员来到病房,他们像牧师最后一次给垂危病人祈祷似的想超度他的灵魂,不让他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焦菊隐,你还有什么话对组织交代吗?”给他最后一次机会去承认自己反动的罪行。更有甚者,剧院通知家属,不许给焦菊隐穿衣服,只能用一张床单包起来去火化,骨灰盒也只能买七元钱一个的,而且骨灰盒只能放在八宝山的地下室。这做得太过分了,太无情了。
关于焦菊隐的政治历史问题,1952年人艺建院时就有了他在国立剧专国民党区分部选举时,他当选区分部委员的材料。北京市委根据党的政策,对民主人士(焦菊隐当时是全国政协委员)的这类问题持慎重态度,所以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未向焦提出过这个问题。
“文革”中,军宣队在一次全院大会上,把这个材料拍在桌子上要他承认,焦却平静地说,在他的记忆里,从来就没有过这件事情。这就成了对他批判审查的大事情。
焦菊隐在病中很痛苦地说:“连我自己也糊涂了,为什么国民党说我是共产党,共产党说我是国民党?”尽管他是带着蒙冤的遗恨而去,然而他始终坚持自己的心地是清白的。
粉碎“四人帮”以后,人艺党委做了大量的调查,曾向剧专在江安期间与焦共过事的20多人(包括校长余上沅)进行访问,对证核实。大量材料说明:焦于1942年在江安剧专期间除根据当时国民党的规定:凡在剧专任教授者,必须参加国民党。
焦菊隐除被迫填写了参加国民党的表格外,没有参加国民党的任何活动。有些材料证明,焦菊隐当时的政治态度是倾向进步的,是受国民党监视的。如1945年10月,他写了一篇《自由大学》,刊登在国统区《新华日报》上,内容是反对反动势力干涉学校教育。
至于他在抗战胜利后回到北平以后,无论在戏剧活动方面,还是1948年由他倡议北平各大学教授联名抗议国民党逮捕师范大学八名同学的正义活动上,以及最后在地下党的协助下离开北平投向解放区石家庄,都可以说明焦菊隐进步的政治态度。
我与焦先生在北京人艺共事22年。但真正地、全面地、深刻地了解他,那还是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
这场十年浩劫一开始,我就被打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到了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时,我又被打成“北京市文化艺术界复辟回潮的代表人物”,他就自然地被打成我“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
在“文革”中,凡是被造反派列为批斗对象的人,无一例外地都要被关进“牛棚”,实行“三同”加“一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同挨批斗。凡进牛棚的人,一切自由也就随之消失了。大家长时间被关在一起,彼此也就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焦菊隐在“文革”中沉默寡言,即使我们在休息中谈一些生活中的问题时,他也言语不多。
“文革”初期,焦菊隐为他的大女儿宏宏的生日写了一封祝贺信(此信是在“文革”后发现的),其中只有四句话,大意是:我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我将来还要做导演的,我现在没有钱给你买生日礼物,希望你一定要努力学习。
这封信,头两句话好像是发表了两点声明,但重要的是他告诉下一代,让女儿相信自己的父亲不是坏人;第二层意思是让女儿相信他在这场运动中能够挺得住,不会悲观绝望,而且还要继续做导演。因为他一生中最大的愿望就是做导演、排戏,就是在中国话剧艺术这块土壤上搞出点真名堂,为中国话剧事业扬眉吐气。
他在我们这群“黑帮”中是年龄最大的。“文革”那一年,我48岁,他已62岁了。他的身体并不太好,脚和小腿一直浮肿,而且还患有视网膜脱离,视力很差。尽管如此,不论是在批斗会上做“喷气式”,或被连续批斗站五个小时,或劳动时抬200斤重的垃圾箱,或两个人到郊区一上午装满一汽车沙子等等重劳动,他都毫不含糊地干得很出色。
除了我听说他在青少年时受过苦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这个人做什么事都不甘落后,每做任何一件事都要求自己做好。
在劳动中即使有些困难,他也不会表现出来,就连他自洗的衣服,也从来都是晾干、叠平放在身子下边,使之平整不皱。再如各单位都进行“拉练”,北京人艺组织全体人员,打起背包,从北京出发到顺义、平谷行程500里,他没有叫苦,也没有要求别人照顾。这就是焦菊隐的性格。
根据他平时慎重的工作态度,原以为他的沉默寡言会持续下去,其实不然。大概是在1971年,人艺全体人员被下放到郊区团河进行劳动锻炼,从育秧、种稻开始到收割全过程都要参加。每两周回城休息两天,每次都留下四五个干部留守看管稻田。
这次轮到焦菊隐留守了,晚饭后大家一起看电视,正巧看的是《红灯记》。看片中,他忽然感慨地说:“我在北平创办中华戏曲专科学校不能全给否了,你们看样板戏中不少都是德、和、金、玉班的,我为京剧界培养了不少人才 ”的确,从中华戏曲专科学校毕业的学生,据我所知,像傅德盛、宋德珠、李和曾、王和霖、王金璐、李金泉、李玉茹、侯玉兰、陈永玲、高玉倩等等,都是全国著名的演员。
《红灯记》中就有三位,一位是演李母的高玉倩,一位是为《红灯记》作曲的李金泉,还有一位是鼓师耿金群。
后来我听到他的这一番感慨和自我辩白简直不可想像,他这不是自找苦吃吗?不是自己送上门让人家进行批判吗?但不知此时此刻他为什么非发表这样的感慨不可呢?实在不能理解。
可能是“文革”开始以来,把过去他为国家做出的那些成绩都扣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对这一笔抹煞,他是不服气、不平的。特别是中华戏曲学校是他创办的,为改革京剧旧科班的弊端,为改革旧课程,他曾受到戏曲界保守派的打击而被迫出走国外,至今仍记忆犹新。
现在把事情颠倒了,他觉得受到极大的委屈,怀有很大的愤懑,他隐忍四五年都没有向谁表述过。也许这天晚上他触景生情,当看到自己的学生在“样板戏”中出现时,他就情动于衷地把他想要说的话一下子发泄出来了。当时虽然没有对他进行批判,但还是送给他两顶帽子:一是为30年代翻案;二是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翻案。
1964年,依江青指令,北京人艺和北京京剧院按原样重演《智取威虎山》。这一举动的背景是:上海京剧院第一稿《智取威虎山》来北京参加现代戏会演,受到评论界的批评,江青很生气,就叫北京人艺和北京京剧院同时演出这一题材的两出戏,说是:“叫大家比较比较,看上海的戏好在哪里 ”此时从院外传来一条小道消息,说《智》剧要受批判。
我们没有管这些,对上演这个戏我们是认真对待的。焦菊隐是《智》剧的导演,我和焦菊隐一块到剧组动员,要求按原样演出,不改一句台词,不改一个动作,听听不同意见有好处,还说这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一定要保证把戏演好。
戏演完了,事情也过去了,但在“文革”中,这却成了北京人艺一大罪状,说这次演出是有意反对江青;反对京剧现代戏;说什么八大金钢占据舞台中心;群魔乱舞;歪曲解放军形象等等。
大帽子铺天盖地而来,在焦菊隐参加的一次小组会上进行了批判。军、工宣队参加了这次会议。焦菊隐解释这不是阴谋,也不是反对谁,是奉命演出。
这当然满足不了当时那种无限上纲者的要求,指责他是包庇黑线,包庇旧党委,“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个工宣队员甚至口吐脏话侮辱他是“耍死狗”。他受不了这种人格侮辱,以后他就再也不回答问题了。在这种黑白颠倒、是非不分、以势压人的气氛下,焦菊隐没有跟着上纲,没有昧了良心拿艺术去做政治交易。他除去说明当时的真相以外,不多说一句话。
1972年,在全院大会上宣布成立三人领导小组,但没有说谁是小组长或负责人,只是说了一句由赵起扬多抓点工作。于是赵起扬被大家称为“赵多抓”了。会后焦菊隐悄悄地对一个演员说:“起扬同志又要抓创作了,以后我就有戏可排了。
”这个时期确实是抓起创作来了。剧院全体艺术干部都下去进行创作,组织了五个组搞多幕剧,近十个组搞独幕剧。已经六年没有演戏了,演员们如饥似渴地想上舞台,想演戏,没有剧本不行。所以大家对搞创作都很积极,连曹禺同志都动情了,他提出要写《巴黎公社》,把于是之、英若诚调去做助手。剧院真正热闹起来了。
焦菊隐在这一段时间的精神比较好,因为中央有一个文件,其中对于“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要“一批二用三养”。因此那时的当权者对他的专政不像以前那样严了。有些胆子比较大的艺术干部还敢到他那间又潮又暗的小屋去聊天,请他给讲点什么东西。
如方 Unfixed Problem here?Unfixed problem in this lineg德的女儿请他教英语,王志安同志请他讲授导演。不管是谁,凡是对他有要求的,他都热情对待,认真讲授。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剧院新创作的多幕剧《云泉战歌》进行连排了,军宣队通知焦菊隐可以来看戏。这是焦菊隐自“文革”以来第一次被允许可以参加艺术活动。
“文革”中和焦菊隐接触最多的一位演员得知要焦去看连排后,就急急忙忙地跑到他住的小屋开门见山地说,不希望焦去看连排。焦问为什么?他说,形势和政策都是在不断地变化,今天说要用你,明天可能一脚把你踢开。焦则表示,已通知我去看连排,而且已经答应了,不去是不礼貌的。
这位演员说,如果你非去不可,我提出三个办法供你选择:一是看完戏一言不发,这样他们就抓不住你的辫子,顶多说你不积极;二是净讲好话,一个字也不要批评,他们顶多说你有顾虑,不诚恳;第三种办法是凭着你的认识水平和艺术水平,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但我不希望你选择第三条。因为这条办法的后果不堪设想,即使暂时不批,也会记你一笔账,随时都可敲打你。
焦听完这位演员非常周到的思考之后,没有讲话,只是看着他笑了一笑。这位演员猜不出这一笑是什么意思,不知焦选的是哪种办法。但一直为焦担心。
第二天,焦为看这次连排,还郑重其事地整了装束,虽然穿了一件半旧的灰制服,但干干净净,平平整整,裤线棱角分明,头发梳得整齐黑亮,人特别见精神。他是很认真对待这次看连排的,给人一种俨然像是昔日人艺总导演的神气。他不紧不慢迈开方步登上三楼大排练厅。看到军宣队没有招呼他坐在前几排,便很自觉地走到最后一排,和演员们坐在一起。
连排结束了,没有请他参加讨论,第二天军宣队派人去问焦菊隐,让他谈观后感,他没有提一条具体意见,只说了十四个大字:政治上刚及格,艺术上只能给二十分
对焦的访问记,很快地登在了剧院的十三号简报上。那位关心焦菊隐的演员看了简报后焦急万分,见了焦就说:焦先生,你捅了大漏子了,三种办法你为什么偏偏选中最坏的一种呢?焦很平静地说:我一辈子都是凭艺术家的良心办事的,你跟我排过不少戏,你应该了解我,我知道你的意见都是出自善良的愿望,我谢谢你对我的关心。
军宣队对他的意见尽管很恼火,但当时并未对他进行批判,可是这笔账已经给他记下了。
到了1974年“批林批孔”进入高潮的时候,也就是在北京展览馆有北京市文化艺术界参加的“批判赵起扬进行黑线复辟回潮”的大会上,点了焦菊隐的名,连他“为30年代翻案”,“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翻案”的账一块儿算,说他“反对新生事物”,说他讲《云泉战歌》政治上刚及格是假,艺术上只给二十分是真,说他是一贯地反对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是明目张胆地反对“三突出”的创作原则等等。
焦菊隐对《云泉战歌》的评语,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在艺术上的发言,也是他在政治环境极为恶劣的情况下一次战斗性的发言。对于“四人帮”在文艺上倒行逆施的极“左”方针与封建法西斯式文化专制是一次严重的挑战。
当“批林批孔”逐渐深入的时候,特别是焦菊隐已经知道这次“批林批孔”主要是批“周公”的时候,他对于国家的命运感到担心,他觉得自己的前途暗淡了。他对一位演员说:“我已经彻底绝望了,今后我也不能再做导演了。”他的精神崩溃了。
从此,他的情绪一直不好,不久就住进医院,诊断为肺癌,已无法做手术。尽管医生瞒着他,但他懂外文,从床栏上的病卡上,他明白自己已经得了不治之症。他要求把大女儿焦世宏从陕西调回来。费了很多周折,宏宏才出现在他的面前。
他对女儿说:我在“文革”中写了几百万字,比斯坦尼都写得多,可惜都是交代问题的材料。我要去了,没有别的东西可留,但还有一些做导演的心得体会,一定要把它留给后人。我知道自己还可以再活两年,你把我说的都记下来,这要难为你了,孩子!
宏宏听了父亲的话,心如刀绞,难过万分,想说几句安慰父亲的话,但已泣不成声。
宏宏虽然已做好了记录的准备,但焦先生由于对化学放疗反应强烈,病情随之不断恶化,他实在支撑不住了,他在离开人世之前,惟一一点珍贵的希望也没能够实现。终于,在1975年2月28日含恨而去。
焦菊隐有许多理想都没有实现。据我所知(当然只是极小一部分),如他对于话剧民族化的理论只写出一篇提纲。太可惜了,这是一篇影响戏剧发展的一个新课题。又如他很早就想排出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哈姆雷特》。解放前在北平,他就曾用京剧的形式演出过《铸情记》(即《罗密欧与朱丽叶》)。
尽管他的这种精神在人艺的许多外国剧目中也有所反映,但总是没能由他自己排演而总结出一套经验来。再如,他很早就想把《白毛女》改编成话剧,构思已经比较成熟了,他要将原歌剧后半部作重大修改,他要把喜儿这个人物一直贯穿到底。
还有,他不仅要继续进行像《虎符》那样的民族化实验,而且还想对西洋话剧的各种流派做实验,来滋润丰富中国话剧,使中国话剧能扬眉于天下。
他热爱戏剧事业胜于爱惜自己的生命。他在艺术创造上那种刻苦钻研、锲而不舍的忘我精神和为中国话剧事业所做出的重大贡献,已是人所共知的了。人们都说他创造了人艺的艺术风格,可他自己的生命也成了这艺术的祭品。
他的艺德如何,院外人还不太知道,院内的老同志却非常清楚。他排戏虽然要求极为严格,但从不独断专行,有困难总是和大家商量,演员们公认他是最能启发人们创造角色的导演,最能发挥演员艺术创造力的导演。他在和演员合作中,从不计较个人恩怨,甚至个别演员在几个戏中与他合作都爱争论,别人建议这个戏就不要再用这个演员了,他却不以为然,认为从该戏的整体出发,她是全体演员中担任这个角色最理想的人选。
焦菊隐生前,人们对他的传说很多,褒贬不一。通过多年的接触以及在“文化大革命”风暴的考验中,我觉得虽然他也有缺点,但他一生的主流是热爱祖国,热爱艺术并忠于艺术的。他对于中国民族艺术有精辟的解析,他对话剧建设做了开创性的贡献。
他不仅是一个宁愿抛弃在国外当教授的安逸生活而回国参加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爱国者,而且是尽其所有报效祖国文化戏剧事业的痴情到“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执著的艺术家,就在他临去世前政治上得不到正确结论的时候,他竟能撇开这不公正的对待,要把应留给后人的宝贵艺术经验毫无保留地贡献出来。
在他身上体现出中国知识分子所特有的傲骨与忠贞的品格;体现出为自己的艺术理想而心疲力竭地战斗到最后一息的奉献精神。
谁能想到,北京人艺创建人之一,中国著名的戏剧教育家、翻译家,北京人艺艺术风格的带头人,“中国话剧学派”的探索者,戏剧界一颗灿烂、光辉的巨星,竟是这样冷漠凄凉地殒落了。这对北京人艺和中国戏剧界,都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他不是在生前而是在死后,享受到人们真正对他的崇敬。













![蔡文姬回血8000出装 王者荣耀S10蔡文姬出装攻略 S10蔡文姬怎么出装[多图]](https://pic.bilezu.com/upload/4/11/4113b4f26b92860eb4f1c10396853ade_thumb.jpg)